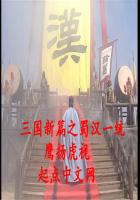但不多久,景象有了,记忆有了,思绪有了……自己在哪里呢!在沈家院落的老房子里。为什么会有刚才天堂、地狱般的遭遇,一定是做梦了!对,一定是做梦了,唯有做梦才能解释这种际遇,从才能解释自己明明被碗口大的蚂蚁、蜈蚣、壁虎或是别的什么虫子吃掉了可显然依然活着的事实。可那梦也太过真实了,真实到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真实到梦中自己的感受都清晰明了,真实到如同这些事情就如同真实发生过一般。可惜世上没有九维空间或是科学家没有证明出九维空间的真实存在,没有证明出真正存在着天堂与地狱,要不他可真的相信了……屋子里静静的,没有人任何人存在,也听不到任何人讲话,闻不到任何人存在的气息,他想努力着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可刚刚站起来才走一步就不知被什么东西拽到了!“啥东西?”“什么破东西?”当他念叨着朝后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双手都被铁链子锁了起来,铁链子绑在了火炕拐角的一根铁棍子上,铁棍子深深扎在墙里。他朝铁棍子冲去了,奋力的想拔出扎在墙里的铁棍子,可刚一用力,便再次摔倒了……
“怎么了?”
“到底则么了?”
“自己这到底什么怎么了?”
“难道还在梦里?”
“……得罪了什么人嘛?”
……
他奋力的思索着,奋力的思索着眼前这一幕发生前的所有故事,所有过往:似乎自己买了了漂亮的媳妇,可媳妇总是断断续续的时不时的伺机逃脱;父亲死了,死在一个柳絮恒生、草长莺飞的季节,死因似乎也与自己有关;母亲总是在啼哭、不停的啼哭;马山遍野的罂粟花开着,不败的开着;似乎有直升飞机从头顶飞过,飞过之后罂粟花便没了,地理充满了刺鼻的怪味……有人闻到那种味道手足舞蹈着……街尽头的骨架似乎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一个插入云霄的尽头……“哥特风格的,这个哥特风格的,晋北,晋北……不,是中国,是整个东方世界里最最美,最最虔诚的教堂,比巴黎圣母院还巴黎圣母院”有人在边点头边年脑着,那人似乎是一个穿着黑色袍子的眼眼镜白皮肤的人,对是神父,肯定是传说中的神父……奥,一个女人被乱石头砸死了,死前那张脸似乎朝着他看,那是一张凄美动人的脸,奥,蓝眼睛白皮肤,原来也是蓝眼睛白皮肤,怎么了,怎么又是蓝眼睛白皮肤,那个女人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记忆好乱,真的好乱,这是真实存在的吗?真实存在过的吗?还是自己的脑子发生了状况,仰或自己依然在梦中……不可能在梦中了,在梦中或者人死了进入阴曹地府看到阎王孟婆是看不到自己影子的,所以自己定然是在现实中,切切实实存在的现实中……可现实怎么了,自己怎么会被人锁起来了……一块碗口大的镜子出现在了不远处的灶台边上,他连滚带爬的朝镜子冲过去,拿起了镜子。一张熟悉由陌生的脸出现在了镜子里。当他看着镜子的时候,忽然发现镜子里的男人也在看着他。镜子里的那个男人?啊?那是一个男人嘛?那个男人怎么那么熟悉,那眼神,熟悉的眼神,分明是自己啊!再熟悉不过了。自己,怎么会是自己,自己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模样?奥,也不是自己!是做梦了,肯定做梦了。当这种想法再次冲心头冒出了的时候,她再次摸了摸自己的脸,他掐了一下脸颊,疼的,有疼的感觉,所以应当是在现实中,自己应当在现实中。可现实中怎么了,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怎么会变得骨瘦如柴、面色如纸,怎么会变得毫无活气,怎么会变得或者如同死了一般,怎么会变成梦醒如同做梦一般。那种浑身发痒的感觉再次袭来,如同梦里蚂蚁、蜈蚣、壁虎爬过来即将吃掉自己时候的那种感觉一般,那种感觉居然不知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不知从身体里的那个部位袭来,进而弥漫到了全身。他开始用手挠,开始在炕上打滚,可这一切终究毫无半点作用,滚烫的感觉上来了,万箭穿心额感觉上来了,万蚁啮骨的感觉上来了、万针刺心的感觉上来了、万嘴吮血感觉上来了、万虫断筋感觉上来了、万刃裂肤的感觉上来了,他开始难以忍受,开始痛不欲生……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朝他张开了邪恶的讪笑,对,这次是邪恶的讪笑……啊,就是这种花,就是这种花朵产生的白色粉末啊,就是这种花提炼出的乳白色液体,就是这种话凝固了的暗黑色药丸,就是这种话加工而成的乳白色粉末,对是这些,就是这些,这是是他此刻想要的,这些就是他此刻最最想要的,也是能够驱赶万箭、万蚁、万针、万嘴、万虫、万刃的东西啊!啊,罂粟花、乳白色液体、淡黑色药丸、纯白色粉末,你们在哪里,在哪里,快点出现,快点、快点来拯救我吧!他一边打滚、一边苛求、一边祈祷着,可没有屋子里静静的,门窗冷冷的,没有回应,没有任何人的回应……一种自杀的冲动开始弥漫心头、脑海,于是朝强壁冲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