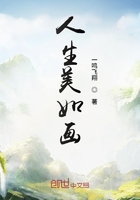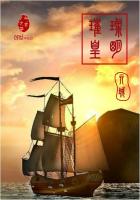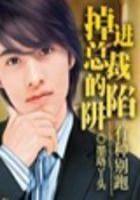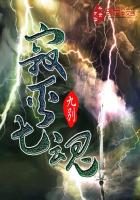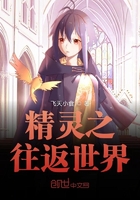相比常水沟的其他村落来讲,常水村最大的优势在于有着丰富的天然林区。
这些天然林区来自远古的积累,来自庙宇的带动,更来自抗日战争年代里逃亡者的开发。
抗日战争年代,收大生产运动的影响,一些游击队和逃难的人们进驻了常水沟和土生土长的沟里人汇合在了一起。许久之后,茂密的森林逐渐稀疏,零星的房舍逐渐多了起来,开拓者和土著居民们用尖刀利斧将或是茂密或是光秃的山岭变成了绿油油的庄稼地。然而,当大豆、豌豆、莜麦、胡麻、油菜、甜菜或是山药蛋(土豆)逐渐填饱人们肚子的时候,沙尘暴、干旱、洪水、泥石流等一大堆的自然灾害也便逼近了人们的生活。
这个时候,原是游击队员,时任村干部的明姓小伙提出了植树造林的建议。
村委会获得了通过,村民们执行了决议。
十多年后,明姓小伙变成了中年明姓,并且成了村支书。
也是在这样的年月里常水村的生态逐渐恢复了平衡,与生态恢复相伴的还有年年增长的粮食与日渐辉煌的明家大院。
又过了十多年,向晚年过度的明姓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当明老太爷的称呼在沟里日益传开的时候,常水村的人口达到了极限。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村支书沈贵带领村民再一次伐木垦荒。
伐木垦荒的第三年夏,涓涓细流的常水河宛若发怒了的魔鬼一般横冲直撞了常水村。
那一年起,修路成了常水村乃至常水沟人每年夏天反复做的必修课。
在道路不断的疏通与堵塞中,常水村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世外桃源。
不知有改革,无论开放。
无电、无路的常水村被时代丢在了历史的暗角。
无人问津。
“不是有路通的时候吗?”也许你会问。
路通的时候,要想让一辆车通过十五里坑坑洼洼的石头路,最少也要三个小时。
无人对这里感兴趣,有路等于没路。
电也没有嘛!
是的!
没有!
不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常水村始终与电力无关。
常水村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常水村人没有午饭,没有午休,没有中午。
夕阳西下,晚霞来临时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谈时常水沟人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
黑暗来临的时候,各家的煤油灯如同苍凉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点缀了孤寂的夜空,凄美而纯净。
是的,常水村不仅是星星点缀的时候,就连艳阳高照的时候,同样的孤寂,同样的落寞。
常水沟的最深处是当地闻名的天然林区大望山,大望山的涓涓细流孕育了常水村。河流往前大约两里是一块开阔的谷地。
常水村人三三两两的屋舍便分布在谷地的两旁。
面朝南坡、背靠后坡。
由于降水和光照的原因,南坡成了一座“佳木秀而繁阴”的山。在明枫出现的时候,其繁阴的程度虽然随着刀耕火种而减弱,但奇峰怪石、悬崖绝壁、灌木杂草依然吸引着当地一拨拨的登山者。和大望山一样,南坡是各种动物游荡的乐园。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常水村人总能各种各种动物的叫声。
狼嚎的悲鸣、猿啼的悠扬、野猪的刺耳、嘈杂的虫鸣、多样的鸟叫……
后坡在革命战争年代原本是有些草木的,但随着刀耕火种的加快,当明枫走进常水村的时候,它早已成了一毛不拔的,可以喝大望山比高低的石丘。不过山上依然如南坡般奇峰怪石、悬崖绝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