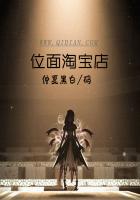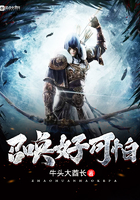这种社会伦理标准起源于何时,目前已经没有确切的记载,是孔子见南子不敢直视对方的那一刻,是阮籍穷途当哭的一个个日落的黄昏(据史书记载,阮籍曾去为一个未曾相识、极有才华、未曾出嫁的女子莽撞吊丧,在灵堂前大哭,而自己母亲去世当日自己和友人象棋,死讯传来后,对方要求停止,他却板着脸不肯罢手),还是温庭筠远离鱼玄机寄情于山水歌酒的醉生梦死之间。
步入近代以后,西方的民主、科学、自有、博爱等观念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传入终于,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天朝上国”梦的荒昧可笑。于是扎根于国人心中的传统观念开始解体、坍塌。新文化运动八年后,出生于广东望族许氏家族的许广平走入了鲁迅的课堂,那时鲁迅,这个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给学生上《中国小说史略》。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后期,整个社会弥漫着冰冷、潮湿、腐臭的滋味,鲁迅给学生(尤其是许广平)带来了和煦的春风。许久之后的某一天,许广平开始模模糊糊的试探,当天夜里她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称她为“广平兄”,于是二十六岁的她失眠了,诚如十多年来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已经步入中年(当年鲁迅四十四岁)的他一样失眠一般。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在漫长的通信过程中,鲁迅一直不敢直视已然存在的自己与女学生之间所产生的禁忌之恋。于是许广平搬出了老师课上所讲授的《出了象牙之塔》,故事中一个年长的老师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相爱了但老师认为不能相爱,但女学生却认为到了晚年神未必这样想。反复思量后,鲁迅接受了许广平的爱。那个年代里,关于他们,世人眼里尽管存在着诸多的非议,甚至没有得到亲人的祝福,但他们的爱却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生命的最后一刻,鲁迅握着许广平的手告诉让对方忘记他好好生活。许广平做到了,研究、宣传、保卫鲁迅文稿,积极主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继续鲁迅未尽的事业。文革开始的时候,红卫兵雕刻鲁迅塑像的后来征求许广平的意见,许广平说那不像她的导师、丈夫,他们还是把它派上了用场——那个对旧社会充满愤怒的满是革命气质的鲁迅。没多久,许广平离世,在她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念的梦里,鲁迅依然那么消瘦、温暖、充满活力——那才是她的男人,让她生命为止燃烧的男人。纵观鲁迅的一生,无愧于世人对他的评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然则在李恪的追根溯源中,最让他佩服感动的确实对方对生活与爱情(尤其这一点)的态度: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与许广平,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一路走来,历经诸多的凄风苦雨,一直相互理解、信任、包容,这一点着实感动了李恪,重塑了他对爱情、对生活、对文学创作的新的认知。然则,之后不久,等他读完《与从文书》后,却再次迷茫了。他再次想起了电影《黑色大丽花》中的台词:在童话的浮华外表下,是难以为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