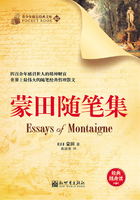在昆明联大任教期间,唐兰开了很多课程,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大师,从甲骨文到楷书,原原本本地道出了文字的构造和演变。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该校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的评介是:“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是甲骨文、金文的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除了《说文解字》之外,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此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他特意于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在提到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时说: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接下来要阐发一番宏篇大论。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和今天的诵读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古人一直很强调诵读的重要性。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到词的细微美妙之处,颇有点禅宗“明心见性”的意味。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
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过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书法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以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当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
师徒情缘,巧系红丝
唐兰门下桃李无数,语言学家朱德熙是他在联大培养的众多学子当中的翘楚者。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进一步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德熙有幸听了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和甲骨文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1946年5月,在闻一多推荐下,朱德熙正式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
唐兰不仅是朱德熙的恩师,还亲自为弟子牵线搭桥,做了一回月老。朱德熙与何孔敬订婚时,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为条幅,并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
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还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正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由此不难看出,唐兰与学生的感情是非常融洽、亲密的。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描绘唐兰讲课时的神采: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数年后联大复原,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开文字学课,裘锡圭任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唐兰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他的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
此外,唐兰的弟子汪曾祺还提到其师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这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着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当中传阅,丝毫也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竟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这些教授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将其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先生有着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成绩卓著的学子。在他培养的学生当中,有许多早已成为知名学者。唐兰先生每谈起这些人时,心中总是充满欣慰的幸福。1963年,北京大学请先生作关于古文字专题的演讲,先生刚一走进演讲会场,下面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见先生影响之大。
治学严谨,于书无所不窥
唐兰先生知识渊博,有着深厚而扎实的国学根底。他在1939年出版的《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说:“九年冬就学无锡,同学有熟习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奋小学,渐及群经。”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曾称赞唐兰先生“于书无所不窥”。先生运用文献学、文字学、历史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知识,在学术研究中游刃有余,取得了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重要成果。
先生治学严谨,对一些治学的不良现象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例如,先生在去世前不久发表的《蔑历新诂》一文中说:“我对‘蔑历’一语,往来心目中,将五十年了,未敢轻于下笔。”可见先生在学术上用心之良苦,态度之谦恭。先生在一些论述中还批评有些人“想用十天半月东翻西检作学问是绝对不成的”,有时“外面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一个真实的学者,决不肯把学问看得如此容易的。”
先生一生用力最多、最勤的,应首称中国古文字学。古人最早将汉字的学习和研究称作“小学”,近人始称“文字学”。对汉字形体构成的研究,早在秦汉时代已逐渐形成“六书”之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六书更加理论化。六书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对这一有关汉字构成的传统说法,一般学者都墨守成规沿袭之,不能摆脱秦汉以来“六书”说的羁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唐先生在研究古文字上,并不因循守旧和人云亦云。他在《中国古文字学》一书中说:“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现在所看见的商周文字,都要早上一千年,而且古器物文字材料的丰富,是过去任何时期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不去自己寻找更合适精密的理论?”唐先生突破旧说,创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建构成汉字的“三书说”理论,对研究汉字的构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师小传】
唐兰(1901—1979),号立厂,又作立庵,曾用名唐佩兰、唐景兰,笔名曾鸣等。文学家、金石学家。1929年在天津主编过《商报》的《文学周报》及《将来月刊》。1930年在辽宁教育厅任编辑。此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36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北京。1952年回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等职,后任副院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8年任中国古文学研究会理事,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沈从文:创作、教书均怀赤子之心
沈从文先生教学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的爱学生的心。在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身为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的沈从文,开过“大一国文”、“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同时参加《国文月刊》的编辑工作)。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用手势,也没有任何戏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过他的讲课风格:“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一言道出了沈从文先生的诚恳与率真。
胡适提携,首次讲课
说起沈先生的从教之路,不能不提到胡适先生对他的提携与帮助。许多年过去之后,沈先生对于自己第一次上课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1928年,生活困顿的沈从文,收到了徐志摩写给他的一封信:“你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但是,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重返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一句“教书”,点燃了沈从文心中的希望,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当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该校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资料估计足供1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槛,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6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今天又是他上的第一堂课。因此,来听课的学生非常多。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过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相、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所以,在他们的头脑里,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面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故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1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5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5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
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
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18岁,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她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并成为他的夫人;而沈专一、热切追张的故事,也成了中国近代高校与文坛的一段佳话)。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自己的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些心地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10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校长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虔诚育人,手书“写课”
在教学育人方面,沈先生很会为学生着想。为了让学生腾出更多的自学时间,他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这里面有他为学生们批改的习作,也有他特意为学生们找的各种课外读物。
在讲《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的时候,有些资料一时不易找到。作为老师,他完全可以给学生指明方向,让学生自己课下去找。但沈先生不是这样,他自己动手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1尺,长4尺,并不裁断。抄成之后,卷成卷子,上课时发给学生。当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沉甸甸的资料时,心中的分量远比手中的这些竹纸深重许多。大家内心里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对沈先生敬业精神的钦佩!
由于沈先生祖籍湖南,讲课时不免带有浓重的湘西口音。有些学生因为听不懂,渐渐失去了兴趣。沈先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补救办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他评点的文字,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因此,有人戏称沈先生不是上课,而是在“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