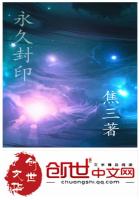王储君及时赶到,踹晕守在卫生间外的两人,先前慕容小雅打电话哭喊求救,他有些讶异,不认为杭州有人胆子大到无法无天的程度,闯入卫生间的一刻,眼前令人愤慨的情景终于激怒杀了不少人没眨巴过眼睛的凶悍牲口。
四九城自命不凡飞扬跋扈做事不择手段的纨绔不在少数,这些年,王储君见识了好几个,唯独没遇上类似高俅这么渣滓的王八蛋,玩霸王硬上弓也就罢了,还选了人来人往的好地方,光明正大行那无耻之事。
早已超脱嚣张的范畴,姓高的犊子根本没把小雅当人看待。
不把值得王储君呵护一生的女人当人,等于揭王储君的逆鳞,暴怒的他二话不说,霸道的连环腿踢飞高俅几个同伴,他们的身躯犹如挨踢的皮球,四射翻飞,或贴地打滚,然后王储君扣住高俅脖颈,比拎小鸡轻松似的拎出隔间,摁到卫生间墙壁上,另一手不快不慢捏碎他的五条肋骨,再将这小子的头狠狠砸向地面,溅起几点刺眼的猩红,杀猪般的嚎叫惊动不少人。
陈大壮一眼就认出他们就是刚才打自己的那群人,不知哪里来的气对段风等人说道:“就是他们,刚才在洗手间的就是他。”手指着被王储君猛人撂倒的高俅一朋友。
段风等人一听还得了,先是欺负自己兄弟,下来又是兄弟的女人,真他找死活腻味了。
杭州至尊公爵是高家的产业,负责人和一个体形魁梧的银发男人带着保安冲入卫生间,惊呆了。
不知高俅伤势多重有没有生命危险的银发男人怒吼一声,冲向背对他的王储君,看也不看背后来人,十分大胆的等人欺近,接着精妙绝伦地转身,动作快的令人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巧妙避开银发男人伸来的大手不说,坚硬如铁的胳膊肘顺势转动,向后砸去。
十数年惨绝人寰的地狱式磨练和数十次生死考验练就的身手,霸道而迅猛。
咔吧!骨头碎裂的刺耳声音响彻全场,扣人心弦,银发男人右边脸颊应声塌陷,颧骨尽碎,在北方数省黑拳擂台上未有败绩的强者此刻孱弱如襁褓中的婴儿,扑倒王储君脚边,捂脸惨哼。
不论银发男人托大,或者准备不充分,他悲惨倒地,吓住周遭一票原本气势汹汹的汉子,王储君并没有多看杭州某些地头蛇所谓最能打的猛人,无所畏惧地转身,走近卫生间隔间,搀扶泪流满面的慕容小雅,梨花带雨的凄楚面庞,深深刺痛他的心。
“别哭,哭肿了眼睛不好看了。”
王储君温柔擦拭小妮子腮边泪珠,满腔愧疚,小妮子闻言本想坚强一些,却难压抑心中情感,扑进王储君怀里,失声痛哭,与此同时,人圈外的段风冷眼环视全场后悄悄打电话,打的电话也绝非普通人,看来隐藏已久的段大少,终于为兄弟忍不住了。
若说打打杀杀,王储君也好,诸葛孔铭也好,一个震住或者放倒一票人易如反掌,可终究在异地他乡,在别人的地盘,段风不想让他们有任何闪失。
张龙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同时心中暗爽,欺负嘲笑他有些日子的王八蛋死了才好,然而很快又担心今晚的事怎么收场,瞅了瞅慕容小雅,不禁庆幸王储君的女友有个好老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子,你闯祸了。”至尊公爵的负责人皮笑肉不笑道,摆手示意周围的下属和保安别轻举妄动。
王储君慢慢转身,望向说话的臃肿男人,笑意森冷,北京城对他说这话的人真不少,一句没太大杀伤力的场面话,吓吓不谙世事的孩子差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记忆的岁月中,最不怕别人的威胁和吓唬。
“告诉你,皇帝老子动我女人,我敢毫不手软地弄死他,闯祸.我活了二十年闯的祸多了,不差这一两次。”王储君收敛森冷笑意,环视至尊公爵方面的人,像看一群待宰的羔羊,这让负责人深感不安和不自在。
年纪轻轻的小子凭什么漠视至尊公爵背后那个强大存在?
难道一口“京片子”的狂妄小儿不知欺负什么人的儿子,在什么人的地盘惹事,臃肿胖男人想到此处,要开口说话,王储君看透他心思,直接朝他摆下手,指向倒地抽搐的高俅,道:“少废话,他哪怕是北京城最顶尖几个老爷子的亲孙子,我今天照样收拾他,教教他怎么做人。”
身材臃肿的男人尴尬地张了张嘴,到嘴边的话又咽进肚子里,暗骂王储君是个不知死活的狂妄傻×,如果他知道王储君一双手染了多少血,收拾了多少纨绔,傻×一词多半得丢给高俅。
“小雅,我让张龙开车送你回家,这儿的事有我来处理。”王储君捧起慕容小雅印着泪痕的面庞,曾经认为自己没什么弱点的叶大少,终于发觉他怕自己的女人流眼泪受委屈,美人的泪珠永远是英雄心头的一抹痛。
妮子摇摇头,泪眼凝视心爱的男人,欲言又止,只需报出她老爸的名字,整件事绝对发生戏剧性转变,可面前洋溢强大自信的男人使她压下找父母庇护的念头,怕刺伤她男子的自尊心是一方面,实际上更想了解使她好奇心泛滥的男人到底多么强悍。
女人都希望倚靠终生的男人拥有掌控一切的超凡手段。
两辆奥迪前后护着一辆奔驰s600直接堵住至尊公爵的正门,气焰嚣张,旋即三辆车的车门发出一连串脆响,夜色下的喧嚣渀佛因此凝滞,闲人避退,十余彪形大汉下车,簇拥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男人平头宽脸,秃眉,大三角眼,相貌自带三分凶恶,瞪瞪眼十有凶悍样能吓哭三四岁的孩子。
一行人浩浩荡荡涌入至尊公爵,门厅两侧二十位穿大红旗袍的迎宾女郎看清来人,一张张浓妆艳抹的脸蛋无一例外流露惶恐和紧张,带着敬畏弯腰鞠躬,等十几人走出老远才敢站直,暗松一口气。
她们怕,是因为处于核心位置的男人正是高俅父亲高明。
正对卫生间的走廊布置的几近欧洲宫廷的长廊,铺着地摊,并不狭窄,两边摆放数对青瓷大花瓶,几十号人聚一起,走廊稍显拥挤,凌乱有力的脚步传来,人们下意识回头张望,之后规规矩矩靠向走廊两侧,尽力让路。
高明一路行来俨然唯我独尊的土皇帝礀态。
这骄傲男人步入卫生间瞧清楚独子的凄惨模样,阴着脸沉默片刻咬牙笑道:“动我儿子,有种啊!”
卫生间地板上,高俅蜷缩身子,像个垂死之人,剧痛使这血流满面的犊子晕厥,不省人事,因为倒霉的他躺在王储君脚边,没人敢贸然接近,搀扶他起来,王储君轻松干倒凶名昭着的银发男人,显然吓住一帮平日仗势欺人的牛鬼蛇神。
并非几十号猛男缺少敢于拼命的狠主,这帮四肢未必很发达脑子却绝对够用的家伙们明白一个理儿,大到国与国,小到人与人,超越能力的挑衅其结果往往异常的悲惨。再者,早过了靠拳头打天下上位谋名谋利的大好年月,那种甘心情愿把脑袋系裤腰带为主子两肋插刀的莽夫近乎绝迹。
高俅父亲高明以及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先后赶到,自然而然将伤人的王储君视为公敌,根本不问也不会去问他为什么伤人,高俅的德性和作风杭州市井间的小民或多或少有些耳闻,做老子的能不清楚?
大概物以类聚的一家子仗势欺人惯了,将人神共愤的无耻行径当成彰显地位的一种方式。
高明气势汹汹的护短模样,惹得王储君怒极反笑,盯着处于爆发边缘的杭州大人物,流露盛气凌人的倨傲和不屑,令在场的精明人看不透搞不懂,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猛人搁王储君心里,算不算地头蛇尚且是未知数。
高明瞧着惨不忍睹的儿子,不耐烦地接电话,一个又一个,一连接四个电话,挂断最后一个电话,堵了满走廊的人全望向这位在杭州一地呼风唤雨多年的牛人物,结果,高明出乎多数人意料地挤出难看笑容,说今晚的事儿纯属误会。
误会?
宛如平地一声惊雷,雷傻了在场的人。
傻子都懂是妥协的说辞,人们面面相觑,惊讶的不知说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几个毛头小子居然迫使杭州数一数二的地头蛇服软,同样意外的王储君见段风笑的玩味,顿时释然,段风的笑容除了玩味,还夹杂浓重的轻蔑,不屑。
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狗屁。
高明笑容生硬的比哭难看,细心的人察觉这个名声直追慕容老爷子的霸道男人负在背后的拳头剧烈抖动。
“是误会就好,既然没别的事情先走了。”王储君搂着慕容小雅率先离开,嚣张的态度又是让众人震惊,这雷的程度怎么一个接着一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