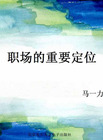不知道是兴奋还是迫不及待,顾一鸣驾车早早地就来到了贺红云居住的小区。早晨接贺红云上班是俩人商量好了的。因为那天去省办事儿有一件未了事情,他们打算今天早晨在贺红云家完成。有句俗话说:当一个人忘乎所以的时候,旁若无人可能是他们最鲜明的写照。
顾一鸣开车径直来到了贺红云家的楼下,找个位置把车停好,离开两步又返了回来,险些忘记锁了车。来到贺红云的门口,发现房门虚掩着,顾一鸣没有敲门,一闪身便钻了进去,房门咣当一声从里面反锁上了,门与门框的磕碰声顺着楼道传了出去,估计连后来又回来的张晓峰都会听见刚才的关门声,只是他没有往那方面想罢了。
“他刚走,没看见你吗?”贺红云趴在顾一鸣耳边说。
“他怎么能看到我呢,我到的时候楼下甭说汽车了,就连自行车都没有了。放心吧,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俩的了。”说完,双手又不本分起来,弄的贺红云浑身麻酥酥的。
“真讨厌,咱先坐下待会儿,聊聊单位的事儿。我不是倒小肠儿,昨天你怎么了,像是一只饿极了的野狼,恨不得扑上来把我咬死。”
顾一鸣像是检讨似的央求道:“前几天不是心情不好吗?”
“你心情不好就拿我撒气吗?我成了你的出气筒了。”
“不是出气筒,是心灵的垃圾桶。”
“要不着你这死皮赖脸的挽留,我真的横下一条心离开你,你以为缺了你这棵歪脖树就吊不死人了呢。”
“你再现找歪脖树多麻烦呀。”正当俩人你来我往斗嘴儿的时候,门外传来微弱的脚步声,“是不是他回来了?”要不怎么说做贼心虚呢。
一位同一楼门的居民下楼的脚步声着实把顾一鸣吓了一跳,“看把你吓的,是不是要钻地老鼠洞呀。”
“万一他这时候进门就不好办了。”顾一鸣不安地说。
“放心吧,知识分子的心都被课题占有着,他才不回来呢。”贺红云的话还没说利索,防盗门的锁柄在旋转,随着开锁的咔咔声,防盗门打开了,张晓峰走了进来。
“你怎么又回来了?”贺红云假作拢发掩饰着发红的脸庞说道。
张晓峰看了看没有什么异样后说道:“顾总来了,我忘记点儿东西回家拿来了。”
顾一鸣很不自在地站了起来,说:“我也是刚到,想接贺总一起上班,因为单位出了点事故,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这事儿想必她到家跟你说了吧,所以今天想开个会研究一下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相关制度。”
“现在干什么都不好干,看你们旅行社挺阳光的,其实干起来也是竟麻烦事儿。我们也是一样,整天泡在电脑里,家里家外的事儿都顾不上。我听说咱们旅行社的人没少帮助红云,包括家里家外的事儿,太谢谢你们了。”
“顾总,咱们走吧,开会的人差不多到齐了,哥俩有什么话抓时间再续。”贺红云主动提出来上班去。
虽然虚惊一场,但在张晓峰的心理,对他们俩微妙关系的疑虑更加沉重了。藐视的双眼看着他们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心中的无名之火一个劲儿的往上窜,恨不得追上前去一刀砍了他们,苦于没有证据,只能暂且过去。
等到上车后,顾一鸣的心还在激烈的跳动,冲着后视镜朝楼房的方向看了又看,直至确认张晓峰没在跟踪这才转过头来,看着贺红云苦笑的脸发愣,说:“你发什么愣呀,这事多玄呀。你知道就在他开门的一刹那,我的心都快出来了。”
“还我发愣呢,你着什么急呀,大早晨的到我这来,没事不是找麻烦吗。这回好了,张晓峰算是盯上咱俩了,只要发现咱俩在一起,到家后非得问出个子丑寅卯不可。”
“刚才我一进屋咱俩就……,那麻烦就大了。”
“还说呢,你也不嫌害臊。”
虽然顾一鸣与蒋秀英之间的矛盾还没有真正解决,但离婚两个字她已经说出了口,所以,事态的发展对顾一鸣来说很不利。
“在家休息的时候我们俩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得很好,不知什么原因昨天晚上又摔盘子又摔碗,并向我提出离婚。她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了。”
贺红云坐在后面的坐上,看着后视镜中顾一鸣可怜的样子心里乱糟糟的。自己能说什么?要不是那次同学聚会,要不是俩人都没能控制住自己,能出现这个结果吗?可怜的不是顾一鸣,而是蒋秀英,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忍受着顾一鸣经常的辱骂和殴打,而且还操持着这个家的里里外外,现在又担起了运输公司的管理工作。而顾一鸣不但不知足,不感谢妻子对他、对家庭所做的一切,反而红杏出墙,转移了对蒋秀英的感情,这太不公平了。张晓峰也是一样,虽然他还没有感到头上的绿帽子已经戴上,但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产生了怀疑。
“你想什么呢?半天不言语。”顾一鸣说完看看坐在后面的贺红云。
贺红云嫣然一笑,说:“顾一鸣,”
“嗯。什么事儿?”
贺红云接着说:“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说吧,我洗耳恭听。”
贺红云仰起头,不知从哪说起,迟疑了一下,说:“为了咱们两个家庭的和谐,我想咱们俩的行动从现在起要收敛一些了,免得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影响。你说呢?”
顾一鸣怎么也没想到,贺红云这个时候提出了结束俩人关系的话题,太突然了。如果是那样,这几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另外,顾家的企业没有贺红云的执掌,就凭自己的这点水平很快就会垮台。不行,结束关系可以考虑,但她继续在企业工作不能结束。
顾一鸣鼓起勇气说:“你不用说得太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想是这样,既然咱们俩有了这层关系,要想彻底结束我想是很难的,就好像人一旦陷入泥潭要想拔出腿来是要费一番功夫的,除非他陷得很浅。”
“那你的意思这层关系不结束了?”
“不,那不叫结束,准确一点说应该叫短暂休息,蓄发精力,以利再战。”
“当一个人不要脸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癞皮狗的水平。”
“你在说我吗?”
“难道不是吗?我都说出了结束咱们的关系,你还一个劲儿地短暂休息,蓄发精力,以利再战,战什么?再战我们的两个家庭会垮台的,你明白吗?”
顾一鸣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他不是不想说什么,而是贺红云的几句话使他陷入了理还乱的乱麻之中。片刻的沉默被车外的一片噪杂声打破:“那一帮人干什么呢?”
顾一鸣看到九曲河边围着一帮人不解其缘由,问到。“有人落水吗?”
“不可能,大早晨的谁那么想不开,采取了这种极端的办法。”汽车稳稳地停在了路边,“咱们下车看看吗。”顾一鸣征求意见似地看看贺红云。
“好吧,看看也好,备不住还能吸取什么教训呢。”
正像贺红云所说,一位落水的中年妇女被好心人救上岸来,一位先生摸样的人正在做着挤压腹内积水的动作。顾一鸣看到,十几米长的河坡有一溜长长的湿印,很明显,这位落水者是被人从河里拽上来的。旁边看热闹的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太可怜了,刚三十多岁就被对象踢出了家门。”
“谁说不是,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一个小三儿搅得一塌糊涂。”
“他那个对象简直就是畜生,整天不务正业,是活不干,跟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吃喝玩乐,醉醺醺回家还不算,到家后无休止的打骂使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她想一死了之,这不是上策,她应该站起来战胜小三儿,挽救自己的男人。”
顾一鸣缓慢地转过身儿低着头走向汽车。贺红云没有走的意思,她是想弄清事实真相。
一位大爷说了一句话使她浑身的肌肉都颤了起来:“这位大姐一看就是明白人,不会犯这方面的错误。我要是领导非下一道命令不可。”
“什么命令?”
“像这些男人舍近求远在外面搞小三儿,女人不甘寂寞寻求偷情刺激的,男的阉割女的杀。出现一个办一个,看他们还敢不敢偷腥盗情。”
贺红云没在说什么,她看了看这位大爷,又看了看渐渐散去的人们,按原路回到了汽车上。早已发动好汽车的顾一鸣看着满脸凝重的贺红云说:“教训深刻吗?”
贺红云坐在后座上,仰面看着车顶没说话。顾一鸣开着车没有再往下问。
“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呀。”
她恢复了原来的坐姿,并向顾一鸣提出一个他很难回答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吗?”顾一鸣用手指了指自己。
“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嗯,是这样,聪明一点儿的男女都不会让问题发展到跳河溺死的地步。”
“你聪明吗?”
“我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的家庭没有破裂,我和情人的关系该收收该放放,掌握得恰到好处。”
“还是那句话,我算看透了,你是真不要脸呀。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同学呢,我怎么上了你这条贼船呢?”
“后悔吗?”
“不是后悔,而是后悔至极。”
汽车停在了旅行社大门旁边的停车位上,贺红云整理了一下衣服,关好摇下来的车窗,从挎包中拿出镜子照了照。带着憔悴的容颜走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