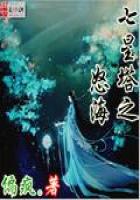因为我心怀鬼胎,程铮又有意试探,二人之间的交流就有了些鸡同鸭讲的味道。
他说两年前曾有人顶着程念筝的名字向正道传递消息,武林盟多亏于此才能顺利创建,我说墨潜等老一辈在新教主继位时已然随东方储而去,现下新一代领导班子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他说武林盟现下小有规模,再部署个一年半载便可举正道之力将魔教彻底根除,我说魔教这两年在中原的势力又有所增长,而且听讲东方储当年在中原还存了些家当没有见光,也不知道现下有没有落在东方厉的手上,若是有,可甚是麻烦。
他又说四年之期转眼将至,若谢如期还不来找他,他就杀上魔教,纵是豁出性命也要问个明白。
他说这话时语气淡淡,我却情不自禁一缩脖子,半晌方讪笑着冲他抛了个不伦不类的媚眼:“相公说什么胡话呢,我就在你身边,你还要找谁去?”
他看我一眼,半晌无声叹了一口气,道:“天色不早,睡吧。”
我眨眨眼睛:“睡哪?”
“卧房。”
“你床上,我地下?”
程铮看着我,突嘲讽一笑:“既是夫妻二人,自然应同床共枕的,再分床上地下,岂不生疏。”
嗷?!
同床共枕!
耳鬓厮磨!
情意绵绵时干柴烈火一下,做点害羞的事!
我那怀春少女的小心肝当即克制不住地狂跳一气,然而几乎是立刻又发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只得砸着嘴沮丧摇头:“我身怀剧毒,相公你与我同床共枕的话,不怕我毒死你么?”
他不置可否,攫住铁链拉起我走到房门口,伸手隔空一推,我便被他掌风送到了床边:“躺下。”
我扭头眼巴巴看着他:“我身上带毒,就算沾在床单上要不了命,你又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呢?要不然,我还是睡地上吧?”
他将之前绑我的那件深衣扔给我:“裹着。”
我条件反射地伸手接住,怔怔看他转身走到桌前坐下,铺开纸笔奋笔疾书,心下不由又是一阵怔忪。一忽儿有冲动拎着衣服披上他肩头,再顺势绕着他脖子索要一个吻,一忽儿又懊恼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与他重逢,本姑娘相貌欠奉,身怀剧毒,连趁他不查偷个香都是奢望。
思及此又是叹息连连。药何涣始终是魔教的人,即使他曾用唇语告诉我可以在四年之内散尽毒功,之后却从未和我说过具体的方法。我苦于装疯卖傻不能向他直白挑明,再加上朔望散的威胁一直比毒功要大,因此我一直不清楚散功的具体方法,只知道必定还要另吃一番苦头。
至于药先生?他连药人如何做都不清楚,又怎么会知道药人散功的方法?
一切都取决于药何涣愿不愿意帮我,我能不能活着回到魔教。
如若两者皆否,只愿我待在程铮身边的时间能够尽量长些。
我深深望着他背影,半晌才将他衣裳铺在床上,哗啦哗啦躺下,再将半扇衣服盖在身上,依旧侧头瞧着他。
程铮并不回头:“看什么?”
我一惊:“什么?”
他平平道:“你在看我,我感觉得到。”
我讪讪移开目光,半晌又理直气壮移回来:“都要同床共枕了,我先看看不行?”
他放下笔,将手上写的东西仔细叠好,放入抽屉落锁,转身向我道:“自然可以。”
他起身走到我身边,居高临下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亦抬眼回望他,然而一望进他深不见底的眸子,我心里的小兔子就蹦蹬蹦蹬跳个不停,只得先一步惶然垂眼望地。
程铮轻嗤一声,一手拉住我腕上锁链,一手搭住床沿轻飘飘翻到床尾盘腿坐好,双眼微阖,表情安然,似是就要这样睡过去一般。
我恍然:他当年带我去青阳山时不也是这样与我“同床”的么!如今时隔这么久,竟然又被雷声大雨点小的预告片忽悠了一通!
我气愤不已,心中大骂奸商虚假广告,骂了一会儿又忍不住开口问他:“你是一直这样睡觉,还是与别人有拼床的需求时才这样委屈自己?”老实交代,你有没有同别人同过床共过枕?
他闭着眼答我:“坐卧皆可。”又一拉我手上铁链,冷冷提醒道,“别想逃跑,此谷一入夜便遍山野狼,你身上气味陌生,根本不可能走出木屋十丈之外。”
我干笑一声:“多谢提醒。”
想了想又连珠炮似的问他:“这谷中这么多野狼,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你将它们引过来的?这谷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说过逐风山庄附近有这样的地方?”我在魔教当然没听说过,但我在药王谷时也从没听向大哥说过,这可就有些奇怪了。
程铮缓缓道:“此谷原本就有狼群出没,我在此建屋饲狼之后,附近的野狼便都依附了过来,轮流在此过夜。——此处并非在逐风山庄附近,你偷袭我和向靖声已是三日前的事了。”
我一惊:“三天?!我们走了多远?这是在哪?”
程铮微微蹙眉:“告诉了你,难道叫你通知你那些同伙么?”
我不觉无趣,喃喃解释道:“我不过是随口问一句罢了,你便是告诉我个名字,我又能知道在哪儿?”
程铮沉默一会,淡淡道:“没名字,在我之前,这里就称作无名谷。”
我笑:“无名谷太普通了些,你既是在此隐居,总要起个拉风的名字镇宅。——你这谷中蓄了这么多狼,恐怕被当地人直接叫做恶狼谷了,可是你是正道侠士,隐居的地方加个恶字,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依我看,不如叫做止啼谷好一些,群狼止小儿夜啼,也可理解为此处不闻鸟鸣,说着倒也含蓄。”
他半晌不答我。
我以为他睡了,刚要翻身合眼,却听他低声道:“睡吧。”
顿了片刻,又用口型道,睡吧,如期。
我不觉又是胸口微酸,忙在心中亦回他一句少爷晚安,说完之后又怨他:你连我身份都不确定,便这样大大方方地让我睡在身边了?你是当真不拘小节还是无爱无恨,所以全无所谓啊!
想到这儿不由狠狠瞪他一眼,拽着链子猛地翻了个身,气鼓鼓地背着他睡了。
再醒来已是天光大亮,我环视一圈,见程铮并不在房内,不由疑惑地起身下地,在屋中走了一圈之后听见门外剑气声声,甫推开木门便被白花花的剑芒晃瞎了狗眼。
我了个去,少侠您是要立志成为剑圣啊?
我索性拖着锁链在门槛上坐下,眯眼看程铮练剑,越看心里越痒。
这小腰!
这长腿!
这动作!
这身段!
看武林高手练剑是一种无上的享受,他一招一式即使拆分成单个的定格动作都极具力量和美感,更何况我家程铮不光动作漂亮,人更是帅得没边,看那回眸转身时不经意的风情,哪还用得着什么干柴烈火掌情意绵绵刀?
太特么考验我定力了。
我痴痴地看着他,不觉看到一套剑法已近尾声,看程铮高高跃起,于半空中旋身抖腕挽了个剑花,突然一抬手向我刺来。
我大惊失色,连忙震臂抖腕,用手上锁链当做九节鞭格挡住他袭击,另一手一拍地上,整个人当即向右平侧了几尺。
程铮一笑,招式未老便旋身收势,跃回原地收剑入鞘,向我伸手道:“锁链。”
我无奈,只得一抖手腕将锁链交至他手上,低着头嘟嘟哝哝:“牵狗也没有让狗主动提供锁链的啊。”
程铮侧眼看我:“狗不会逃。”
我被他憋得没脾气,只得恨恨转头不理,任他牵着我走到后院。
后院角落里堆着两只血淋淋的、皮毛被磨得掉了大半的肥羊,肥羊脖子上赫然各有一处齿痕,应该是狼群进贡来的猎物。另有一匹白马温顺地站在院子一角,身形比程铮之前骑的那匹飞雪略小些,大概是飞雪的下一代了。它背上驮了只鼓鼓的皮囊,似是刚到,鼻子里还在呼呼向外喷着热气。
程铮扔下锁链,将白马背上的皮口袋拖到地上打开,从里头取出个布包来交给我:“你的衣裳。”
我愣愣接过打开,却见里头是几件极鲜亮的襦裙和褙子,顶上头一件是桃红色的,看着就十分有少女范儿。
我连碰都不敢碰就又交还给了他:“我身上带毒,不能穿鲜亮的衣裳,会发黑。”
这是真的。别的功夫都是将内力好好地存于丹田,平时并不动用。药人所练的毒功却因其毒性巨大,而非得时时运功,将毒气不断游走于身周、发于体表,这才能最大减少对内脏的伤害。
也正因于此,药人的皮肤才隐隐泛青,发丝血液莫不带毒。
程铮沉下脸来:“里面还有中衣,布料厚实,能挡得住你身上毒气。”
我喃喃:“我穿原来的衣裳不是挺好?”虽然低调朴素了点吧,但也没什么不对嘛。
一张脸都已经整得跟车祸现场似的了,再穿得桃红柳绿的才奇怪吧。
他看我一眼,突然一扯铁链将我拉到近前,盯着我淡淡道:“你不想换衣裳,是因为身上有什么东西藏着?”
我无奈:“我换就是了。”接过衣服走了几步,又转头看他,“我还扣着脚镣手铐呢,换不了啊。”
他看我一眼,从怀中掏出手套戴上,俯身替我解了铁链,却跟着我进了房,用帕子将自己眼睛蒙上:“我不看你,但你也逃不了。”
我苦笑一声:“是,我知道您功夫高强,耳力惊人。”
他沉默着伸脚勾住椅子坐下。我伸手在他眼前摇了摇,便大大方方地转身换衣裳,换好之后却也不急着叫他,而是蹑手蹑脚地走到他面前,缓缓躬身,在他前面约一寸的地方隔空印下一吻,做完这动作也觉得自己矫情,赶紧踮着脚尖退后几步,清清嗓子叫他:“好了。”
程铮扯下帕子看我,眼神复杂,不辨喜怒。
我笑问:“是不是挺不般配的?——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帕子借我用用。”
他将帕子递给我,我伸手接过盖在头上,遮住自己脸面,又问他:“是不是这样就好多了?”说着就要抬手扯下来。
他却突然几步走到我面前,按住我手,哑声唤我:“如期……”
我一愣,旋即又大大方方笑道:“我说什么来着,遮住脸就像了嘛。你要是看着我有压力,我可以天天这么遮着。”
他一怔,继而又扯下帕子,捡起我换下的衣裳大步走进厨房,将旧衣全部填入灶膛,一把火引燃了。
我亦步亦趋地跟到他身边,与他并排蹲着:“生气了?你要是不喜欢我提,我以后不说我是你媳妇就是了。谢如期还在魔教好好待着,我全是骗你玩的,你们的四年之约还有效,再有不到一年时间,你就能看到她了。”
他突然长叹一口气,轻声道:“你是不是谢如期,我自有主张;你究竟为什么要骗我,我也大概能猜到几分。你不想和我待在一处,我自然能感觉得到。然而就算你有千般不愿,为了大局着想,我也必须强留住你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你说什么都是白搭,不如就顺其自然,别再想说服我什么。若我有什么需要问你的,我自会开口,却不必你来提醒。武林中的事是如此,如期的事也是如此。”
他望进我眼底:“在这一个月里,我不会将你当成任何人,你也不必真真假假地骗我。你身怀毒功,自然也不用担心我占了你什么便宜。只要你不想着逃走,我自会好好待你,不伤你分毫。待尘埃落定之后,我会亲自送你出谷,一路护送你去任何地方。”
我沉默一会,终于轻笑道:“好哇。”顿了顿又补充,“你这么漂亮,我要不是身怀毒功,其实是很想你占我什么便宜的。”
心里却满是问号:少爷,你平常都是这么对待异性的?
这么暧昧?
哼!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