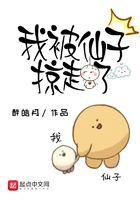“不必了!”基督山一面说,一面收起那五张支票,“这样就不必了,这种事情是这样的稀奇,我要亲自去体验一下。我预定在您这儿提六百万。我已经提用了九十万法郎,所以您还得支付我五百一十万法郎,就给我这五张纸片吧,只要有您的签字我就相信了,这是一张我想用的六百万的收条。这张纸条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因为我今天急需钱用。”
说着,基督山一手把五张纸片放进衣袋,一手把收据递给银行家。
即使一个霹雳落到那位银行家的脚前,他也未必会这样惊恐万状。
“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您的意思是现在要提钱吗?对不起,对不起!但这笔钱是我欠济贫院的,——是我答应在今天早晨付出的一笔存款。”
“噢,嗯,那好!”基督山说,“并不是一定要这几张支票,换一种方式付钱给我吧。我拿这几张支票是因为好奇,希望我可以对人家说:唐格拉尔银行不用准备就可以当时付给我五百万。那一定会使人家惊奇。这几张支票还给您,另外开几张给我吧。”
说着,他把那五张票据递给唐格拉尔,唐格拉尔脸色铁青地伸出手来,就像秃鹫隔着铁笼伸出爪子来抓别人从它那儿夺去的肉似的。
但他突然停住手,竭力控制住他自己,然后,在他那失态的面孔上渐渐露出了微笑。
“当然啰,”他说,“您的收条就是钱。”
“噢,是的。假如您在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就会像您刚才那样不必太麻烦地付款给您。”
“原谅我,伯爵,原谅我。”
“那我现在可以收下这笔钱了?”
“是的,”唐格拉尔一边说,一边揩着从头发根里往下淌的汗珠,“请收下,请收下。”
基督山把那几张支票重新放回到他的口袋里,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情,像是在说:“好好,想一想,假如您反悔,现在还来得及。”
“不,”唐格拉尔说,“不。绝对不,收了我签的支票吧。您知道,银行家是办事最讲究形式的人。我本来是准备把这笔钱付给济贫院的,所以我一时头脑糊涂,认为假如不用这几张支票来付钱,就像被抢了钱似的!——就好像这块钱没有那块钱好似的!原谅我。”
然后他开始高声笑起来,但那种笑声总掩饰不了他的心慌。
“我当然可以原谅您,”基督山宽宏大量地说,“那我收起来了。”
于是他把支票放进他的皮夹里。
“不过,”唐格拉尔说,“我们还欠十万法郎的尾数没结清呢”。
“噢,小事一桩!”基督山说,“差额大概是那个数目,但不必付了,我们两清了。”
“伯爵,”唐格拉尔说,“您此话当真吗?”
“我是从来不和银行家开玩笑的。”基督山用冷冰冰的口气说,他老是用这种态度来止住他人的鲁莽,然后他转向了门口。
而在这时,跟班进来通报说:“济贫院出纳主任鲍维尔先生前来拜访。”
“哎呀!”基督山说,“我来得正好,刚好拿到您的支票,不然他们就要和我争执了。”
唐格拉尔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赶紧跟伯爵告别。
基督山伯爵向站在候见室里的鲍维尔先生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基督山一走,鲍维尔先生便立刻被引入唐格拉尔的书房。
看到济贫院出纳主任手拿皮包,伯爵那非常严肃的脸庞上闪过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
他在门口登上他的马车,立刻向银行驶去。
这时,唐格拉尔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走上去迎接那位出纳主任。
不用说,他的脸上当然挂着一个殷勤的微笑。
“您好,我亲爱的债主,”他说,“我今天料到一定是债主登门了。”
“您说对了,男爵,”鲍维尔问先生说,“本人是代表济贫院来见您的,寡妇孤儿们委托我到您这儿来,要您付清那五百万社会救济款。”
“人们都说孤儿是应该同情的,”唐格拉尔故意打趣地说,“可怜的孩子们呀!”
“所以说我是以他们的名义前来见您的,”鲍维尔先生说,“您也许收到我昨天的信了吧?”
“是的。”
“今天我把收据带来了。”
“我亲爱的鲍维尔先生,”唐格拉尔说,“如果您愿意,请你们的孤儿寡妇再等上二十四个小时,因为基督山先生,就是您刚才看见从这儿出去的那一位,您看见了,不是吗?”
“是呀,怎么啦?”
“嗯,基督山先生刚才把他们的五百万带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伯爵在我这儿有一个可以无限提款的户头,是罗马的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开的。他刚才来,要在我这里一次提款五百万;我给他开了法兰西银行的凭票:我的资金都存放在这家银行里;而您明白,我怕在同一天里向银行理事先生支取一千万,会使他觉得很奇怪的。”
“如果能分两天提,”唐格拉尔微笑着说,“那就不同了。”
“哦,”鲍维尔用一种不信任的口气说,“那位刚才离开的先生已经提去了五百万!他还对我鞠躬,像是我认识他似的。”
“虽然您不认识他,或许他认识您,基督山先生的社交非常广泛。”
“五百万!”
“这是他的收据。请您像圣多马《圣经》故事中耶稣十二信徒之一。据《新约·约翰福音》,耶稣复活后,他先不相信。直到看见耶稣身上的钉痕并用手探入耶稣肋旁,才相信耶稣复活。一样,验看一下吧。”
鲍维尔先生接过唐格拉尔递给他的那张纸条,念道:
兹收到唐格拉尔男爵先生五百一十万法郎,此笔款项他可随时向罗马的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支取。
“的确是真的!”出纳主任说。
“您一定知道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吗?”
“知道,”鲍维尔先生说,“我曾和该银行有过一次二十万法郎的业务往来,但此后再没有听到有人说过它。”
“那是欧洲最有信誉的银行之一。”唐格拉尔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将鲍维尔先生手里拿回的收据扔到他的写字台上。
“他仅从您手里就拿了五百万?哦!这位基督山伯爵一定是个大阔佬啰!”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但他有三封无限提款的委托书,——一封给我,一封给罗斯希尔德,一封给拉斐特。而您看,”他漫不经心地又说,“他把优惠权给了我,并且留下十万法郎给我做手续费用。”
鲍维尔先生用十分钦佩的神情。
“我要去拜访他一次,”他说,“我得请他为我们捐些款。”
“哦!这您是十拿九稳的;他每月光花在施舍上的钱就不止两万法郎。”
“那太好了;另外,我还要向他引用一下德·莫尔塞夫夫人和她儿子的例子。”
“什么事例?”
“他们把全部财产捐给了济贫院。”
“什么财产?”
“他们的财产,也就是已故的莫尔塞夫将军的财产呗。”
“什么理由?”
“因为他们不想接受一份不光彩的家产。”
“那么他们靠什么为生呢?”
“母亲隐居在乡下,儿子去参军。”
“嗯,我已经必须承认,这些都是造孽钱。”
“我昨天把他们的赠契登记好了。”
“他们有多少?”
“噢,数目不大,一百二三十万法郎左右。现在再谈论我们的那五百万吧。”
“听您的,”唐格拉尔油腔滑调地说,“那么,您很着急要这笔钱?”
“是的,明天我们要查账。”
“明天,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明天!这等于过了一百年!几点钟开始查账?”
“两点钟。”
“十二点钟送去。”唐格拉尔微笑着说。
鲍维尔先生不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拿起那只皮包。
“现在我想起来了,您可以有更好的办法。”唐格拉尔说。
“怎么说?”
“基督山先生的收据等于是钱,您拿它到罗斯希尔德或拉斐特的银行里去,他们立刻可以给您兑现。”
“什么,在罗马付款的单据都能兑现。”
“当然啰,只收您付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六的利息就得了。”
那位出纳主任吓得倒退一步。
“馊主意!不,我宁愿等到明天!您真想得出来!”
“请原谅!”唐格拉尔带着犯了大过错似的口气说,“我本以为您有亏损补贴呢?”
“啊!”那出纳主任叫了一声。
“请听我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是这样,就要做点牺牲了。”
“感谢上帝,没有!”鲍维尔先生说。
“那明天见,是不是,我亲爱的出纳主任?”
“是的,明天见,但不得有误!”
“啊!您在开玩笑!明天十二点派人来,我会事先通知银行的。”
“我将亲自来。”
“那更好,因为又给我有幸见到您的机会。”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
“顺便问问,”鲍维尔先生说,“您不去出席那位可怜的维尔福小姐的葬礼吗?我在大街上看到了。”
“不,”那银行家说,“自从闹了贝尼代托事件以来,到现在我还丢人现眼的,我不得不深居简出了!”
“嗨!您弄错了!在整个事件中,您有什么错?”
“听我说,我亲爱的出纳主任,当人们有了像我这样没有污点的名誉时,有些人就起了疑心了。”
“大家都会同情您,请您相信这一点,而且尤其同情唐格拉尔小姐!”
“可怜的欧仁妮!”唐格拉尔长叹一声,“您知道她要进修道院吗,先生?”
“不知道。”
“唉!这件事很不幸,但却是真的。事发第二天,她就带着一个她所认识的修女离开了巴黎。她们已到意大利或西班牙去寻找一座教规非常正格的修道院去了。”
“噢!太可怕了!”
鲍维尔先生带着这种表示同情的感叹后,又向这位父亲说了几句宽心的话,然后告辞了。
这位出纳主任跨出门还没走多远,唐格拉尔便做了一个极富有表情的姿态,喊道:“傻瓜!”那有力的举动和姿势,只有看过弗雷德里克扮演的罗贝尔·马凯尔1834年首演的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海盗出身,但一直以银行家的身份混迹上层社会。该剧剧本系法国剧作家邦雅曼·昂蒂埃(1787—1870)等三人所作。的人才能知其奥妙。
然后,他一边将基督山的收据塞进一个小皮夹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十二点来吧,十二点,我早就脚底抹油啰。”
接着,他把房门上了两道锁,倒完保险柜所有的抽屉,集中了五十张左右一千法郎面额的现钞,烧毁了一些文件,又摆上一批放在显眼处,然后写了一封信,签上名,封好口,信封上写着“唐格拉尔男爵夫人启”。
“今天晚上,”他喃喃自语,“我要亲自把这封信放在她的梳妆台上。”
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护照。
“好!”他说,“还有两个月的有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