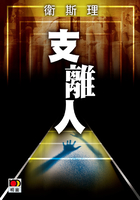“这时,”波尚继续说,“我趁无人和黑暗,安全地走出了大厅。原先领我进去的那个听差的,正在门口等着我呢。他带着我,穿过走廊,最后一直来到一座通向沃吉拉尔大街的小门。我是带着一种悲喜参半的心情离开的,请原谅我这样说,阿尔贝,悲是为了您,喜的是那位姑娘决心为父报仇的高尚情操。是的,我向您打保票,阿尔贝,揭露的那个事实无论来自哪个渠道,我认为,这可能出自一个仇敌,但这个仇敌只能是上帝的使者。”
阿尔贝双手抱头;然后又抬起他那羞得通红的、流满泪水的脸,紧紧地抓住波尚的手臂。
“我的朋友,”他说,“我的生命完了,对着您我不想说,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而是要找到究竟是什么人跟我这样过不去;要是被我发现了,不是我干掉他就是他干掉我;所以,我全仗您的交情帮助我,波尚,假如您在心中还没有瞧不起我的话。”
“瞧不起?这是朋友说的话?这个不幸同您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感谢上帝,子承父过的不公正时代已经过去了。重新生活吧,阿尔贝;它好像刚刚开始,真的,即便是个朗日的黎明,难道比您的珍珠光泽更纯洁?不,阿尔贝,相信我,您还年轻,您又有钱,离开法国吧!在那伟大的巴比伦,在那动荡的生活和改变口味的国度里,一切都很快会被忘却;过三四年后您再回国来,还娶了位俄国公主当做新娘,到那时,谁也不会再想昨天发生的事情,那么推而广之还有谁再推翻十六年前的那些老账呢!”
“谢谢您,我亲爱的波尚,谢谢您那想使我放弃这种念头的好意,但我是不能这样做的。我已经把我的打算告诉您了,假如有可能的话,好,也可以说那就是我的决心。您知道,以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而论,我不能采取与您一样的态度。在您看来纯粹是天意的事情,在我看来却远没有那样简单。我觉得上帝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也幸亏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我这一个月来所忍受的痛苦,才能不以那摸不到看不见的惩恶天使为对象,而可以向一个既摸得到又看得见的人去寻求报复。现在,我再说一遍,波尚,我愿意回到人和物质的世界,而假如您还像您说的我们还是朋友的话,就帮助我来找出那只击出拳的手吧!
“那好吧!”波尚说,“假如您坚持要我立足大地,我就下到人间,假如您坚持要我帮您寻找仇敌,我就来帮助您,而且我 一定会找到的,因为我的荣誉和您的荣誉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上几乎不可分割。”
“嗯,那好,您知道,波尚,我们立刻开始搜索吧。每一瞬间的推迟在我来说都像很长的时间。那个诽谤者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惩罚,他或许希望他可以不受惩罚。但是,以我的名誉担保,假如他那样想的话,他就在欺骗他自己了。”
“好吧,听我说,莫尔塞夫。”
“啊,波尚,我看您已经明白这一点了,您恢复了我的生命。”
“我并没有说事情真是那样,但它至少是黑夜中的一道光芒,沿着这道光芒,我们或许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告诉我吧,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嗯,我把我从雅尼那回来的时候设想对您说的那件事告诉您。”
“说吧。”
“我到了那里,当然先到当地的大银行家那儿去调查。一开始,甚至我还没有提及您父亲的名字,他就说:‘啊,我猜道您为什么来的了。’
“‘怎么猜到的呢?’
“‘因为两星期以前,也有人来问我这同样的问题。’
“‘谁?’
“‘巴黎的一个银行家,我的业务伙伴。’他的名字是……’
“‘唐格拉尔。’”
“是他!”阿尔贝大叫道,“果然是他,原来他早就对我可怜的父亲怀恨在心了。这个自称与世无争的家伙,连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莫尔塞夫伯爵都不放过。喏,再加上这次婚姻又是毫无理由破裂,对,正是为了这个。”
“您去调查一下,阿尔贝,但不要事先发火,听我说,去调查一下,看看事情是否真实……”
“噢,是的,假如是确有其事,”那年轻人喊道,“他就要偿还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
“要小心,莫尔塞夫,他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
“我尊敬他的年龄就像他尊敬我的家庭一样。假如他恨我的父亲,他为什么不打死我父亲呢?噢,他是怕跟一个人当面作对的。”
“我并不是在责备您,阿尔贝,我只是要跟您说不要感情用事,要慎重一些。”
“噢,不用怕,而且,您要陪我去的,波尚。严肃的事情应该当着证人来做的。今天,假如唐格拉尔先生是有罪的,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嘿!波尚,我将以一次庄严的葬礼来维护我的名誉。”
“既然您已下了这样的决心,阿尔贝,那就应该立刻去执行。您想立即到唐格拉尔先生那儿去吗?我们走吧。”
波尚差人去叫来了一辆出租轻便马车。驶到银行家府邸跟前时,只见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的四轮敞篷马车和仆人在门口。
“啊,太好了!很好,”阿尔贝用一种阴郁的口吻说。“假如唐格拉尔先生不和我决斗,我就杀死他的女婿,他应该是愿意决斗的,——一个卡瓦尔康蒂!”
仆人去向银行家通报年轻人来访,唐格拉尔已经知道昨晚的事情,所以一听到阿尔贝的名字,连忙吩咐挡驾。但是已经晚了,阿尔贝本来跟在那个仆人后面,听到唐格拉尔这样吩咐,就带着波尚推开门,径直闯到银行家的书房里。
“先生,”那银行家喊道,“难道我没有权力在我的家里拒绝不想接见的人了吗?您看来是忘乎所以了。”
“不,先生,”阿尔贝冷冷地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是由于懦怯,这是我给您的托词,一个人就不能拒绝接见某些人。”
“那么,您对我有什么要求呢,先生?”
“我要求,”阿尔贝一面说,一面走近他,似乎并未注意到那背着壁炉站着的卡瓦尔康蒂,“我要求让我们在一个没有人来打扰的地方交谈十分钟,我对您只有这一点要求,仇人相遇,必定是一死一生。”
唐格拉尔脸色变得煞白,卡瓦尔康蒂往前挪了一步。阿尔贝转身朝那个年轻人走过去。
“还有您,”他说,“假如您高兴的话,您也来吧,子爵先生,您也有资格这样,因为您几乎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了,只要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约会,多约几个也无妨。”
卡瓦尔康蒂带着一种愕然的神情望着唐格拉尔,唐格拉尔竭力振作了一下,站起来走到那两个年轻人的中间。阿尔贝对安德烈的攻击使他有了一种不同的立场,他希望这次拜访别有缘故,不是他最初所假定的那个原因。
“啊,先生,”他对阿尔贝说,“如果您来向这位先生找碴;因为我喜欢他而不喜欢您,那我倒要告诉您,我将让检察官来断这个案。”
“您弄错了,先生,”莫尔塞夫带着一个阴郁的微笑说,“这与婚事毫无关系,我所以要对卡瓦尔康蒂先生那样说,是因为他刚才似乎要来干涉我们的企图。在一方面,您说对了,我今天准备要跟每一个人吵架,但您有优先权,唐格拉尔先生。”
“先生,”唐格拉尔回答说,他又气又怕,脸色惨白,“我警告您,要是我交了晦气,在街上碰上一条疯狗,我就会宰了它,而且我会觉得这是为社会做了桩好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过错。所以,要是您也疯了,而且张牙舞爪地想来咬我,那我可有言在先,我会毫不手软地宰了您。喂!您的父亲丢脸献丑,难道是我,是我的过错吗?”
“是的,你这卑鄙的家伙!”莫尔塞夫喊道,“就是你的错。”
唐格拉尔后退了一步。“我的错!”他说,“您一定疯了!我怎么知道希腊的历史?我到那些国家去旅行了吗?是我劝告您的父亲出卖雅尼那堡,背叛——”
“住口!”阿尔贝用一种窒息的声音说,“不,您并没有直接揭露这件事情,并没有直接来伤害我们,但这件事情是您暗中唆使的。”
“我?”
“是的,您!那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咦,我想报纸已经告诉您了,当然是从雅尼那儿来的!”
“谁写信到雅尼那去的?”
“写信到雅尼那?”
“是的。是谁写信去打听关于我父亲的消息的?”
“我想谁都可以写信到雅尼那去的吧。”
“但只有一个人写了那封信!”
“只有一个人?”
“是的,而那个人就是您!”
“我写了,当然要写的;我觉得,一个当父亲的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青年,他可以调查有关这位青年的家庭情况,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责任。”
“您清楚地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所以您才写了这封信”阿尔贝说。
“我知道?啊!我向您发誓,”唐格拉尔带着一种自信心和安全感的神色大声嚷道,这种自信心和安全感的产生,或许并非出自惧怕,而是来自对这位不幸的青年从内心感受的关切,“我向您发誓,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向雅尼那写信。我哪里知道阿里总督的遇难情况?”
“那肯定是有人煽动您写的了?”
“是的。”
“那个人是谁?说说呀……”
“啊!这事很简单。我谈到您父亲的过去。我说,他的财产由来还不大清楚。那个人就问我,您父亲的财产是哪儿弄来的?我回答说:在希腊呗。他就对我说:‘好呀!写信到雅尼那去就是了。’”
“劝您的那个人是谁?”
“不是别人,就是您的朋友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叫您写信到雅尼那去的?”
“是的,于是我就写了,假如您高兴的话我可以把回信给您看。”
阿尔贝和波尚对望了一眼。“先生,”波尚说,“您似乎在指责伯爵,而您知道伯爵此刻不在巴黎,无法为他自己辩护。”
“我没有指责任何人,先生,”唐格拉尔说,“我只是实话实说,即使在伯爵面前。”
“伯爵知道回信的内容吗?”
“知道,我给他看过回信。”
“他知道我父亲的教名叫费尔南,姓蒙代戈吗?”
“是的,我早就告诉过他了;除此之外,我所做的每桩事情,换了别人在我的处境,也是一样会做的,说不定还比我做得多些呢。我收到回信的第二天,您父亲在基督山先生的怂恿下,正式来为您提亲,这时,我就来个快刀斩乱麻,拒绝了他,我拒绝得很干脆,这没错,但我既没作任何解释,也没揭他的老底。其实,我又何苦去揭他的老底呢?德·莫尔塞夫先生是露脸还是丢脸,管我什么事?我既不会因此多赚些钱,也不会就少赚些。”
阿尔贝觉得自己连额头都涨红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唐格拉尔卑鄙地为自己辩解,但说话的神气却不像在为自己辩解,好像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他的吐露真情并不是由于良心发现而多半是由于害怕的缘故。但莫尔塞夫不是要证实唐格拉尔和基督山谁的罪大;而是要寻求一个肯答复侮辱的人,一个肯和自己决斗的人,而唐格拉尔显然是不肯决斗的。
这时,以前那些被他遗忘或没有察觉的事情,现在每一件重新变得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基督山伯爵既然能赎回阿里·帕夏总督的女儿,他当然无所不知;而正因为她无所不知,所以他才怂恿唐格拉尔写信到雅尼那。一知道答案,他便同意满足阿尔贝求见海黛的愿望;一到海黛面前,他任凭海黛放言阿里之死,对海黛娓娓长谈毫无阻拦之意;而他又不时地见机说上几句现代希腊语,无疑是授意姑娘不让莫尔塞夫知道她的父亲;此外,事先他不也是请求莫尔塞夫在海黛面前不要说出他父亲的名字吗?最后,在他得知一场大揭发必然发生之时,他又领着阿尔贝去了诺曼底。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当然也毫无疑问,基督山和他父亲的仇敌沆瀣一气。
阿尔贝把波尚拉到一边,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
“您说得有理,”波尚说,“唐格拉尔先生在这件事情上只是做得鲁莽俗气一些,而这位基督山先生,您倒是应该要求他解释清楚。”
阿尔贝转过身来。
“先生,”他对唐格拉尔说,“您得明白,尽管我现在告辞了,可事情并没算完;我还得弄清楚您的推诿是不是成立;我这就到基督山伯爵先生的府上去把事情弄个明白。”
说着,他朝银行家躬了躬身,带着波尚就往外走,对卡瓦尔康蒂就只当没他这个人似的。
唐格拉尔一直陪他们到大门口,到了大门口,又对阿尔贝再三申明他对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并无个人恩怨,所以是不会想去得罪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