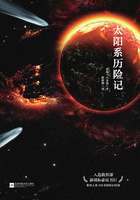弗朗兹走出诺瓦蒂埃先生房间时的那种脚步和神色,连瓦朗蒂娜砍了也心中不忍。
维尔福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就回到他自己的书房,大约过了两小时,他收到下面的这封信:
鉴于今晨揭露的情况,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已断无同意其家族与弗朗兹·德·埃皮奈先生家族联姻之可能。德·维尔福先生对今晨所述之事看来早已知悉,而竟未及时知照,弗朗兹·德·埃皮奈先生对此不胜惊骇之至。
如果此时有人看见这位法官大人,见到他被搞得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就会相信维尔福没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结局。的确,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竟会把多年前的事情在此时此刻坦白或冒失地公布出来。说句公道话,维尔福一直相信盖斯内尔将军或埃皮奈男爵——这两种称呼都有人用,那个说话的人愿意称呼他的家名或者称呼他的爵衔而定——是被人暗杀掉的而不是在一场公平的决斗中被对手杀死的;因为无论做什么事情,诺瓦蒂埃先生都从来不顾及儿子的意见,决斗的事情,维尔福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对维尔福来说,这封措辞严厉的信使他的自尊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写这封信的人从来都是如此之温文尔雅。
他的妻子在他刚回书房不久就进来了。
弗朗兹在诺瓦蒂埃先生召见之后的不辞而别使每一个人都非常吃惊,维尔福夫人一个人和公证人以见证人在一起,她此时愈来愈觉着迷惑不解。她再也忍受不了,便起身离开,说她要去问问理由。
维尔福先生对这件事只是说诺瓦蒂埃先生向埃皮奈先生和他做了一番解释,瓦朗蒂娜和弗朗兹的婚姻即将因此破裂了。
这个消息,对等在客厅里的那些人是难于启齿的;所以德·维尔福夫人回到客厅时,只说是诺瓦蒂埃先生在谈话开始时突然发病,因而婚约自然只得推迟几天再签署了。
这个消息虽然是编造的,但是紧跟着那两件同样的不幸事件之后宣布出来的,显然把听的人惊呆了,他们一言不发地告退了。
这当儿,又惊又喜的瓦朗蒂娜拥抱了羸弱的老人,感谢他一举击碎了她已经以为无望挣断的锁链,随后就表示她想回自己房间去稍作休息,诺瓦蒂埃用目光答允了她的请求。
但瓦朗蒂娜一旦获得自由,却并没有回到她自己的屋里去,她转进一条走廊里,打开走廊一头的一扇小门,马上就到了花园里。在这种种接连来到的怪事发生的过程中,瓦朗蒂娜的脑子里老是存有一个极为不安的念头。她感觉莫雷尔随时都能带着苍白的脸色和颤抖的身子出现,来阻止婚约的签订,像《拉马摩尔的新娘》一书中的莱文斯乌德爵士一样。
瓦朗蒂娜此时的确也应该到后门口去一下了。马克西米利安看到弗朗兹和维尔福先生一起离开了坟场,就已经料到了他们的心境。他跟着埃皮奈先生,见他进去,出来,然后又带着阿尔贝和夏多·雷诺进去。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他急忙赶到他的菜园里去等候消息——因为瓦朗蒂娜一有脱身的机会,一定就会赶来见他。
他一点也没猜错;他一只眼睛贴着木板,真的看到姑娘露面了,她丝毫没有往常的拘谨,大步流星地向栅栏墙走来。他看了第一眼,心里就踏实了;他听了她的第一句话,高兴得跳起来。
“我们得救啦!”瓦朗蒂娜说。
“得救!”莫雷尔跟着说了一句,他不能相信会有如此幸运,“谁救了我们?”
“我的祖父救了我们。噢,莫雷尔!好好地爱他吧。”
莫雷尔发誓要用全部的灵魂去爱他。他做这个誓言毫不勉强,因为他此时觉着爱诺瓦蒂埃超过了朋友和父亲——他把他崇拜得如同一位天神。
“这一切是怎样成功的?”莫雷尔问道,“他施展了什么奇特的手法?”
瓦朗蒂娜正想把一切经过讲出来,但忽然又意识到,如果那么做,就必须泄露一个可怕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不但牵连到别人,而且也牵涉到她的祖父,于是她就说:“这件事我将来可以原原本本地跟您说。”
“可那得什么时候呢?”
“在我成为您的妻子以后。”
这是莫雷尔最心爱的话题,一提到这茬儿,莫雷尔就什么都肯答应:所以,他甚至答应说,一天工夫就知道这么些事情,确是够多的了,对此他应该满足。但他坚持非要瓦朗蒂娜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再跟他会面,然后才肯离去。
瓦朗蒂娜答应丁莫雷尔向她提出的一切要求了,一小时以前,如果有人对她说她可以不嫁给弗朗兹,实在感到难以相信,但现在如果有人向她说她可以和马克西米利安结婚,她自然就不会那么觉着相信了。
在刚才描写过的那场会见进行的过程中,维尔福夫人已去拜访过了诺瓦蒂埃先生。老人像往常见到她的时候一样,用严厉和厌恶的神情看着她。
“先生,”她说,“瓦朗蒂娜的婚事已经无可挽回了,我跟您说这个是多余的,因为破裂就发生在这儿。”
诺瓦蒂埃依然毫不动色。
“但我可以跟您说一件事情,这件事儿我想您也许还不知道。就是,对于这门亲事,我从来都是反对的,最初而谈这项婚约的时候,根本没有得到过我的同意或赞许。”
诺瓦蒂埃用一种希望对方解释的目光望着他的儿媳妇。
“我知道您非常讨厌这门亲事,现在它已经完结了,我来向您提出一个维尔福先生或瓦朗蒂娜不好提出的请求。”
诺瓦蒂埃的眼光问那个请求是什么。
“我来请求您,先生,”维尔福夫人继续说,“作为唯一有权利的人来请求您,因为唯有我不会从中受益;我来请求您把您的财产归还给您的孙女吧,我也不说什么宠爱了,因为她一直是您的掌上明珠呀。”
诺瓦蒂埃的目光一时很迷茫:他显然在探寻这种请求的动机是什么,但没有能奏效。
“先生,”维尔福夫人说,“我可以希望您符合我的要求吗?”
诺瓦蒂埃表示可以。
“那么,先生,”维尔福夫人又说,“我就告退了,我此时很感激,也很快活。”
她向诺瓦蒂埃先生鞠躬告退。
第二天,诺瓦蒂埃先生派人去请公证人:把以前的那张遗嘱销毁,重新另立一份,在那份遗嘱里,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遗赠给了瓦朗蒂娜,条件是她永远不能离开他。
于是大家都传说:维尔福小姐本来就是圣·梅朗侯爵夫妇的继承人,现在又获得了她祖父的欢心,将来每年可以得到一笔三十万里弗尔的收入。
与维尔福先生家里解除婚约的同时,基督山已去拜访过一次莫尔塞夫伯爵;然后,莫尔塞夫伯爵为了表示他对唐格拉尔的尊敬,他穿上了中将制服,挂上了他的全部勋章,这样打扮好以后,就吩咐人备上他最健壮的马匹,赶到昂坦堤道街。唐格拉尔正核算他的月帐,如果有人想在他高兴的时候去找他,现在恰好不是最好的时机。
一看到他的老朋友,唐格拉尔就做出他那种庄重的神气,四平八稳地在他的安乐椅里摆好架子。
莫尔塞夫一贯拘板,可这一次他一反常态,笑容可掬,态度和蔼,因为她大概以为,他这样的开局表现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接待。所以他也就免去了一切外交礼仪,开门见山地进入本题:
“嗯,男爵,”他说,“我来了,许久以来,我们总在说过的话上兜圈子……”
莫尔塞夫以为对方那种冷淡的态度是因为他自己不开口造成的,而现在他说了这句话,银行家的面孔一定会放松起来;然而恰好相反,让他大感惊奇的是,那张面孔竟然更加严肃无情了。
“我们说过什么样的话,伯爵先生?”唐格拉尔煞有介事地问,似乎他对将军想要说的话百思不解。
“啊!”莫尔塞夫说,“看来您是一个很讲究形式的人,我亲爱的先生,您提醒我不应该免除古板的仪式。我请您原谅,但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又是我生平第一次打算给他娶亲,所以我还是个学徒的生手,好吧,我愿意加以改进。”
于是,莫尔塞夫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站起身来,向唐格拉尔深深地鞠躬,说:
“男爵先生,我很荣幸地为我儿子阿尔贝·莫尔塞夫子爵来向您请求与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结亲。”
然而唐格拉尔不仅不像莫尔塞夫所期望的那样以热情的态度来接受这次求婚,反而眉头紧皱,仍然让伯爵站着,不请他落座,说:“伯爵先生,在我给您一个答复以前,这件事情必须得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莫尔塞夫说,愈加感到惊愕了,“自从我们一开始谈起这桩婚事以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在这八年时间里,您难道考虑得还不够吗?”
“伯爵先生,”银行家说,“有些事情我们原以为是决定了,但每天发生的事使我们不得不随机应变。”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男爵先生。”莫尔塞夫说。
“我的意思是,先生——在最近这两星期里,发生了一些我料想不到的事情……”
“对不起,”莫尔塞夫说,“咱们这是不是在演戏哪?”
“什么叫演戏?”
“嘿,咱们还是有话直说吧。”
“我巴不得这样呢。”
“您见过基督山先生?”
“我常见到他,”唐格拉尔挺直了身子说,“他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
“在您和他最近谈话的时候,您说,我对这件婚事的态度不够坚决,好像把它淡忘了。”
“我确实这么说过。”
“好吧,我现在来了。您看,我既没有淡忘,也没有不坚决的意思,因为我现在来提醒您的诺言了。”
唐格拉尔不作答。
“难道您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莫尔塞夫又说,“或者您是想让我再三向您恳求,以我的屈辱来取乐吗?”
唐格拉尔觉得谈话继续这样进行下去,与他就不再有利了,于是就改变口吻,对莫尔塞夫说:“伯爵先生,您有权对我的含蓄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承认——而我向您保证,我用这种态度对待您,于我也觉得十分别扭。但相信我,在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实在也是由于万不得已。”
“这些都是空话,亲爱的先生,”伯爵说,“您去讲给一个偶然遇到的人听听还差不多;但是德·莫尔塞夫伯爵不是那样的人,当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去找另一个人,提醒他说话要算数,而那个人却想赖账的时候,他是有权利要求对方至少当场说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的。”
唐格拉尔是一个懦夫,但他在表面上却不愿意显得如此;莫尔塞夫刚才使用的那种口吻把他惹怒了。
“我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他答道。
“您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但却不好明说。”
“总而言之,您一定要明白,我对于您的沉默不会感到满意,但至少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就是您不想和我的家庭联姻。”
“不,先生,”唐格拉尔说,“我只是想推迟我的决定而已。”
“而您真的这么自以为是,以为我竟可以随着您反复无常,低三下四地等您回心转意吗?”
“那么,伯爵先生,如果您不愿意等待的话,我们就只好就算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些事情好了。”
伯爵紧紧地咬住嘴唇,直到咬得嘴唇渗出了血,才总算按捺住他那孤傲、暴烈的性子,没有发作出来;他转身向外走去,但刚走到客厅门口他就想到,照眼下这种局面,成为笑柄的只能是他自己,这么转念一想,脚步也就停了下来。
一片阴云掠过他的额头,抹去了脑门上的怒气,剩下一种淡淡的不安的痕迹。
“我亲爱的唐格拉尔,”他说,“我们相识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脾气。您应该向我说明一下,我也应该知道我的儿子为什么失去了您的欢心,这本来是很公平的。”
“那并不是因为对子爵本人有什么恶感,我能告诉您的仅此而已,先生。”唐格拉尔回答,他一看到莫尔塞夫软下来了一点,就马上又恢复了他那种傲慢的态度。
“那么您对谁产生了恶感呢?”莫尔塞夫脸色发白,音调都变了。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唐格拉尔的眼睛,他以一种以前不常有的自信的目光盯住对方看着。
“您最好还是不要勉强我说得更明白吧!”他说。
伯爵气得浑身颤抖,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狂怒,说:“我有权要您必须向我解释清楚。是不是莫尔塞夫夫人不讨您喜欢?是不是您觉得我的财产不够,是不是因为我的政见和您不一致?”
“绝不是那一类的事,先生,”唐格拉尔答道,“如果是那样,那就只能怪我自己了,因为这些事情在一开始讨论婚约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不要再追究原因了吧。我真感到很惭愧,让您这样作严格的自我检讨。我们暂且先不提这件事,采取中和的办法——就是,放一放再说,不算破裂也不算成约,用不着忙。我的女儿才十七岁,令郎才二十一岁。在我们等待的过程中,时间自然会促使事情不断地发展。晚上看东西只觉得一片黑暗模糊,但在晨光中看却就太清楚了。有的时候,一天之间,最残酷的诽谤会突然从天而降。”
“诽谤,这是您说的吗,先生?”莫尔塞夫脸色顿时灰白,喊道,“难道有人敢造我的谣?”
“伯爵先生,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认为最好是不要做什么解释。”
“那么,先生,我就耐心地忍受遭您拒绝的屈辱吗?”
“这件事在我更是痛苦,先生——是的,我比您感到更加痛苦,因为别人都知道我要跟您高攀,而一次婚约的破裂,女方所受的损害总比男方要大。”
“行了,先生,”莫尔塞夫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再说了。”
于是他气冲冲地紧抓着他的手套走出房间。
唐格拉尔注意到:在这次谈话的过程中,莫尔塞夫自始至终不敢问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唐格拉尔才放弃他的诺言。
那天晚上,唐格拉尔和几位朋友商量了很长时间;卡瓦尔康蒂先生则在客厅里陪着太太小姐,他最后一个离开那位银行家的家。
第二天早晨,唐格拉尔刚醒来就吩咐要报纸,仆人立即拿了进来;他把三四份别的报纸往边上一推,拣起了《大公报》,也就是波尚主编的那份报。
他急忙忙地撕掉封套,慌慌张张地打开那份报纸,不屑一顾地掀过“巴黎大事”版,翻到杂项消息栏,带着一个恶毒的微笑把目光停驻在一段以“雅尼那通讯”开始的消息上。
“好极了!”唐格拉尔在看完那一段消息后说,“这儿有一小段关于费尔南上校的文字,这一段文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可以省掉我一番劲儿,免得再跟莫尔塞夫伯爵来解释了。”
在同一时刻,就是说,在上午九点钟刚刚响过,阿尔贝·莫尔塞夫身着黑装,衣扣整齐,举止焦躁,在香榭丽舍大街基督山伯爵的宅邸门前三言两语地通报了自己的来访。
“伯爵大约在半个小时前就出门了。”值班仆人说。
“他带巴蒂斯坦一块走的吗?”莫尔塞夫问。
“没有,子爵先生。”
“请叫一下巴蒂斯坦,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门房去找那位贴身跟班,一会儿就跟他一起回来了。
“我的好朋友,”阿尔贝说,“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我很想从您这儿知道您的主人是不是真出去了。”
“他真的出去了,先生。”巴蒂斯坦答道。
“出去了?即使对我也是这样说?”
“我知道主人一向十分高兴地见到子爵先生,”巴蒂斯坦说,“所以我绝不会把您当做普通客人看待。”
“您说得对,我现在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想见见他。您说他是不是要很久才能回来?”
“不,我想不会,因为他吩咐在十点钟给他备好早餐。”
“好吧,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转一转,十点钟的时候再回来。在这个期间,如果伯爵先生回来了,您请他不要再出去,等着见我,行不行?”
“我一定代为转达,先生。”巴蒂斯坦说。
阿尔贝让轻便马车就停在伯爵府邸门前他刚才下车的地方,自己徒步走去。走过浮维斯巷的时候,他好像觉得瞅见伯爵的马车停在戈塞打靶场的门前;他走近一看,不仅认准了马车,而且认出了车夫。
“伯爵先生在里面射击吗?”莫尔塞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