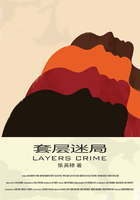在夜里与众多亘古化石相伴的感觉是奇妙的,至少给我的体会是死亡也不尽然只是散发着恐怖。我们吃着食物,喝着啤酒,讨论着化石堆的奇异,任时光飞逝。
为了助兴,胡莉变身为一名小提琴手,在月光下拉起了小提琴。音乐声似乎为化石堆注入了灵魂,恍惚中在月光下反光的众多化石仿佛复活了一般。
一曲终了。
康仪鼓掌:“小妞,能演奏帕格尼尼的名曲,说明你的品味真不一般。可是处在这种境地,我认为吹奏萨克斯能更好地安抚我们狂躁的心。”
胡莉摇身一变,变成一名打扮狂野,手持萨克斯的女乐手:“康小姐,你想唱有关爱情的歌曲的话,我倒愿意为你伴奏。”
康仪持酒瓶喝了一口酒:“我可没经历过悲天悯地的爱情。”
花酒用纸巾拭了拭手,站起身走到胡莉跟前:“看来失恋的体会还是我最深。我来唱。”
两人小声交换意见。
少许,低沉浑厚的音乐声响起。
花酒转身面对我们,开始演唱一首忧伤的歌曲。
我们沉浸在悲怆的旋律之中。
悲欢离合是人类不可辨驳的永恒主题,所以有关爱情的歌曲,任何时候都忧郁缠绵。
花酒唱完一首歌,三妖精自告奋勇地去跟他合唱下一首。
音乐声又起。
在两人的对唱声中,康仪靠在我肩膀上有些醉眼朦胧地说:“失恋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我敢肯定要是我现在吻你,黑蜘蛛会马上冲过来掐死我。”
我瞟了瞟坐在一旁用刀切烤肉的黑蜘蛛:“你多虑了。我没有过多吸引女人的魅力。”
康仪用下巴噌了噌我的肩膀,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抽了一口递给我:“就算不是纯粹为了爱,在有好感的男人面前,女人免不了争风吃醋。”
我接过香烟:“我不想在这方面消耗太多精力。”
康仪笑了:“那就简单多了。什么时候想和我亲热,吹声口哨我就心领神会。”
一番热闹之后,我们又围坐在一起讨论考察事宜。
“要全面发掘这个化石群,至少要五十年时间。”花酒明智地说,“所以我认为不如尽早上报,让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来进行系统的发掘工作。”
康仪表示赞同:“确实应该这样做。何况还有很多谜题不是随便就能解开的。”
三妖精瞅了瞅四周:“几亿年前的火山爆发形成的这种可怕景象,实在让人心悸。”
“不是火山爆发引发的灾难。”花酒抚摸着红宝石烟嘴,“我们看到的化石,没有蜂窝状和气泡特征。而且,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过几株红珊瑚化石。我认为这个化石群的形成不超过一万五千年。”
黑蜘蛛抿了抿嘴:“花酒兄的意思是这不是泥盆纪时代的产物?”
花酒点了点头:“我觉得很多化石不是古生物,是变异的畸形生物。”
胡莉歪了歪头:“花酒先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生物变异和大范围密集死亡呢?”
花酒冷静地说:“非常剧烈的辐射。”
黑蜘蛛有意识地看了我一眼:“博士…”
我摆了一下手:“我认为花酒兄的看法很有见地。我不慎掉进地洞中时,发现地洞中的石头有玻璃化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的地下,曾经发生过穿透力极强的核爆炸。也许当时发生的爆炸,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
胡莉张了张嘴:“我明白了,神话中上天入地的龙,不是一种生物,是一种爆炸形成的烟雾具象。龙与隆同音。电闪雷鸣,呼风唤雨是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的反映。”
康仪摆弄了一下酒瓶:“小妞,你一定喝多了。”
胡莉白了她一眼:“我就是跳进酒缸里也不会醉。你也不想想,传说中古代神仙打架,动不动就乘各种神器飞来飞去,不是喷火,就是发射各种光。要是激光武器都能造,那制造核武器和穿透力威猛的燃烧夷弹又有什么不可能?”
我站起身来:“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小狐狸,向导航中心汇报我们的发现,请中心派遣专业的检验师来进行发掘工作。”
胡莉点头,将康仪扶起来,送她去帐篷。
我走向自己的帐篷。
黑蜘蛛跟上来轻声说:“博士,我明白你为何会中止讨论…我知道在继续下去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鬼母计划,讨论这个计划无论如何都会让人不舒服…”
我顿了顿脚步:“我不是想逃避这个话题。我有一种感觉,企图利用等离子武器激活全球的火山和地震带毁灭人类的人,对上古文明的认知比我们更全面,更彻底。”
黑蜘蛛扯下一只手套:“那么,在合适的时候,你应该和花酒兄多探讨《白泽图》。”她微微仰起头看着我,“三妖精的能力其实也不弱,但你没必要袒护她。因为有时女人出现失误在所难免。”
我不想做过多解释,点了点头。
黑蜘蛛转身向前走了一步,偏过头来:“康小姐经常在你面前故意喝醉吗?”
我皱了皱眉:“什么意思?”
黑蜘蛛晃了晃手套:“没特别的意思。晚安。”
我看着她婀娜的背影,依稀想起了旧日的恋人。
花酒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是不是有种飞蛾投火的感觉…”
我笑了笑:“也不是。我想起了一些往事。至于在旅途中与旅伴太疏远和太亲热,我认为都不明智。”
“兄弟,以后的路,还长。”花酒瞅着化石群沉思了片刻,“你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我们这几个人的命都交给你了。所以,有些事不应该成为你的困扰。”
我点了一下头。
花酒把红宝石烟嘴装进衣兜,走到帐篷前,侧脸笑了笑:“何时有那么一个女人在你面前总唠叨让你戒烟、刮胡子、勤换衣服勤洗澡,还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撒娇和发脾气,这个女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女。”
我走上前掀开自己的帐篷:“你有过这种女人吗?”
“有过。”花酒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的妻子曾经是**女郎,实际就是**女。可是我从没为此感到丢脸。天底下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太多都是同床异梦。由此可想而知获得真爱实在不易。我这一生最自豪也是最伤感的事,就是有一个女毫不犹豫地爱上了我,并为了我献出了生命。”他掀开帐篷,“我的经验是,如果你不想为了缔造幸福,就不要为了逢场作戏轻易把靠近你的女人搂在怀里。****上的说法是:玩弄别人的人,最终玩弄的是自己。”
我由衷地说:“真是金玉良言。”
我们相对一笑,各自钻进了帐篷。
黎明时我从睡梦中被摇醒,睁开眼看到康仪披头散发地指着帐篷外,表情惊慌:“我们的头顶上停满了飞碟…”
我掀开睡袋坐起身:“你酒醒了吗?”
康仪不由分说把我拖出了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