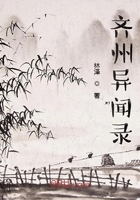芳草萋萋斜阳路,白雪茫茫终不归。
黑夜静静地过去,又一个白日到来了。
景昌元年腊月初七,经过短短十日的准备,北勐金印大王苏赫率三十万北勐大军南下,即将与号称有百万之众的南荣雄师一决高下。
汉水滔滔,汉江南北,一边哀号之声。
这一日,天冻死狗。一片苍茫的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北勐大军经过之处,一行行的车马痕迹,烙在雪上,或深、或浅,远远望之,像一朵朵从雪上长出来古怪花儿。漫天飞雪,扑簌簌落下,与被风吹得七零八乱,点缀着这一个硝烟四起的人间。
一南一北,两个国战,战事一触即发。
北勐骑兵南下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南荣。
江山万里,悲声阵阵,为了避祸而四处逃匿的民众,为正在遭遇雪灾的南荣朝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此时,离一年一度的除夕,已不足一月。临安府里,景昌皇帝为了备战,勒令宫中停止各种节庆活动,便于景昌元年腊月初十,御驾亲征,北上抗敌。
皇帝御驾,声势浩大。
临安城里,从皇城大门到北上的运河,长长的一路上,红毯铺路,净扫归整,两侧站满了前来送行的南荣民众。他们天不见亮就在这里等着,就为了亲眼看一眼景昌皇帝的风采。
他们很幸运。
景昌帝宋熹今日没有乘坐轿舆,而是身着金甲,头戴金盔,腰系宝剑,高倨于一匹俊美高大的白马之上,领着一群北上部将及亲近禁军徐徐行至运河,见到大气都不敢出的百姓,偶尔还会微笑颔首,英挺的眉宇间,一派温煦之色。
他很俊美。
他也很镇定。
这样的皇帝同,让紧张的临安百姓心里,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
群龙有首就好,天塌了,毕竟还有高个子顶着。
于是乎,有了景昌皇帝的御驾,这一场战争的看点似乎更浓了。
从南到北,由西及东,整个天下,各个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着动向。
宋熹北上,于腊月十二,领南荣军到达建康。
建康守将率众出城相迎帝驾,全城百姓欢欣鼓舞,于城外三里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声赫赫,其势震天。让一些民间术士占卜云:此战南荣必胜啊。
似乎宋熹一出,战事的胜负就转了风向。
百姓们看到皇帝,脸上笑意盈盈。
大军簇拥之中,宋熹面色安宁,淡然带笑。
可不等他尚未入城,就有人前来禀报。
“陛下,苏丞相回来了!”
在苏逸离开临安之前,南荣只有一个宰相。
那时,北勐南下的消息传来,宋熹想要御驾亲征,朝中就不能无人理政。于是他又紧急任命了另一个宰相,是为右相。也便说,如今的苏逸,已经成了南荣的左相。
从哈拉和林逃离,他如今到达建康,自然要先前来拜会皇帝的。
宋熹得闻消息,没有表现得太过激动,但晚膳都没有顾得上吃,当即就在建康的临时府邸里召见了苏逸。
大步进入客堂的苏逸,两鬓斑白,胡子及胸,形似老叟,把宋熹吓了一跳。
“你是何人?”
苏逸一把扯掉下巴上的花白胡子,伏身冲他行了一个大礼。
“微臣苏逸参见陛下。”
“苏爱卿,你这是何故——?”宋熹没有问完,就又止了话题。他也想到了苏逸在逃离北勐时,被蒙合的追兵围追堵截,这才不得不乔装改扮成这样的。于是,叹一口气,又微笑着抬手。
“苏爱卿吃苦了!快快起来说话。”
说罢,他转头吩咐,“李福,看座!”
一张木椅子搬到了宋熹的下首,苏逸慎重地谢了恩,一撩袍脚,正襟危坐着把自己带着紫妍公主千里迢迢前往北勐,再遇北勐陷害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向皇帝做了禀报。然而,说到宋妍之事时,他稍稍一顿。
“紫妍公主不堪羞辱,自缢而亡——”
早就得了消息,宋熹并不意外。
听罢,他眉梢微低,陷入了沉默。
苏逸瞄他一眼,又低声请罪:“是臣保护不力,还望陛下责罚!”
宋熹静默着摆摆手,淡淡道:“那便也是她的命了!”
时也,命也。
人一生的辗转坎坷,谁又说得清楚?
这一回,换苏逸沉默了。
那一晚的惊天动地,换来了如今的烽火连天。
确实,谁又能想到呢?
北勐与南荣这一战,是关乎南荣国运的战争。而国运之战,有时候就是一场赌博。赢了,国兴。败了,国衰——甚至于,国亡。南荣自太祖起,已三百余年风雨江山,到宋熹这一代,其间数百年,一直饱尝战争之苦。可哪怕曾经武力强大的珒国在最鼎盛的时期,亦远远不如现在如狼似虎的北勐。
这个天下,已无人能阻挡北勐骑兵。
他们铁蹄所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
而南荣,一个早已过气的大国,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满朝的沉疴弊政,除了可以在那一些文人墨客们留下的诗词中彪炳寻找富饶繁华,再无其他。
“陛下——”
苏逸幽幽一叹,将脑袋上的花白头发扯下来,捋了捋绫乱的发冠,突然站起身,朝宋熹行礼。
“微臣有一个不情之请!”
“苏爱卿坐下讲!”宋熹抬了抬手。
“多谢陛下!”苏逸拱了拱手,却没有坐回去,立在他的面前,一张老年少成的脸上满带忧色,“请陛下收回成命!即刻返京。由微臣代为领兵北上,与北勐一战!”
他一字一顿,声如洪钟,说得极为响亮。
可这带兵的要求,还是让宋熹微微一怔。
天下人都知南荣宰相苏逸能文能武,少年英才。可他这样的年纪,又是以状元身份入翰林,从而位极人臣的一个人物,几乎没有人看过他展示自己的武艺。包括宋熹,心里亦一直把他当成只通文墨,不懂兵策的文臣,根本就没有想过他能领兵打仗。
“苏爱卿——”盯着微微颔首的苏逸,宋熹刀刻似的峻峭眉目,似乎更深邃了几分,“并非朕不信任你。只是御驾亲征之事,早已周知四方,若朕半途而返,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我未战先惧?这一仗,朕怎么都要打的。”
顿一下,他像想到了什么,唇角微抿。
“人固有一死,胜负朕已不惧。反倒忧心我这一走,朝内空虚。一帮臣子昏聩老迈,成日里你争我夺,似不知国之将亡,还在蒙头做白日梦。叹,朕还真怕他们闹出些什么事来。爱卿回来得正好,明日你即返回临安,与右相一起,代朕主事。”
让他回去主事?
苏逸怔了怔,又要争辩,“不可,陛下!”
“朕意已决!爱卿不必说了——”宋熹目光略沉,视线从他的身上,慢慢转向了屋子中间里那一副陈闳的《八公图》上,目光变得温柔了许多,声音里似乎还带了一丝笑意,“朕一年四季都困于那皇宫之中,浑不知做人乐趣,早已厌倦非常。借此机会,可以出来四处走走,观山水,识佳人,可不快哉?!苏爱卿,又何苦拘了朕的乐子?”
“——陛下!”苏逸叹着,目光里带着无法掩饰的担心,“你的安危,就是南荣的安危啊,你怎可让自己身临险境?”
“谁说那是险境?”宋熹一笑,“彼之险境,吾之桃源。”
彼之险境,吾之桃源?
苏逸抿了抿唇角,看着他微光中的侧脸,突然换了话题,“来建康的路上,我听人说,她此番亦随苏赫王爷南下,这两日,恐怕已到达阴山了……”
“哦!”宋熹表情淡淡,像并不怎么在意,问得也极为随便,“见到苏赫了?他可是故人?”
这个问题,让苏逸迟疑了片刻。
没有听到他回复,宋熹也不逼迫,只静静观着画,唇上略带笑意。
终于,苏逸叹了一口气,“陛下,正是他。”
“嗯。”宋熹并没有意外,满不在乎地瞥一眼苏逸脸上的疲惫,微笑着摆了摆手,“苏爱卿下去歇息吧,明日一早还要赶路呢?”
“陛下!微臣想随你北上。”
“不可!”宋熹淡淡地笑着,轻松地面对他满脸的忧色,“朕登基一年有余,朝堂内外的事情,并无几件是我自己愿意做的。那时便想,做皇帝也就这样了。不能随心所欲,竟不如民间百姓自在。可这一次北上,朕却是心甘情愿,即便吃了败仗,再被人骂着昏君,也在所不惜。”
苏逸笑:“陛下又怎会是昏君呢?”
“呵!”宋熹也跟着他轻笑,“在他们嘴里,朕可不就是昏君吗?”
“唉!”从头到尾,苏逸都是极为了解宋熹的一个人,听完他的自嘲,苏逸叹息着,像要劝慰几句。可宋熹幽幽淡淡的目光,早已挪到了远处,正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
抬了抬袍角,他起身施礼,“微臣告退!”
宋熹没动,就像已然融入了那一方景致中,失去了自我……
……
南荣声势浩大的皇帝御驾亲征,消息自然早就传入了北勐。
一南一北,两路大军都在往汴京进发,于是,汴京地界就必然成为此次短兵相接的主战场。只可怜了汴京府的人们,结束战争不到两年,又迎来了一场更为严峻的战事,连年都过不好。
人心惶惶中,谣言四起。
汴京府的人,有门路的早就举家搬走了,没有门路的人,也只能苦苦盼着北勐人少做一点伤天害理的事,不祸及百姓,或者汴京守将古璃阳可以率领昔日萧大将军留下的这一支强悍旧部将北勐骑兵赶出南荣去。
古璃阳接到朝廷的圣旨,已有些时日了。
皇帝并未令他出征,只令他驻守好汴京。在接到圣旨的第一天,他就开始准备防御工事,调兵遣将,安排防守。这个时候,一切备战之事,早已准备妥当。而且,从腊月初一开始,汴京的各大城门就派下了重兵,守得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似的。一律人等,只准进,不准出。
汴京,这一座古老城池,还未开战,但风雨声、马蹄声,似乎就已传到了众人的耳边。
城墙上,风声凄厉。
古璃阳手按腰刀,目光静静地看着远方。
在他的身边,一个大块头的男子穿着盔甲,满脸黑沉。
“古将军,你这些工事,是做来何用的?”
古璃阳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却也有力,“防御外敌!”
“草你娘的外敌!”孙走南突然淬了一口,上去就要拎他领子,“旁人不知情,难道你也不知情?如今的形势,明镜似的摆在你面前,你不早早向主上投诚,你竟然筑起了防御工事来防他?狗皇帝一道圣旨,几个美人儿,几坛美酒,就让你的良心都喂了狗?”
孙走南性子暴躁,生起气来六亲不认,黑着脸,虎着眼,一般人还真就受不了。
然而,在他气咻咻的怒骂中,古璃阳不挣扎不抗拒,任由孙走南粗糙地拎着他的领子,将他重重推撞在垛墙上。脊背生痛,他皱了一下眉头,却也只有冷冷一句。
“我是南荣人!”
“有种!”孙走南二话不说,抡起拳头就揍。
真没客气,“砰”一声,古璃阳的脸上就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拳,眼下当初淤青一片。头一低,嘴角就有一丝鲜红溢出来。
呸一口,他冷哼,“你他娘的,揍得真狠!”
“这就叫狠!?”孙走南胳膊肘儿一撑,将他生生压在墙上,不客气地又挥起一记老拳,“你既然把主上当成了外敌,那老子如今也是你的外敌了。不乘机多揍你几拳,等没了性命,再去阎王殿里等着揍你么?”
“嘶!”古璃阳又挨一拳,再也受不得了。
他一把抓住孙走南的拳头,反身一拧,就将他制住,“你听我说!”
“说你娘的卵!”孙走南不是一个肯听人慢慢说的人,一激动起来连他自己都害怕。这一会儿,手脚被古璃阳扯住,他当然不肯认怂,一个反勾拳朝他肋下击去,用的全是十足十的力度。古璃阳双眼一眯,也不再忍让。两个人便这般在城墙上扭打了起来。
你一拳,我一拳,虎虎生风,老远就能听见孙走南的骂声。
北勐骑兵南下,对此时的古璃阳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他一直知道萧乾没有死。
而孙走南便是萧乾派到他身边的人。
从孙走南来的第一日,古璃阳就知道,他一定会有面临选择的那一天,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他生在南荣,长在南荣,家眷亦在南荣,若让他任由北勐铁骑踏过南荣的山山水水,蹂躏南荣的百姓,他做不到。然而,让他领兵与萧乾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一回,他还是做不到。
这一刻,他甚至有些羡慕迟重。
那个早就已经魂飞九天去了的迟大将军。
他死了,成了一个英雄。
不仅是南荣的英雄,也是萧乾心中的英雄。
可他呢?这一仗,到底何去何从?
在与孙走南你一拳我一拳的互抠中,他心中憋了许久的积郁,终于在战斗中彻底暴发了,就像为了寻找一种发泄的出口一般,他不再忍耐了,挣扎着狠狠脱掉了披风,脱掉了盔甲,也丢掉了腰刀,只穿了一身单衣与孙走南肉搏起来——
薛昉走上台阶,看到的就是这样荒唐的一幕。
两个人脸上有血,身上有血,人也滚在雪里,盔甲什么的丢了一地。
薛昉微微蹙眉,沉声低呵,“大敌当前,你们在做什么?”
两个紧紧抱在一起互不相饶的人,齐齐一怔,抬头望向薛昉。
“薛副将——?”
当初萧乾离去时,薛昉便被任命为北伐大军的副将了。后来萧氏一案之后,临安亦有亲自来的任命。也就是说,薛昉如今坐着的是汴京北伐军的第二把交椅。尤其,他曾经是萧乾的贴身侍卫统领,是萧乾极为信任和亲近的人,因此,他在这支北伐军旧部里面威信极高,将士们也都极为敬重他。
被他这么一吼,孙走南亦清醒了过来。
人一生气,差点忘了场合。
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古璃阳,慢慢从他身上爬起来,想想又有些落不下那口恶气,指着古璃阳就对薛昉道:“薛小郎,你自家问问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吧!问问他都做了什么?!哼,老子从未见过如此忘恩负义之徒!算我眼瞎,还曾拿他当兄弟!我呸他奶奶的腿儿!”
“你先消消火!”
薛昉身为军中副将,又怎会不知道古璃阳的防御工事?
可他年岁比孙走南小得多,却做了萧乾的侍卫统领,论心思,自然比孙走南缜密了许多。他慢慢走过来,捡起地上古璃阳丢掉的盔甲与衣袍,慢慢披到他的身上,然后走到城墙边上,望了北方一眼,重重叹口气,方才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笺,递了上去。
“主上都还没有消息过来,你们就先在窝里斗了!这事儿要让主上知道,得有多伤心呐!?喏,先拿去看看,再说吧。”
古璃阳抹了一把唇角的血丝,“主上来的?”
嗯一声,薛昉声音不轻不重,却字字诛心,“主上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吗?你们能想到的事情,主上会想不到吗?你们心里的顾虑,主上就当真不为你们着想了吗?亏你们跟在他身边那么多年,竟不了解他的为人!”
手指微微一颤,古璃阳慢慢接过信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