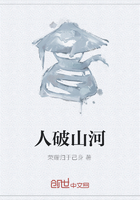我要是能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一写出来,那将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有一些人我在书中已经提到过,读者大概已经很熟悉了,还有一些人则可能不为人知,默默无闻。可这并不表示他给予人们的影响就会因此而磨灭。那些影响将永远活在所有因他们而变得甜美、高贵的生命中。
结识一些良师益友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算只是一个简单的握手,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传递的温暖。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他们诙谐优美的语言,就如同一首首优美的音符般婉转动人,总会融化我的愤怒,带走我的烦恼以及忧虑,当第二天阳光升起时,我又会以一个最佳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天,真是有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也许,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同他们相会,可是他们传递的爱却足以融化我心底千年的冰川,如同山泉涌入大海,降低海水的浓度。
时常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让你厌烦啊?”我总会回答说:我讨厌那些有着很重的好奇心的人,我更不喜欢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爱说教的人。他们很虚伪,好像在故意缩短步伐来适应你的速度,这会让人感觉不爽快。
这个问题从我握手中就能得知答案,有些人傲慢无礼,不愿和你握手,通常表现在握手不到一秒就会拿回自己的手,有的还会用纸巾手帕之类的物品去擦手;有的则是郁郁寡欢,和他们握手,会感觉自己很没有亲和力;而另外一些人则活泼乐观,他们的手就像阳光一样能让人感到温暖。可能这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手,然而它确实给了我最纯真的快乐,那感觉就像有人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你一样。我总能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万分愉悦。
我有很多远方的朋友,从未谋面,那数量多的我以至于常常不能—一回复他们的来信,我愿借此来感谢他们的亲切来信,只是我又怎么能感谢得完呢!
能够认识许多智者,甚至能和他们进行交流是一件让我感到很荣幸的事。只有认识布鲁克斯主教这样幽默风趣的人,你才能体会到和他在一起的情趣。还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用我冰冷的小手紧紧握住他温暖的大手。他总会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和我抓过我的我的一只手,因为她要在我手上复述给我听。我听了又惊奇又喜欢。虽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他那吸引人的语气却使我对生命产生了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他说:“可是海伦,你知道吗?贯穿这些宗教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爱的宗教。只有去爱你的天父、全身心的去爱上帝的每一个儿女,才能把这种善的力量聚集,让它慢慢的变强大,其实你的行动会暗示着你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他的一生就见证了这个伟大的道理。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与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一种洞察力,他看见:上帝拥有着无穷的力量。
布鲁克斯主教只教会我两个信条——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虽然只有两个,可是它们却使我受益终生,我也一直坚信爱会驱走黑暗,带来光明;爱会打败邪恶,带来正义。因此我很快乐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很少想一些暂时不会发生的事情,可总会时不时想到离我远去的朋友们。茫茫人海中,已经找寻不到他们的足迹了,可是他们的爱一直在伴我成长,那些快乐的回忆总会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相信,他们还是在用爱生活在天堂里。
在布鲁克斯主教也去往天堂后,我把《圣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宗教的著作,其中有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可是最能打动我灵魂的还是布鲁克斯的爱。
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温暖的握手令我感动不已。他是一位很适合做朋友的人,热情、而且知识渊博、健谈,只要他在场,总会有满堂的欢声笑语。
我清楚地记得同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博士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季节,莎莉文老师和我带着一个愉悦的心情在周日的下午拜访了他。那时,我刚学会说话,一进门,他就带我们去了他的书房。他坐在壁炉旁边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劈啪作响,可是他却说自己还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之中。
“还在聆听查尔斯河的细语。”我补充道“是的,孩子!”他激动地说:“查尔斯河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
书房里弥漫着油墨的香味,我用平时的知识不难得到这里有很多书籍的结论。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找寻它们,手指落在一卷装订精美的坦尼森诗集上。莎莉文老师告诉我书名后,我就开始朗诵: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我感觉到有滚烫的水滴在了我的手上,于是我就停止了朗诵。原来这源自这位可爱的诗人的泪水,这突发的事件让我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靠背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最后,我还答应了他的要求,朗诵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被禁闭的鹦鹉螺》。以后我又同他见了好几次,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而且喜欢他的为人。
在会见霍姆斯博士后不久的一个夏日里,莎莉文老师又带我去看望了惠蒂尔,那时,是在梅里迈克河边,他和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博士不同,相比之下他更温柔,可是也能从谈吐中得知他有很渊博的文化底蕴。这让我一下子就入了迷,而且我读了他自己的一本凸字版诗集,当我用准确的发音读到了一篇题为《学生时代》的诗歌。他高兴的为我鼓掌,还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语。他也很乐意的解决了我请教的问题,并且他还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还告诉我说故事里的小男孩就是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一些详细的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然后我又朗读了《赞美上帝》,这让我兴奋了好久,因为读到最后一行时,他把一个奴隶的塑像放在了我的手中。塑像是蹲着的,而且身上还掉下了两条锁链,仿佛是天使把他从牢房中带出来一样,那样子我从手中都能想象出来,可见它有多逼真了。后来,他还在书房为莎莉老师题字,以此来表达她从事这份工作的佩服以及尊重。而后对我说:“她是你心灵的解放者。”他送我们到大门口,温柔地吻了我的前额。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但是约未践,人却已逝去。
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就是我忘年之交中的其中一位。 我在8岁就认识他了,随着我判断人的标准的成熟,我也就越来越敬重他。他的博学并不是他最大的优点,他身上发出的最亮的光芒源自他拥有的人性美,这也使他最后成了莎莉文老师和我在忧患之中的最好的益友,他那坚强的臂膀帮助我们越过了许多艰难险阻。
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予新的含义,并引导人们如何冲破迷信的信仰,如何快乐的生活,如何正确的追求自由。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用爱来带领我们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是全人类最好的朋友。
愿上帝保佑他平平安安!
上文已经写过我与贝尔博士初次见面的情形了,再次见面是在华盛顿,那时,他在布雷顿角岛中心,那儿的环境很幽静,很适合他居住,那也是他给予我最美好的回忆的地方。特别是在他的实验室里,他把我当朋友对待,我们一起讨论各自的观点,这让我源自灵魂的自卑一点点的瓦解。不仅这样,他还会带我去放风筝,他告诉我,他希望以此能找到控制未来飞船的方法的灵感。
贝尔博士近似于一个全才,他最出色的莫过于把自己的研究生动有趣的描述给你听,这让人求知欲望更加的强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会让你感到很自信,因为他会用最简单的方法介绍复杂的问题,让你瞬间变成发明家。他会用最真诚的微笑来打动人的心灵,最后会和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产生共鸣,这将会救下多少孩子啊!我能遇到他,是最幸运的。
在纽约的两年里,我感觉每天都狠充实,因为我见到了很多久闻大名却从未见面的知名人士,这要很感谢赫赫先生为我提供的机会,都是因为他们夫妇让我去参观他们的藏书屋。
赫顿先生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唤醒人的人性美,不用读《我所认识的男孩》,就可以了解他。因为他很简单,是一个很慷慨、很宽容的人。
赫顿夫人则是一个能患难与共的朋友,她给我传授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如果不是她的引导和帮助,我在大学里也很难取得进步。她的鼓励成为了我最大的动力。
除此之外,赫顿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就有著名的——威廉·狄思。霍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过李察。华生·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豪德·克拉伦斯。
惠特曼先生。我也认识善于讲故事的查尔士·杜德里。华纳先生他们都很友好。有一次,华纳先生带着森林诗人——约翰·柏洛夫先生来看我。我最钦佩的是他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当我接触到他们本人之后,就越发的喜欢他们了。这些文学界名流,谈天说地,唇枪舌剑,妙语如珠,令人望尘莫及。就好像小阿斯卡留斯以不对称的脚步跟着英雄阿留斯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他们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
吉尔德先生同我说起他那伟大的行为——穿越大沙漠。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次他的来信,不仅仅是他的内容,最主要的是他的用心,把签名做出我能读出了的文字了。这也让我想到了赫尔先生,他的每次来信也会那样做。而且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深深的吸引着我,与他的接触就能感到他眼睛发出闪闪的光芒。甚至,当他以特有的、难以形容的幽默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使你觉得仿佛他就是那个温柔、又有同情心的伊里亚德的化身。
我还见过这些有趣的人,编辑玛莉是《圣尼古拉斯报》里受人尊敬的人,玛普斯·道奇女士、《爱尔兰人》一书可爱的作家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他们带给我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反映他们思想的书籍,以及留下最美时刻的照片。
可惜我不能一一的描述他们,而且他们那高尚的品质又岂是文字能表达出来的呢?这里由于篇幅问题,只能再提来两个人,为此我很犹豫。一位是善良的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在林德斯特时,我常拜访他们家。她乐于助人,而且总是很热心地向别人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另有一位是卡内基先生。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深深地震撼了我,他办事的果断也博得了大家一致的尊重,他的仁慈更是影响了一批批青年才俊。由于一些原因,也许不该提到他,但是他给予我的热情帮助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我恐怕就上不大学了。
就这样,朋友们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们总是绞尽脑汁地把我的缺陷变成美好的东西,并帮我彻底摆脱它们所带来的阴影,使我安详快乐地生活着。
我是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在华盛顿进行过演讲,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我永远记得的是,那时候贝尔博士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愉快的时光。
其实,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并不是那一次在华盛顿。我早在10岁的时候,就和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过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也许一说到贝尔博士,大家就会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是投身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但对于我来说,他却是位最亲爱的朋友。我并没有说谎,贝尔博士与我交往的时间最长,感情也非常好。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贝尔博士,可能是因为他比莎莉文老师更早地闯入我的生活吧。那时候我仍然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热心友好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是因为他的帮助,安那诺斯先生才愿意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从始至终,贝尔博士对莎莉文老师的教导方式都非常欣赏。并且他认为,莎莉文老师对我的教育方式,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可见他是非常钦佩莎莉文老师的。
贝尔博士一生热衷于聋哑教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据说他的这种对聋哑教育的热情与执着还是家传的呢!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就是贝尔博士的祖父,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是聋哑教育读唇法的发明者。贝尔先生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古板,他很幽默,而且把名利看得很轻,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教育的贡献而张扬自诩,总是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是不挣钱的。”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说:“可相对于电话的发明来说,它更重要。”
贝尔博士喜欢同父亲交流,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他就会说:“我要去看看我父亲了,和他聊天我总能有所收获。”
博士的住宅非常典雅美观,它坐落在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那里风景宜人。我以前看过他们父子很悠闲地坐在河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
有时候传来几声稀罕的鸟叫声,贝尔博士就会对父亲说:“爸,用什么样的标记来代表这种鸟声呢?”于是父子俩便津津有味地研究起发声学来。分析任何一种声音,他们都会把它们转换成手语来表达。父子俩的发音非常清晰动人,这可能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有关吧,听他们说话简直是一大享受。贝尔博士对母亲也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要聋了。
有一次,贝尔博士开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游玩,采了不少漂亮的野花。回来的时候,贝尔博士突然想到把这些采来的野花送给母亲,就带着小孩似的调皮对我们说:“我们几个直接从大门冲进去,给我爸妈一个惊喜吧。”
就在我们快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贝尔博士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抓住我的手说:“我们还是安静点,轻轻走进去吧,我爸妈好像都在睡觉。”
于是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大门,将花插入花瓶又小心翼翼地返回来。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父母沉睡的样子,很安详。在两张并列排着的椅子上,他的父亲仰着头,神态庄严地靠着椅子上,就像一个君王。他的母亲则伏在椅子的靠手上,脸完全被遮住了,只见满头银发。
我常常去拜访这一家子,博士的母亲喜欢在闲暇的时候编织一些东西,特别擅长编一些花草的图案。有时候她会抓着我的手,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儿,每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她们都当我是自己家人,让我感觉很温馨。我很庆幸能结识这样热情、善良、友好的一家人。
贝尔博士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常常和另外一些知名的科学家聚在一起。如果当时我正好也在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谈话内容一一拼写在我的手上。在博士看来,世界上无所谓难易之事,只要你肯努力,你就一定能理解它或者征服它的。我总是听得很认真,即使有时候没有听懂,我也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