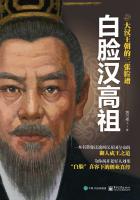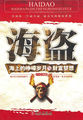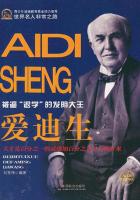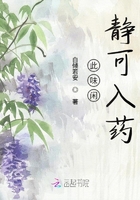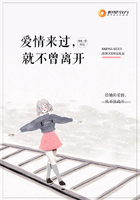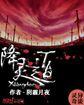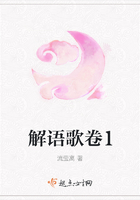毛泽东少有大志。早年辍学在家干农活时,就常在空余时间读一些呼吁国人起来救亡图存的小册子,如清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其中有一本关于列强如何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开头的第一句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正是这些小册子的慷慨悲呼和国家积弱的现实,造就了少年毛泽东忧国救民的远志。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已开始在这个山乡少年的内心深处发生躁动。
16岁那年,毛泽东与表兄文运昌一起,挑着行李,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投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是这个表兄,曾经积极向他推荐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报,而今又成为他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荐人和担保人。应该说,在自己的漫长的人际交往生涯中,毛泽东首先受益于这位表兄。解放后,文运昌曾六上北京,毛泽东在与其会晤时曾当面称赞他对引导自己接触新思想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篇《言志》,四座皆惊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所学校,1905年前称为“东山精舍”、“东山书院”,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费都有相当可观的津贴,然而韶山冲与湘乡虽只一山之隔,却不能隶属于此县,家庭又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因此出于地方观念,毛泽东是很难被录取的。
考场上,毛泽东面对着一篇《言志》的作文试题,笔落如飞,直抒胸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个人的志向与积弱的祖国联系在一起,雄文一气呵成。
“好文章!”几个主考老师不约而同地把全考场的桂冠判给了毛泽东。其中国文老师谭咏春,就是极力推荐毛泽东文才的主考老师之一。正是在他的全力斡旋下,毛泽东才得以最终录取。
赢得了老师的器重,并不等于就能在同学中获得尊敬。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读书,由于口音不同,衣着简朴,且入学年龄偏大,因而屡遭其他同学的奚落和白眼。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几十年后,与斯诺谈起他的那些高小同学时,他还反复说:
“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时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有感于这种环境,毛泽东后来以诗言志,乘兴作了《咏蛙》一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此诗一出,令所有的同学刮目以待,其中就有萧子升兄弟。他们日益与毛泽东接近,谈诗记事,并偶尔接济和维护毛泽东。这使毛泽东感激他们一辈子。弟弟萧子璋(肖三)后来和毛泽东保持了一生一世的友谊。萧子升则因政见的差异与毛泽东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谭咏春老师荐举他到长沙读中学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房里。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东山小学堂这块地方毕竟太小,已经容纳不了毛泽东这位有栋梁之材的弟子的成长了。他对这位从师于己仅有半年的学生说:“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科目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
毛泽东说出了没有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先生听后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恩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了东山高小。离别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至湘乡涟河渡口。毛泽东登舟挥臂,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东山小学堂的师友,也告别了自己少年的时光和追求,开始走向那外面的世界。
离开东山高小后,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谭咏春这位国文老师的知遇之恩,建国后,他才得知恩师已经谢世,曾给谭家寄去三百元钱,接济师母,并邀请谭老先生的儿子、自己在东山高小的同学谭世瑛多次来京叙旧。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呆了四个星期,就参加了湖南新军。此后又连续报考了几所长沙中等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最后终于决定继续上学,报考四师,后并入一师。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接触了大量的新鲜事物和报刊书籍,对世界观的形成有了积极的影响。他不再满足于感观上的见闻,知识上的被动接受,而决心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他需要结交一批新的朋友,与他们一起探讨国事,议论朝政,将刚刚获取的一些人生理想和见解去付诸实践。
愿做匏瓜不做牡丹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与自己在东山小学堂时的同窗好友萧子升重新相聚。两年前,萧子升就考入这里。在湖南一师,这对学友的友谊更深了,彼此引为知己,经常一起探讨学问,还曾经一起“游学”(见第二篇)。现在,保留下来的两人的通信中,从1915年8月到1916年7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就有12封之多。
1915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特地抄录了自己近期写成的一篇日记,题为《自讼》,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毛泽东以匏瓜(即葫芦)、牡丹相对照,阐明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这是一篇富有哲理的古文,翻译成白话文是:
有一位来客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野生的匏瓜?每当春天来临,土层变暖,它的嫩苗便冒出地面,伸展纤细的茎条,顺地缠来绕去,成为瓜蔓。这瓜蔓不能自行向上延伸生长,假若无人栽培管理,它便就近向荆棘丛上攀绕,或者向临近的杂草间躺爬。长到一定程度,瓜蔓上逐渐有间隔地生出一个个小花苞,在荆棘杂草丛中时隐时现,极不显眼。过往行人看到后一定会指着说:‘这不过是一种杂草而已。’可是,到了深秋时节,杂草叶子枯萎了,牧童过往其间,拨开杂草,便发现果实累累,大的像大肚酒瓮一般,原来是葫芦。
我们反过来看看,牡丹生长在由园丁栽培的庭院里,绿色叶子衬托着大红花,交生怒发,华贵鲜亮,争妍斗艳。无知之人一定会指着牡丹说:‘这牡丹花结的果实一定大得不得了。’然而谁晓得,到了秋凉时节,牡丹花一下子枯萎了,果实却一个也得不到。你比较比较,一个葫芦,一个牡丹,到底哪个值得你效法呢?”
我回答说:“牡丹先是盛开而后衰败,匏瓜先衰弱而后繁盛结实,一个是有始无终,一个是有始有终,有始有终的匏瓜是值得取法的。”
来客说:“但是,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就想在人前卖弄;略有一处优点,就迫不及待要告诉别人。每日里呼朋引类,很潇洒地掀动衣襟、耸动眉毛,一点没有沉静淡泊的样子,倒有张扬浮躁之气;像有的女子那样自悦于美丽,简直不知羞耻。你虽然表面十分刚强,其实里面非常空虚,每天心里挥不去名利的念头,使欲望一天天加深;被道听途说的言论,搅扰得神魂终日不宁,而自以为高兴。你每天学的是牡丹媚人之道,没有真实本领可以指望。可你却说愿意学匏瓜,这不是诡辩吗?”
我答不上话来,迟疑地退出,羞愧得汗都出来了,出气都难受,非常沮丧。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还是为了自省,假托一个人来解剖自己。但是,从毛泽东能够把这篇日记原原本本地抄在一封信中,这样严酷的解剖自己,我们就不难看出两人的的友谊之深。萧子升接到这封信后,是如何回答,或者作何感想,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萧子升自己订有一个读书札记本,名为《一切入一》。1917年夏,他请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约600余字。序言开头说道:“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惟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今世学术之涂愈亦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还谈到做学问如垒石筑高台,“积久而成学”。当时,毛泽东根据《群学肄言》书中所述治学方法,谈论了自己的治学见解:“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
1918年4月14日,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蔡和森家里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为干事。此后,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一同为学会会务奔波,一同组织湖南勤工俭学运动。这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率新民学会会员20余人前往北京准备赴法。1919年1月,萧子升先期赴法,与毛泽东暂时分离。
萧子升赴法后,毛泽东主持了新民学会的全部工作。后来,毛泽东把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汇辑起来,编辑成3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和萧子升的通信3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两位曾经的学友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并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萧子升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透露出它的观点: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会社为实行改革的方法、倾向于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对俄国式的革命……而在1920年底,毛泽东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1年3月,萧子升回到长沙,与好友毛泽东再次相聚,两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上,然而这时候萧子升发现,他们谈得越多,便似乎离得越远。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据萧子升回忆,讨论的最后一晚,两人同床而睡,谈至天色发白。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长沙,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两人分道扬镳。
后来,萧子升做了蒋介石政府的农业部长。建国后,毛泽东排除隔阂,多次寻找和邀请这位流落异乡(乌拉圭)的学友回国,均遭到萧子升的拒绝。1976年,这两位不同命运、不同政见的同学相继去世。生前未能再会少年时的朋友,成为伟人毛泽东的一件憾事。
◎“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在一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张昆弟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岳麓山蔡和森家和城内楚怡小学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越来越感到中国形势的每况愈下,必须寻找一条出路。他们常常引用顾炎武的信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严肃地“以天下为己任”;平时互相鼓励,戏称自己应成为“栋梁之材”。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谈阔论,毛泽东觉得要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目标,决不能单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摸索,而必须有一大帮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股力量,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认为单是团结校内和少数有志青年还很不够,团体要结得大、有力量,还必须向校外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终于发出了前文提到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1915年11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事稍快唯此耳。”
征友启事的内容,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的,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在启事的结尾,毛泽东化用《诗经》里的话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思是鸟儿鸣叫着以寻求朋友,我也像古人那样呼吁,请兄弟们来帮助我。
毛泽东的征友启事发出后,由于这种创举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只征得五六个人的回信,其中就有李立三和罗章龙。据毛泽东回忆,李立三的应征只能算“半个回答”,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走了。罗章龙在学校号房看见这张启事后,便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愿意交朋友。毛泽东随即复信,上面写着:“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相约星期天到定王台图书馆会面。
据罗章龙回忆说,他到第一中学访友,见到墙上贴有这个“启事”:
“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
“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部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此后的一段时间,罗章龙与毛泽东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常漫步市郊各名胜处,也曾经到板仓杨昌济的寓所晤谈。两人都能诗,有过唱和。一次,还一同步行去韶山,在茶店休息,毛泽东还帮助老农熟练地打草鞋。后来,罗章龙成为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
20世纪20年代初,罗章龙在北方做工运工作。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他同毛泽东夫妇、蔡和森夫妇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但是,1931年四中全会后,两位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就分了手,没有再见过面了。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之后,大家在一师研究学问、探索救国之路的活动便越来越活跃了。上课之余,节假之时,他们便三五成群,或聚会,或串门,交流学习心得,探讨国家大事。兴之所至,或游泳,或远足,留下了无限的情趣,隽永的佳话。真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随着队伍扩大,毛泽东在一师期间结识了一大批青年学生。除了萧子升和罗章龙外,其中有中共早期最著名的理论家蔡和森,中共第一个妇女部长向警予,科学家李振翩,史学家李平心,文学家周谷城,工运领袖李立三、郭亮,北伐时牺牲在许昌城下的北伐军团长蒋先云,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以及李维汉、夏曦、蔡畅、陈昌和罗学瓒、张昆弟、易礼容、张国基、周世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