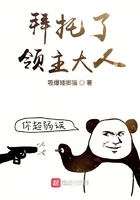李世荣父亲到家后闷睡了三天,他心中有无限的懊恼,最主要的是关于自身的。强人抢劫那晚,当一强悍的劫匪从他褡裢中掏走二十个银元时,他心疼了一下后毫无悲意,想这身外之物下一趟便会赚回,只辛苦一趟罢了。可劫匪后来下高继祖钱财时的分文无得及高继祖的答言,却揪痛了他的心肺。他暗暗羡忌着高继祖的机灵,懊怪着自己的愚玩不化,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高继祖的三十块大洋装在高继祖贴身的褡裢里,可是。转瞬间高继祖的三十块大洋在土匪抢劫时被高继祖藏匿得不见了踪迹。李世荣父亲责悔自己在背崖面壑的山道上无计可施,钱眼睁睁让劫匪拿了去。李世荣父亲的心里面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他在炕上闷睡了三天后,下了炕。呢喃着生意道上自愧不如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儿子还是两亩薄地实在,自己不是吃飞食的料就泥土里刨着吃,不要再吃飞食了。李世荣父亲头摇得货郎鼓一样,显得十分疲惫苍老。他从叫驴脖上摘下老鸹铃,挂在屋檐前的木橛上,偃旗息鼓,决意做纯真的庄稼人了,但他心里始终疑虑那夜不到尺寸的地方高继祖将银元藏在了什么地方。竟使强人半天搜不出一文。他拄着一根拐杖蹒跚到高继祖家里去问。高继祖因数日前的一场虚惊也歇在家里,他见李世荣父亲李满福前来。急忙溜下炕,将李世荣父亲邀到炕上,递过水烟锅。两人即胡乱闲拐了两句。说起那夜的灾祸,李满福老人苦着脸说这一跌怕永远爬不起来了,言语中充满沉痛的苦思,高继祖象征性地劝慰了几句,说:“哥哪!我也是苦了这几天了,想一辈子的苦白下了,人家一伸手全拿走了。”
“你的钱那夜没有拿走吧?”李满福老人听高继祖也哭丧着脸给他做样子,便一脸正经地故意问道。
这一问使高继祖万分作难,凭他的心性应隐瞒着答说钱被强人全搜走了,但那夜强人挨排逐个搜抢钱时,寂静得能听见心跳,想李满福是何等样人,定会听清强人的问话和自己的答言,知道欺骗是不能够的;若说钱没被抢去,怕李满福开口借钱,踟蹰着不知怎样答说高继祖。高继祖在心里稍一筹谋,说声:“哥你坐着,我尿泡尿就来。”说着就要起身出去。李满福老人猜到高继祖的作难心理,叫住了高继祖,道:“继祖你先停停。我问句闲话就走,不打搅你。”
高继祖见说,溜到炕沿的腿凝住了,面上堆起笑,说:“哥,你有啥事就说。咱哥俩还有啥顾忌不好说的。”
“继祖,我只是想知道你当夜那样尺寸之地把钱藏哪儿了?”李满福紧逼住高继祖的眼睛,似乎高继祖的眼睛里贮藏着秘密。
“噢,是这事……”高继祖回看了李满福一眼,知道今日这老儿来不告诉真情是不行的,便把腿收上来,笑着说道:“哥,你晓得那样吃紧的地方我能把钱藏在哪儿,还带在身上。”
李满福摆了摆头,说:“继祖就不瞒了,硬货贴身是藏不住的。我这次是来明明心,生意行道我没饭,今后就到土里刨着吃了,和你不争食!”
“看哥说的!你我哪有什么争不争的。争,也争的是外面人的钱:不争,外面的钱也不会跑到咱的兜里来,况钱哪能一个人挣光,各吃各的饭罢了。”高继祖本不想说,见李满福逼得紧,心想也没有必要隐瞒,便细细道了。
高继祖那夜被强人围住后,就在黑暗的人堆中估摸分辨形势。想趁纷乱溜掉,但旋即听见身后有人呼天抢地地哭号,知是有人逃跑挨了刀。他偷眼看见前后路径全被封死,未被拦截堵塞的,一边是满是尖利突岩高可千仞的悬崖,一边是黑咕隆咚深不可测的谷壑,知是溜跑不能了。他思忖着乘纷乱摸黑蹭到一处崖墙坎角处,挖了一个深坑,将银元全埋了,又慢腾腾扭身钻到人堆里,显出既沮丧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和众人一样跌脚拍手地哀怨着说今日咋就这样倒霉。待强人掠财而去后,他知强人正乐颠颠到安全地点分赃了,不会再回,并且见众人失财后心里乱成一团,各自哭丧着脸灰不沓沓有气无力地往家走,他便显出忧心忡忡十分不堪的样子,故意落在最后,待别人走远,遽忙反身挖出银元,装进褡裢,掂两掂,悠然自得地抄小路走回了家。
李满福老人听完后,点了点头,溜下炕,出了高继祖家门。此后,李满福和儿子李世荣远离了生意场,依靠两亩薄田,养家度口,移推日子。
李世荣坐在高继祖的坟地,在众土工的三言两语中,暗想着高继祖精敏的过去。当头,他又哀叹着高继祖自从招婿上门后的艰难。这种哀哀怨怨的追忆使得李世荣愁绪满怀,无法开脱。交夏的天气。太阳露出云层,地上便着了火。李世荣几人左等右等,眨眼工夫,时光已近中午,炎热的气息像翻滚的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包裹着他们。众土工热得不断地咽着唾津,可光秃荒瘠的田间地头,藏身避阳的一棵树也没有。几人诅咒着这里早晚阴冷中午炎热难耐的天气,脱下还未离身的棉袄,顶在头顶,遮蔽着阳光。包红正已很是不厌烦,建议回家喝口水,待先生来了再挖不迟。半天没有言语的李世荣坚持再等,说咱们莫要误了事情。正为此事几人争来争去,见沟湾里走来三个人,远远听见来人在说着什么,因为远,看不清是谁,那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地头。细看时,前头引路的是高全德,后面垂手端着盘子的是王永贵,中间拄着拐拐棍的正是大家熟知的安先生。安先生花白胡须,高大的身体有点驼,但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安先生是这一带的闲人,很少劳动,若是同样年纪的庄稼人,就没有这样的气宇了。安先生的事业承前启后,代代承传,附近缺少文化的农人对其充满着无限的敬畏。安先生来到地头后和打坟人寒暄了几句,也不歇息,独自在那一亩地上走来走去勘察着地形。安先生参照着周围的前壑后山,口中念念有词。安先生推敲一阵后,两步跨到田地中间的一处靠埂,手中的拐拐棍果断地插了下去,然后,头一扬,肯定地说:“就这。”王永贵有些忐忑,认为安先生简简单单地一棍插下去,是否准确灵验。张嘴要说话,安先生一摆手,永贵的话又咽进了肚里。安先生回头朝高全德说:“歇歇吧!”说着,捋着灰白的胡须,独自欣赏起远处的山景。李世荣等几个打坟的土工和高全德面面相觑了片刻,走上前笑着和安先生说话。安先生沉浸在远山远景的喜悦之中,无暇理会众人。众人见安先生不理自己,也就围聚在安先生周围,顺着安先生的视线看起那绵延横亘得如同涟漪的远山。心头奇怪的是,几十年熟知的山峦,平凡庸俗得猥猥琐琐,怎惹得安先生这般如痴如醉。高全德头上也蒙了一层雾,如在云端,他一会看着远山,一会看着安先生,终究不敢问安先生话。众人正各自心里面猜测,忽听安先生说:“全德,看棍上面露出水珠了没有?”高全德从雾里醒转,“哎”一声,忙紧步走到棍前,一看,连连惊呼起来。众人见高全德一个劲地叫好,纷纷跑过去看,见炎热的太阳下,棍端一颗汪汪的水珠,阳光下正放射七彩。众人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满脸飞溢微笑。异口同声赞道:“真有这么好的坟!”安先生缓缓走过来。众人慌忙退在两边,虔诚地看着安先生。安先生看了看水珠,说:“这便是暗堂的中心。暗堂坐西朝东,宽四长六,前延五尺是明堂,依样大小,要记清了!”众人唯唯诺诺着应承。高全德忙暗示永贵拿彩头。永贵明白高全德的眼色,忙诚惶诚恐跑上前,两手高举着盘子,说:“先生,一点心意。不要嫌少。”安先生推辞说:“算了吧!你手头紧。”高全德忙笑着说:“先生,这也是永贵的一点孝心,请你收下吧!”众人也在一旁顺着高全德的话帮着腔。安先生看见如此情形,说声:“那我就收下了。”伸手拿了一百元。给主家退了一百元。众人见他只收了一半,忙催促安先生全收下勘坟钱,安先生笑了笑,说:“这都多了,如果你们坚持,这一百元我也要退了。”众人见安先生如此固执,怕他真的连收下的也退了,就不敢再坚持,心里更是万分钦佩。安先生拿起拐棍,在插的地方画个十字,焚了炷香,说:“挖了三尺就到头了,莫要伤了这座好坟!”说罢,返身朝回走,去料理祭文和掐算决定下葬的日期。高全德安顿永贵再和土工商量动工的事,自己则扭头追上安先生,回家去了。永贵见此坟已显好兆,很是兴奋,给土工又是递烟又是奉承,催促土工现时动工。永贵又转念一想,疑虑重重地说:“李家哥,这坟的深度是多少啥?”李世荣见永贵问自己,想了想,说:“一般都是六尺。”
“可安先生咋说是三尺?”永贵疑惑地问。
“这个……”众人一时张口结舌,心里很是不解。
“按先生说的吧!先生料事可是极准的。”李世荣见众人疑虑,想了想说。
“三尺怕连棺材都埋不住。”永贵思虑着说,“再多少深些吧!”
“可安先生说……”李世荣还在坚持,不待话说全,永贵打断他的话道:“深半尺无妨碍吧?浅,怕风吹雨淋的,日后培土都来不及。”
李世荣还想说话,后衣襟被谢世仁扯了一把,便不再说话,瞪了永贵一眼,回身去取镢头。众人本对外乡人永贵心里疙疙瘩瘩,今见永贵执拗己见,说声:“就依你的再深半尺吧!”说完,各自取来铁锹、镢头,打起坟来。永贵见众人动了工,也便回去了。李世荣有些气恼,见永贵走远了。忍不住说声:“风水先生的还不如你的!”
“不要生闲气了,我们是下苦的,常言道‘客随主便’,管他的!他要再深,我们也能办到,不过多出一身臭汗!”谢世仁见李世荣气不顺,开导了句。
“有他后悔的时候!”李世荣恨着声骂了句,抡起镢头,使足劲挖了
李世荣他们几个土工轮流打坟,歇歇停停,干得很是消闲。刚干了一阵,永贵家里跑腿的传来话说,让他们到家吃饭。李世荣他们即刻停了手,来到永贵家洗手吃饭。饭后,便聚到茶炉前消停地喝茶。安先生看了眼土工,爬着炕桌用蝇头小楷写着祭文,过了一阵见几个土工还逗留在茶炉前,一副悠闲无事的神情,于是,安先生把年长的李世荣叫到跟前。问:“全德没给你们几个说啥时下葬?”李世荣答道:“没说。”安先生满脸不高兴,说:“后天天晓下葬,错过的话近几天没好时辰,你们几个要鼓把劲莫误了事情”。李世荣听后,慌了手脚,急急巴巴过去告诉了另外三人。另外三人急忙放下茶杯,叼根烟朝坟地走。李世荣随后走出了家门,想起一事,扭头又进了院门,走到跪孝的永贵跟前,压低声音,问:“永贵,坟茔的深度你可想好了,要不再问问安先生?”
“不问了,就按我说的你几个挖吧!”永贵说完,伸手往香炉里上香去了。
李世荣听后,想说话,又一时不想开口,扭头出了院门,来到坟地。
土工听安先生交代了时辰后,不敢怠慢,紧做慢赶,人停活不停,歇息也只是点根烟,喝杯泡的茶水,好在地也不太瓷实,刚下过雨,费力不费劲,到第二天干粮时分,明堂已经完成,暗堂也一尺有余。李世荣一行四人在坟地吃完干粮,就动身打坟,将近正午,正在地底埋头打坟,忽听上面有人招呼,抬头看时,认得是高全德的侄子怀远。李世荣四人停下手中的活忙问啥事,怀远结巴,比画了半天,众人才听清楚原来是王永贵女人樱桃的娘舅家来了人,正在家里闹腾。李世荣等吃了一惊,遽忙从坟坑上来,问:“咋着来闹腾?你叔让我们去帮忙吗?”
“不……不……不是的,是……是要让永贵打醮。”怀远说话时,噎得眼珠直往后脑勾。
“打醮?娘舅家要求永贵打醮?”李世荣拉住怀远的手问。
“嗯,永贵……永贵没……答应,正……正闹。”
“做醮那可得七天,要一疙瘩钱哩!”李世荣思虑着说。
“对了,先前娘舅家妻哥看见继祖有钱无后,想让老三顶门和樱桃成亲,占家产,继祖看见妻侄是个浪荡子没有应承。这次,准是来出气了。”钱生财头头是道地说。
“我二爸也……也这样子说,可……可娘舅……说给高家爸禳罪,说……说永贵对……高家爸不好,要尽……孝心,这次崩了……脸,也要……做……场醮的。”怀远说了一头热汗,左一把右一把擦着。
“你二爸让你来干啥?”李世荣问。
“我二爸……说……扭不过娘舅家,明天……做醮,让你几个……慢慢来,别急。”
“这尸体能放得住吗!天一天比一天热了。”李世荣发着牢骚,见怀远愣着,对怀远说,“你先回去吧!我们晓得了。”
李世荣等人便坐在坟前拉闲,无非是娘舅对还是永贵对,争执了半天,也没搞清做醮还是不做。但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是,永贵这次要把丈人留给自己的银元花完了。李世荣清楚:给先人做醮旧社会有,但如今不兴这个了。李世荣七八岁时见过河阳川首富刘霸天给亡父做醮的场景。当时,刘家三出三进的院落,灯火辉煌,两排一流的吹打手鼓着腮帮,一刻也不停,吹了七天七夜。李世荣记得,那次光请来的神位。就密匝匝摆了一八仙桌。刘霸天那次还请来了崆峒山的道士不停地诵经作法,还请了飞凤山的司公蒋师。蒋师带着十来个弟子。摇着羊皮鼓,抡着马头,庄前院后,跳神累得汗水浸透了衣衫。整个河阳川那几天锣鼓喧天,开了一次空前的庙会。事后,鞭炮的碎屑铺了一层,光棍刘良儿扫去后,点了一个冬天的热炕。听说刘霸天的那次打醮,光银子花销了满满一缸(缸高三尺,宽二尺1半)。李世荣想,虽说王永贵有丈人留的银元,这次打醮的开销,对一个缺吃少穿的农户人家来说无疑意味着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一蹶不振。
打坟的土工这日下午基本上没有做活,熬到夕阳西斜便早早回到王永贵家里。王永贵沮丧地耷拉着脑袋,凑钱开醮。高全德打发走请司公、道士、乐手后,正组织庄里打杂的人设账,准备开醮的相关事宜。娘舅家来的四人斜拧塌挎地倚在桌后款款地吸烟喝茶。李世荣认识娘舅家的一个年纪稍大的老头,搭讪了两句便出了屋子,钻进厨房拿了两个馒头往自己的家里走。永贵的女人樱桃挽留李世荣吃完饭后再走,李世荣说家里只有老婆子一人自己得先回去。李世荣返回家时,女人正给驴添草。女人抬头见男人回来,惊奇这么早不打坟怎么回来了,李世荣将娘舅家要求永贵打醮的事给女人说了。女人叹口气,说庄农人怎经得起这般折腾,钱哪里来。女人叹惋着回头给猪倒了食,站在厨房喊李世荣。李世荣不知啥事,走到女人跟前。女人说:“桶里没水。”李世荣干了一天的活,身体有些疲惫,责怪女人道:“你一天光景连桶水也没担来?”
你当我闲坐着呢?这一场雨糜谷被草荒实了,拔草均苗,脱得了身?从早晨到现在,地里的活一刻也没有停,肚里滴水未进,回家来猪、驴、鸡饿得闹翻了天,有工夫担水!”女人埋怨着。李世荣见女人有气,埋着脸担起水桶就走,身后听见女人唠叨着说:“洋芋、玉米到开犁下种的时节了,这么忙的日月还打醮!闹腾七天,误了开种,吃啥哩么喝啥哩!”李世荣听见女人的话,急在心头,可庄众的红白事,谁能落后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