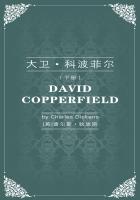“唔,”老聃的眼睛眯得更细了,好像睡着了一般,“你在地上已经看够了么?”
“是,我环游了诸国,各地的话也都听了,稀罕的玩意儿见了不少,不同的礼俗和音乐也都了解过。当时以为,有些是好的,有些太坏,要不得,但是现在年岁长了,像狗一样颠沛流离惯了,心就难免世故起来。虽然依旧躬行,道却总是行不通,于是渐渐觉得地上的东西,其实也差不很多,并没有自己理想中的乐土。我是每天都要反省许多次的,结果是,我以为懂了的,其实并不真懂。人心不古,是要治的,但怎样治法呢?于是我就想去讨教天了。前一回鲁国开文学家笔会的时候,请我们去登东山。上到山顶,我才明白鲁国也就是一块泥丸,于是想,自己从前说的那些,怕是有些天真。可东山也还是太小,离天还是太远,所以我想去泰山,听说泰山是极高的……远离地,靠近天,在云之上,也许就会有新的想法……”
夫子一气说了这么多,脸色微红,有些气喘。老聃微微地转过头,看他那惶惶不安的样子,想起他昔日凌厉的气势,心里竟有些同情了,于是也叹气,“你的心,还是不平静啊。想要的东西多,就会不足,一无所求,才能刚正……”
天色愈发黯淡,远处山脚下升起一缕炊烟。
虽明知老聃会说这种话,夫子心里却还是不甘,
“连天的样子都没见过,怎么能说明白了天道呢?”
老聃似笑非笑地说:“无往,而无不往。哪里都不去,整个宇宙就都去过了。”
夫子孔落寞了一阵,自语道:“我总以为,只有天了解我。现在知道,自己却并不了解天,我的道也要随着命一起完结了,可我总要看看才甘心啊。”
晚霞黯淡下去,天空扯过一块大幕,世界陷进大黑暗之中,一股阴冷萧瑟的湿气弥漫开来,老聃转过身,“你想去,便去吧。”说完,便悠悠地飘走了。
4
“泰山者,擎天之柱也。这东西穿了几百层云霄,顶着天呢,哪里是人能登的啊……”听说夫子要登泰山,季康子第一个跑过来劝,“……您是圣贤,不过……泰山嘛,历来想登的人也不少,要么半路退却,要么跌下来摔死,要么干脆失踪,从来没有一个人真的到过顶啊。就是常年在山中采药的人,走到玉皇坡,也就算是到了头,那片神林,人是进不得的,多少人白白丢了性命,况且那上面云雾缭绕,全是冰雪……不成不成!”
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贵,与夫子私交不错。泰山是擎天柱,乃鲁国圣地,想高攀的人也多,每年都要死不少冒险家,所以鲁国下了禁令,除非有特殊理由,官方不批通行证,私自攀登就是犯法,而这事就归季康子管。
“如果天要我无所求,自然会让我受挫;如果天要我往前走,自然能帮我逢凶化吉。”夫子孔平静地回答。这话他说了大半生,自己是非常相信的。
“嗨,您这逻辑,简直无敌啊……话虽如此……单说您这身体,也不比年轻时候了,怎么能登上去呢?不成不成!”季康子还是力劝。
“总能有办法的。”夫子泰然地回答。
“您毕竟是一代大师,万一有点闪失,我们都担待不起……话说您要是想散心,可以安排您旅游,我们还准备划出一块地,给您专心做学问……”
“谢谢了,不过您就别费心了。”夫子行个礼,送客了。
圣贤荣归故里,鲁国上下庆贺了三天,从此人人都把夫子当成国宝,为有这样的名人自豪。大学邀请去演讲是不好推辞的;达官显贵也都来拜会,请教为政的道理,又送了不少礼物,夫子客客气气地讲几句,也把自己的语录拿来还礼。这样闹了三个月,门庭才终于清净了,而夫子也因为太劳神病倒了。时已入冬,夫子只好在家修养,预备来年开春的时候再行动。
“现在国家终于器重老师了呢……”众人守在跟前,看着夫子枯树皮一样的脸,心里不是滋味,想说点安慰的话。
夫子摇摇头,虚弱地说:“口头上推崇我,却不实行我的主张,是不合礼数的;我不能得到重用,却被称作‘国宝’,是不合名分的。失了礼数就会昏乱,丢了名分就有过失。你们不要学他们。”说完叹了口气,闭上眼,心里感觉很疲倦。
大家都很感动,又想到总有一天老师要驾鹤西去,没人再这样教诲自己,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老师还是别去泰山了吧。我占了一卦,这事似乎不妥当。”子木跟夫子学《易》,颇有心得,近来动辄就喜欢占卦。
“《易》深奥得很,我没有研究得很明白,你已经弄懂了么?”夫子连眼皮都不愿意抬。
子木脸红了,不再说话。
夫子睡去了,并且做起梦来。
梦里,一头红色的大兽在天上飞来飞去。
直到腊月二十三,才下了第一场雪?
子贡进来时,夫子正在炉子旁边删《诗》,门帘掀开,一阵冷风卷进几片雪花,风吹得炉火烧得更旺了。
夫子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所以愈发勤奋。自己的学说,别人听得厌,自己也说得烦,所以他近来不大愿意著书,而更愿意编古书了。《诗》有几千篇,虽然之前删到了五百,但似乎有些还是不合礼,所以打算再删一删,因为气虚,就只能断断续续地做。
“您还弄这个呢?”子贡行过礼,间道。
“是啊,刚删到三百篇……真是百删不厌啊。”夫子把一卷竹简递过去,上面写满了名目,其中一些涂满了红色的圈圈叉叉。
“我看差不多了,您也手下留点情吧。”子贡仔细端详了一阵,半开玩笑地说,“其实有些也还不错,删了未免可惜,不如另出一本作内参……”
“唔……”夫子愣了一会儿,心思似已不在这上面了,“东西部置办好了?”
子贡点点头,“到处都打仗,物资稀缺,好在还有些熟人,买了些内部供应品,所以大体上也齐全了。出版界今年也不景气,《论语》的销量不如去年,但仍赚了不少钱,置办完年货,还剩了不少……”
夫子孔满意地望着他,良久,才温和地说:“给大家都分发下去,过完了正月,就各自散去吧。”
“是。”子贡犹豫了一下,“另外,我在路上还遇到个人,破衣烂衫,一脸的灰,想讨一口水喝,我看他快要渴死了,又不像歹人,就领了回来,”
夫子点点头,“请。”
于是就进来一个瘦高的黑脸汉子,衣服破烂得连抹布都不如,轻飘飘地套在一副干瘪的骨架上,腰间挂着一双踩烂的草鞋,赤脚立在那里,从头到脚一片黑,仿佛一棵被雷劈焦的枯树。
“打扰了。”黑脸汉子抱了抱拳,喉咙里似乎满是沙,一双眼却如两颗星,炯炯发光。
“您赶紧吃些东西吧……”看着有人受苦,夫子心中总不好受。
子贡就领着汉子去了厨房,掀开锅盖,盛了一大盆稀饭,摆上十张饼和一碗肉酱,“请慢用。”黑脸汉子也不客气,坐下来便吃。
足足一炷香的工夫,大汉终于出来了,却把夫子和子贡都吓了一跳:那副皮包的骨架竟如泡过水的菜干一样,忽然膨胀了许多倍,立在厅堂中,虎背熊腰,好像一座黑铁塔,声音也洪亮起来:“唉,好久没吃得这么饱了,真是感激不尽啊!这下子又有力气了,咳……事情实在多,总也干不完……我本来只是路过,讨口水喝……不过人是应该知恩图报的,听说您打算登泰山,虽然我不赞成,但就帮您一帮吧……”
夫子有点茫然,问:“还不知尊姓大名?”
“不敢不敢,别人都叫我翟……”汉子一笑,露出一口白灿灿的牙。
5
这年春天来得早,刚出正月,河上的冰就融得一塌糊涂,到处闪耀着碎光。在湿漉漉的河岸边,立着一个胖鼓鼓的东西,红彤彤的,远远看去,仿佛搁浅的鲸鱼。
“轻的往上飘,重的向下沉。用火一烤,热气自然就能带着人飞上天了。”翟先生解释道,“这就是云桴,有了这个,可以直接飞上玉皇坡。”
“了不起!”季康子盛赞,“万水千山都不在话下了,果然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这个嘛,还是要以人为本。”翟含糊地说。
“能飞得更高点么?”子路问。
“倒也可以……但我不愿意。我是崇敬鬼神的,玉皇坡是人间的界碑,我就只能送到那里拉倒。再往上呢,就看各位自己的命了。”
夫子点点头,望着云桴,满脸的皱纹中,藏了几分忧郁。
云桴能坐三个人,除了翟先生以外,夫子只带子路随行。其他人非要同去,然,夫子心意已决,任何人都没办法。
“现在世道不好,你们都有自己的正经事要做,就不要来凑热闹了。”任谁劝,夫子就只是这样答复,“我只去看看便回来。”又特别对子贡说,“有什么事,你要多照看一下。”
子贡深沉地点点头,大伙都红了眼圈。
三天后是个顺风的好日子,鲁国的政要和各国大使都来欢送夫子孔。翟先生请夫子孔和子路上了云桴,解开缆绳,点上火,云桴腾空而起。
脚下的大地渐渐远去,地上的人、房屋、田野、河流都渺小起来。黑的上,绿的湖,白的烟,连绵的青山,五颜六色的颇好看,尘俗的渣滓都缩小不见了,只剩下一目万里的辽阔。眼前是一轮金黄的太阳,耳畔是呼啸的风,送来阵阵寒意,头顶上的火缸烧得滚烫,喷出一股股黑烟和灼人的热气,鼓胀着云桴,跨越山山水水,攀上层层云霄。
“腾云驾雾啊,哈哈!”子路是勇武之士,但习惯了平地走路的人,初次飞天,还是有点头晕心悸,于是就故意大声喊。
翟先生往火缸里添了些木炭,冲他咧嘴一笑,那自信的模样让子路感动。
夫子觉得有些冷,关节酸痛酸痛的,就裹紧了腿上的狗皮护膝,呼吸有点吃力,心里阵阵地慌,脸色也白了。
“天高气薄,您吸两口这个。”翟递过来枕头一样的皮囊。
夫子把皮碗扣在鼻子上,拧开门,一股气就涌入五脏六腑,吸了两口,顿时舒服多了。
“万千景色都尽收眼底,况且还会移动,实在不输泰山了。”翟开玩笑说。
夫子也笑笑,没有说话,只望着下面越来越远的山河,偌大的一个个国家,都成了巴掌大的弹丸之地,自己一生走过的足迹,不过是一条细线啊。
云雾渺渺,绵绵无尽,一颗明晃晃的大火球,无牵无挂地飘浮着。群山都矮下去了,只剩前方一座苍莽的山峰,披挂着一层冰雪的铠甲,穿破云海,朝着更高远的地方刺过去,消失在一片青铜色的天空中。抬头看去,仿佛苍穹下悬挂的一根巨大冰凌,在无限的空旷中闪烁着光芒。
“那便是泰山了。”翟轻轻地说。
“是了。”夫子点点头。
玉皇坡上,正飘着细雪。
异常高大的松林环山而生,仿佛一条绿腰带,截断了万年不化的冰雪,也阻隔了人的去路。林边有一块草地,旁边有间小木屋,云桴微微一震,就在草地上停了下来。
三人顿时觉得进入了另一个季节。火缸已经熄灭,脚下却翻滚着厚厚的一层热浪,似乎地下有一个热炉子,雪落在地上,立刻融化蒸腾起白烟,恍如温泉池。湿气热乎乎地贴过来,混着松林飘散出的清香,从毛孔往五脏六腑里钻去,令人目眩神迷,心痒难耐。
“听山中采药的人讲,这林子是神设的屏风,人不可穿过,也不能穿过。”翟先生望着那片茂密的松林,幽幽地说,“登泰山的人,到这里就可以止步了。”
这片松林不知生了多少世代,足有几十人高,宽厚的枝叶挂着水滴,苍翠可人,林间白雾缭绕。三个人无声地望着林子,思绪纷飞。
“好像有声音。”子路说。
隐约有几声沙沙的声响,然而很快就从耳畔消失了,三人又仔细地听了一阵,却再无动静,唯有雪花静静飘落,水汽袅袅升起,松林如绝壁般矗立,除此之外,便是了无边际的寂寞。
6
“在云桴上,可以饱览天下,您又何必非得登这泰山呢?”翟一边说,一边往铁锅里扔些干菜,又添上水,生起火,再把饼放在锅盖上,“那上面无非就是冰雪,爬又爬不得,有什么可看的呢……”
这间木屋大约是采药人避风雪的,里面有一铺火炕和一口大锅,堆了些木柴,这些都是翟考察好的。他知道夫子孔是国宝,所以先前自己已经飞来过一次了。
“唉,你还年轻,不懂得老头子的心情。”夫子眼望着铁锅下面跳跃的火焰,有些出神。
翟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么,我就等您一天……下面到处都在打仗,我实在不能多等,天黑时您还不回来,我就只好自己下山了。”
顿时,子路又想到那片雾气蒙蒙的松林,心里忽然一阵惶恐,登山的事竟前所未有地沉重起来,他望望老师,想说又不知该说什么。
“好,”夫子面色平静,又对着子路说,“你也不要去了,在这里陪着翟先生。”
“那不行!”子路急忙说,“老师去,我也去!”
“这事吉凶未卜,你还年轻,应该多做些有用的事,不要跟我去犯险了。”
“不成!来都来了,我一定跟您去!”子路急得脸都红了。
“唉,你还是这么倔强。”夫子摇摇头。
说这话时,铁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菜叶在水上跳起舞来。三人喝着热乎乎的菜汤,就着肉脯,吃起了饼和糗。
吃过饭,子路出奇地困,便倒头呼呼睡去。雪已经停了,夫子和翟推门而出。地下的那股热气已经消退,寒气重又袭来,泥地慢慢冻成了一片冰场。满天星光闪烁,洒下一地银辉,雾气已然散去,松林在星光下无声无息,仿如一道影子做成的墙,森然可畏。
其实,翟对夫子孔的学说向来是不大买账的,以为实在于天下大不利,然而见到老头本人,却又觉得他心肠不坏,只是脑袋有点迂罢了,所以分别在即,心里还有点难过,便想说点轻松的话题:“您觉得我这发明怎么样?”
“唔,”夫子回过神,转眼望向云桴,沉思了一会儿说,“不错呢,前一回我见过公输般先生,他也在搞什么飞机……将来的世界,恐怕要有大变化,我怕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夫子叹了口气,不自觉地揉了揉腿,年轻时东奔西跑受的那些风寒,如今都沉淀在骨头缝里化成了风湿,寒风一吹,就丝啦丝啦地疼起来了。
“咳,那家伙,真让人头疼……”翟摇摇头,“‘能学’倒是很有道理,只是他有点儿走火入魔了,以为搞明白‘能’就天下无敌了。飞机虽然厉害,但终究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我跟他讲过几次,他都听不进去……”
“他只晓得‘器’,看不见‘道’啊。”夫子叹了口气,“这样,就百害而无一利。”骨头还是酸胀,虽然哀公每月邀请他去泡温泉,可惜一双老寒腿,终究不能像年轻时一样健步如飞了。岁数这回事,哪怕是圣人,也一样没辙啊。
“是啊。但我和他不同,他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我是为兼爱而科学的。”翟转过头,认真地望着夫子,“我知道您看重‘道’,瞧不起‘器’,不过器不利,事就难成。譬如有人在千里之外行不义,要治他,走路也许得一个月,乘云桴却只要一日。况且,衣食住行,都要靠器物,粮食丰收就不会饿死人,旅居便利胜过愚公移山,于人有利的就好。您不是也说,仁者爱人么?”
夫子望着前面幽秘的丛林,心绪有些凌乱,琢磨了一会儿,才开口:“话虽如此,只怕器物高妙了,人心就乱了……”
“可您也别忘了,要匡正人心,得先喂饱肚皮。”翟究竟是年轻,反应也快,“没有‘道’,‘器’就走上邪路;没有‘器’,‘道’就走不通。只有器不成,没有器也不成,凡事都不能偏执一端,您不是也主张过犹不及么?不论器还是道,都不能弄得太过啊。”
“倒是这回事。”夫子的思绪还是飘忽,沉默了一阵子,才转过头,“唔,这些话么,我想也是有几分道理的……虽然我不很同意,但确实跟您学了不少东西,以后我再想想这些……”
“呵……”翟笑了笑,“其实我们求的都一样,只是走的路不同吧。”
夫子发出一阵苍老的笑声,淹没在浓稠的夜色中,悬挂在头顶的北斗星,仿佛伸手可及。
7
林子里没有路。
黎明之前,地下的那股热浪又慢慢升上来了,不到一个时辰,满地的冰渣都已经烘成了水汽,松林又是白蒙蒙的一片了。脚下的泥土半湿不干,踩上去有点儿滑,子路背着布包,夫子拄一根木棍,两人互相搀着,一点点摸索着往上爬。
雾气在阳光中弥漫,松叶上的露水不时滴落。没有鸟鸣,也不见虫飞,树与石之间,只有山花和泥土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