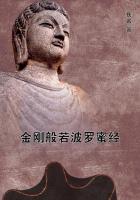春雨纷纷,这时节就是闷热的难受,连翘悠闲的坐在自己的小院子里面扇着团扇,突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跑了来,急切的对连翘说道:“大姑娘,快,快走。”
走?往哪里走?这么晚了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连翘淡定的站起身来,眉头微微的蹙起。
“快,快点,大姑娘把稍微值钱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焦急的指挥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嘴里更是念叨着作孽哦作孽哦。焦急之色溢于言表。
被叫的女子虽然不明白家里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看见从小服侍自己的老妈子如此着急,也不多说话,手脚麻利的收拾着东西。“阿好,我们这是要去哪里?”一边快速的收拾东西,一边问道明显惊魂未定的老妈子。
“去逃命,大姑娘快点收拾,马上我们要离开京城,我去看看夫人收拾的怎么样了。”阿好边走边说,很快就消失在门外。
逃命?离开京城?好好的怎么要离开,连翘放下手中的衣服就往里间跑,打开梳妆台上的小盒子,只见那个普通的木盒子里面静静的躺着一块白脂玉,虽不是上好,但是那剔透的光泽度也可以证明这绝不是凡品。飞快的把白脂玉收到怀里,连翘也不收拾东西了,转身就往后门跑去。
因为是晚上,街道上没什么人,连翘一口气跑到一座大宅子外面,那府门外的两口石狮子威风凌凌,足见得府门里面的也是大富贵人家。喘着粗气,连翘一手紧紧的捂着白脂玉,一手用力的拍着府门。
安奎开门,安奎快点开门,求求你了,安奎快开门,连翘心里着急的呐喊着,终于在手被拍的酸痛不堪的时候,门里传来了一个老者的声音,“谁啊?”
“是我,我是连翘,我要见安奎,帮我开开门。”连翘知道,询问的是安府的守更人福伯。本来以为会和曾经的无数次一样,在福伯的笑容下欢天喜地的被邀请进去,谁知道平时慈祥的福伯居然变得冷漠,“沈姑娘还是回去吧,少爷出远门办事去了没在家。”
用力的拍打着依然紧闭的门,“福伯,你开开门,我有东西要给安奎哥。”
吱呀一声,铁门发出沉闷的声音,福伯的身边站着安远山,安奎的父亲,“沈姑娘还是回去吧,奎儿已经订了亲,下了聘。这东西还是你自己留着。我们奎儿拿着也不方便。”
连翘拼命的摇着头,不,不会的,安奎哥说了,他喜欢自己的。“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安远山冷漠的扔出一带银子,“你们沈家已经败落了,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官家小姐?你根本配不上奎儿,识趣的话就拿着银子快点走。”随即示意福伯关上铁门。
连翘眼睁睁的看着那铁门在自己面前缓缓的关上,好像关住了心里的最后希望。心里的一点信念也轰然倒塌。
那两头威风凌凌的石狮子和那被扔在地上的一小袋银子仿佛有生命般的嘲弄的注视着泪水弥漫双眼的沈连翘一步一回头的离开。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辆马车匆匆忙忙的从一座大宅院里面奔出。
四十岁的老妈子脱掉了长裙褥子,穿上麻布短裤,利落的赶着马车,而马车里面断断续续的传出嘤嘤的哭泣声。
沈氏看着自己身边还一脸睡意未消的小儿女,心里万分的苦涩,自己怎么这么的命苦啊,斗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等着老爷子的正室病逝,做了老爷子的填房夫人,本以为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不想却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老天爷这是要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啊。
沈连翘拉着自己的妹妹沈浣蜷缩在马车里的一角,沈浣年纪还小,大晚上的被折腾起来睡意未消,这时候也不管自己的母亲哭个不停,慢慢的又打起了瞌睡。而沈家唯一的儿子沈浩也是靠在马车内壁上睡了过去。
“娘,我们这是到哪里去?爹爹呢?”连翘一边把自己的披肩往妹妹沈浣身上拉,一边问出自己憋在心里面一晚上的疑问。而怀里的白脂玉慢慢的变得冰凉。
沈氏本来已经慢慢回复平静的心,被连翘这一问,又开始嘤嘤的哭泣,“你们以后就没爹了,被皇上给处死了。”说完也不管大女儿听的明白不明白,捂着心口默默地流泪。
爹爹死了?虽然从小自己就不受爹爹喜欢,听老妈子说,自己生下来的时候,爹爹一听是个女孩子,连娘的房间都没进,直接掉头就走了,娘亲派了人去问给大姑娘取个什么名字,当时爹爹正在药房里面摆弄连翘,就随口一个药名就是连翘的名字了。因为爹爹的不喜欢,连带着娘亲也不怎么和自己亲近,基本上在过去的十二年里面,连翘是没有享受到一点父爱母爱的。尽管如此连翘对自己爹爹依然有一副满腔的崇拜,高超的医术,儒雅的风范,是当今名士。
骤然听到这个消息,连翘也不禁红了眼眶。
夜色慢慢被白天的来临替换退场,马车摇摇晃晃的一路前行,因为走得急,就带了一些金银细软,这荒郊野外的,也没个茶楼饭馆。被饿醒了的沈浣和沈浩,眼巴巴的望着自家娘亲要吃得。
从小享受惯了的人,哪里受过挨饿的苦,眼泪汪汪的就是要吃得,特别是沈浩,因为是沈家唯一的儿子,更是从小就备受老爷子的宠爱,哪里受过这样的苦。
“娘,我要吃早饭。我要吃早饭。”沈浩扔掉披在自己身上的披风,扒拉开身边的包裹,拉着沈氏的手臂不停的摇晃,撒娇的说着,只要自己一撒娇,娘亲铁定了不会拒绝自己的要求,这是在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连翘心里本就难过,看着沈浩这么的不懂事,顿觉生气,“你可不可以别闹了?爹不在了,你以为我们还是以前的少爷小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