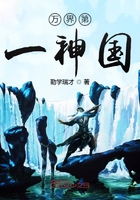1961年2月21日上午,敬爱的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和第二批特赦战犯时,曾特别提醒我,今后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我打从那天开始,力求按周总理指示去做。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时,问我对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有什么体会,我说我尝到了说老实话的甜头,因为说老实话不用费心思去编造,也不用担心以后记不清,更不怕别人戳穿,比说假话容易得多。周总理勉励我应坚持下去,可是这次我竟违背了总理的指示,说假话了。我知道如果我说我在崔万秋家中认识蓝萍(江青)和狄克(张春桥)我就会被他们杀掉——杀人灭口。我还想活下去,我不能不说假话。我请求总理在天之灵能宽恕我,当时,我是不得已才说假话的。我回到牢房,便倒在小床上,为此而难过异常。
没有料到一个星期后,又有三个穿便衣的来提审我,看派头也不小,可对我却不像上次那样,表面客气都没有,一开口就肯定我不老实交代问题。
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我早有所准备,当他们责备我交代问题不老实时,我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过去杀了人都敢交代,杀人抵命我都不在乎,难道认识一个人比枪毙还严重吗?我完全用不着在这样一个小问题上来抵赖,这太没有意义了。其实我知道,如说认识这两个人,可能比拿出去枪毙还要严重,所以我不得不再一次说假话了。但他们不相信,这回可就不是光动口,而是动口又动手了。先是坐在两旁的青年人走过来,一边一个扭住我的手臂,看来是准备殴打我,我考虑了一下,如果反抗,非吃大亏不可。他们一再逼着我问:“记起来没有?”我一再说一个也记不起。他们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去撞,我是练过这种功夫的,但我故意大叫“哎唷!”坐在中间那个把手一扬,他们又扭住我的手臂用力向外弯……总之,凡可以使我感到痛苦和恐惧的动作都试了一下。我除了叫苦连天,满足了他们使我痛苦的欲望后,还是表示不认识,他们便把我猛力摔到水泥地上,一个高大个举起穿皮鞋的脚,准备向我头上踢来,还是坐中间那个向他叫了一声,使了个眼色,才没有踢到我头上。临走时,那个高个子还把皮鞋伸到我脸上,恶狠狠地说:什么时候反省过来,随时向管理人员报告,再来提审。这一关总算这样顶过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崔万秋才从美国写了一篇洋洋数万字的长文在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题为《上海岁月话江青》,写他和蓝萍在上海的情况。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为了讨好过去与崔万秋有关的“四人帮”一号、二号头头,还下条子要枪毙我。因为有人向他提出,全国找我写材料的人很多,等我把材料写完后再枪决,他同意了。我真没想到,写点外调材料,竟能使我“死刑缓期执行”。因而能拖到1972年,周总理发觉我又被关起来,才下令将我释放出来。
在离地一丈左右的时候,我一下把一根横着的小树枝抓住,我飘飘落地,未伤毫发
5年监狱生活还有20天才恢复自由,我被政协一位造反派小头头从监狱领回(不是接回,而是打了领条的),到机关东楼下原来溥仪住过的小房间,便看到骨瘦如柴的妻子,含着热泪在等待我。那天和我同时释放的还有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的董益三。他也是特赦后又被关了5年。他的妻子宋伯阑也是流着泪在等候他。文史专员组全组成员都在那里等我们。
杜聿明,宋希濂……一个个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庆贺我们能活着回来。他们中有一位是第六批特赦出来的,是我们当中最积极的分子,造反派便指定他领导我们劳动。他见我们回来,立即用很严肃的口吻说:“你们回来还得参加我们的劳动,可以回家休息一天,后天起便来和我们一同劳动。”我一听这话,心想造反派真有眼光,挑一个这样的人来管理我们,准比他们还要高明得多。不过我觉得总比在监狱要好一些,起码可以和家里的人在一起,还有一些和我的思想差不多的老友可以边劳动边聊聊天,所以我妻子领我回家休息一天后,我便准时去机关参加打扫卫生和搬运物品的劳动。由于我在押期间,左腿下肢被红卫兵用擀面杖打成骨裂,走起路来总不那么方便,而那位带我劳动的,因刚特赦出来就恭逢十年浩劫序幕拉开,周总理还没有把他们正式委派为文史专员,只是让他们在专员室学习。他为了争取早日成为专员,遇事都表现积极。他看我年龄比较轻,而且身体也较结实,每遇重劳动总是指派我去,我也总是尽力去干,谁会想到竟会一连多次几乎使我造成终身残废甚至摔死。
有天上午,这位朋友带我去卸煤。我们两人要把几卡车的煤在一个上午都卸下来,一般壮劳力也不易办到的。他却向造反派一个管我们的头头包了下来。我一连干了两个多钟头才卸下大半车,一看他已卸完一车了,我只好加劲干,忽然我感到一阵头晕,从没有卸完的煤上头栽了下去,幸好正栽在一堆煤上面,要不那次我就提前“安息”了。
还有一次,有一个管理我们的造反派小头头,新占了别人(估计是我们一样的“黑五类”)一处五层楼上的大套间,让我去为他搬家——从他原来住的四层楼上两小间搬东西上卡车,再从卡车上搬东西上五层楼。我是做到了尽力而为,力尽为止。但在抬一个重达百余斤的大木箱上楼时,我一再说我腿受过伤,抬这么重的东西上楼没有劲,怕出事故,我多提点背点都行,他把脸一沉:“累不死你!”我只好咬着牙关和他抬,他走前面,我走后面,重量绝大部分压在我肩上,我一边上楼一边喘着大气,用手紧紧抓着楼梯的栏杆扶手,刚爬到三层楼的一半,受过伤的左腿一下软了下来,跪在楼梯上,他不但不扶住,还把手一松,整个大木箱朝我身上压了下来,如果不是跟在后边提东西的那位好心的司机,抢一步把木箱顶住,我即便不粉身也得碎骨了。接着司机提出替我抬大木箱,让我提他手上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我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不敢说声“谢谢!”因为怕被别人指责他“划不清界限”,反给他添麻烦。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肯在那样危急之下“助一臂之力”的优秀共产党员、政协汽车队的一位可敬的好司机。
随着局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四人帮”是要篡党夺权,对于“横扫”我们这些人,只是虚晃一枪。虽然这虚晃一下也造成不少人的死亡、伤残,但目的不是完全要消灭我们。所以对我们的劳动也随之而减轻,让我们管理政协机关的全部花草树木和厕所、食堂及机关卫生打扫工作。为了培养好花草,每天一大早还没有人打扫马路卫生时,杜聿明便去捡拾一些马粪来作有机肥。不料有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心血来潮,比平日早点上机关,发觉杜聿明等在大马路上拾马粪,便想到如果让外国记者看到了拍张照片到外国发表,这位全球知名的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的岳父竟落到如此地步,似乎不妥,便下令不准我们再到马路上去拾马粪。
弄弄花木,看来是很轻很轻的劳动了,谁料我竟又遇上一次死里逃生的小事。有天,一位干部指着离地两丈多高的一根枯树枝,要我把它锯下来,我便爬上树去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站立的树离枯树枝有几尺远,我不得不弯着腰,上身扑向枯枝去锯。开始我还考虑到,锯到快要断的时候,得把身子向后挪一点,并用手扶住树干,另一只手伸远点去锯,就不会摔下去。没想到这树枝枯朽多年,只锯到一半,还没等我抓住树干,就“卡喳”一声,枯枝连锯子一齐向下掉,我也跟着往下掉,不知是急中生智,还是人有从猿猴祖先遗留下来的求生本能,在离地一丈左右的时候,我一下把一根横着的小树枝抓住,那根树枝经不起这猛的一压,便由弯而折,我就飘飘落地,未伤毫发,要不是这根树枝的缓冲作用,两丈多高掉到水泥地上就不知会摔成什么样了。那位干部闻声走过来,不但不问我摔伤了没有,还用惋惜带责备的口吻说:“让你把那根枯枝锯掉,你连这根好好的树枝也折断了。”
人而不如树枝乎?我何言哉!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自从我被捕入狱后,我的妻子从原来住的三间北屋被赶到一间车房,又从一间车房被赶到一间由汽车间改成的无窗房子里,我释放后才给了两间小房。1975年3月,在押的全部战犯都特赦出来,黄维等九人留在北京,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又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把永定门东街一座四层楼房,拨给专员们使用。我也分到一套新房。当我的心情刚刚感到一点点温暖时,突然听到周总理病重的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使我感到比抓去坐牢还要难受,每天情不自禁地时时为他老人家暗中祈祷。我从不相信什么神,什么上帝,现在我却希望冥冥中真有一位主宰人类命运的神主持公道,好好保佑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操劳的好总理,早日恢复健康,如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来挽救他老人家的健康时,我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身体上任何部位的东西,直到心肝和生命,都立即献出来。有天下午,我在医院工作的老伴垂头丧气地走回来,我以为又有什么人在斗她揪她,忙问为什么这样?她哭丧着脸说,听一些医务界的人说:“总理的病越来越沉重了!”听到这消息,我晚饭吃不下,也没睡好。第二天,还得照常骑车去政协上班。在这17华里的路上,我心神不安地骑着,几次都差一点点发生撞人与被人撞的车祸。随便什么人骂我几句,我都一声不吭。我自己都弄不清,我一向骑车谨慎小心,从来没出过岔子,这次怎么会这样?
当我饱含热泪,神魂颠倒地高一脚低一脚走进专员室时,几位先到的专员一眼看出了我心事重重,都走来扶住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批斗我的事,我有气无力地一字一句:“周-总-理-病-加重了!”大家一听,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如果这不是在办公室上班,我相信都会痛哭失声的。
我们最害怕听到的不幸消息,终于在1976年1月9日早晨的广播电台一阵哀乐之后公布了。“周总理不幸病故!”那天我正在骑车去上班,这一使人震惊万分的噩耗传出之后,马路上的人都哭了,连正在岗亭内值勤的交通民警,也是带着哭声在劝骑车的人不要因为悲痛而不注意红灯,发生车祸。在平口骑车闯红灯是要罚款的。今天,民警也知道大家的心情,悲痛到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长这么大,稀奇古怪的场面见过不少,像这样一个人死去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哭的事,不用说看,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我读中国历史,有些人为某一封建统治者或什么清官一类人捧场时,说什么“国人皆为之举哀”,那完全是编造的;而今天十亿人民这种出自内心的悲痛,肯定是没有过的。
遗憾万分的是,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接见我们,有些人他老人家不但一见就叫出名字,甚至还能叫出人的别号,而他老人家逝世后,向遗体告别竟不让我们去。更令人气愤的是,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江青去向遗体告别时,连头上的军帽也不摘下来,竟傲慢到这种连常识都没有的地步。这种丑恶的表演,看的人都气愤万分。
尽管“四人帮”使用了一切阴谋诡计,不让人们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但当遗体举行火葬的那天,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在从北京医院经长安街到八宝山的路上,排得满满的,为的是向载有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告别。数也数不清的人群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十多岁的红领巾,当然更多的是中青年。那天我也挤在广播大厦附近的马路上,和大家一样,流着眼泪,等待灵车的到来。谁都知道,隔着车窗是看不到遗体的,但只要看到灵车,也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无比哀悼心情和敬意。这完全是出乎“四人帮”那一小撮丧心病狂的人意料之外了。站在我身边的一个青年,是天不亮就从通县赶来的小学教员,还有一位是从平谷赶来的农村青年,还有不少是从更远的地方赶来的。大家都那么虔诚地等待着。虽然那天很冷,在凛冽寒风中,排列在街道两旁的人还是不断在增加。当灵车远远驶过来时,一片震耳的哭泣声掩盖了汽车马达的响声。这一感人肺腑的悲痛场面,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
由于“四人帮”种种限制,不准许一些单位举行追悼仪式,但文史专员们却在一次学习文件时,举行了一次怀念周总理的座谈会,一开始就有人在啜泣,溥杰先放声痛哭,大家抑制不住一齐哭出声来。这一切说明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无比敬爱与无比怀念之情。我们这些特赦战犯,由他老人家亲自安排在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们,是不轻易掉泪的,这次也哭得那么伤心,这是我们这些人一生中少有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审判“四人帮”,我收到“旁听证”,座位是27排3号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四人帮”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
在传达中央第十五号文件的前两天,不少人已笑逐颜开,交头接耳互相传播着。人们见面时只是问一句:“听到了没有?”问的人是那么兴高采烈,听的人如果已知道了,便也报之以兴奋的微笑。因为,这些年来都在揪、批、斗之下得出了一套明哲保身的经验,消息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还是谨慎一点。
接着是政协领导人正式传达了十六号文件,同意我们这些专员也可以参加上街游行。这对我们来说,真好比被践踏得奄奄一息的小草,又在一阵春风春雨中复苏了起来。
当然,更大的喜事,使我终生感到荣幸的还是1980年11月11日和17日,我得到通知去京西宾馆,听取有关领导讲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公开审讯的有关情况,同时发给我了一张11月20日下午去公安部大礼堂的“旁听证”。这是异常难得的。我的座位是第27排3号,我按照规定提前30分钟到达。我总算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元凶首恶,一个个被押上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和审判长让公诉人员向他们宣读起诉书,一条条指出他们过去的滔天罪行。听到这些经过长期调查核实过的铁一般的事实,虽规定旁听席上的人不要鼓掌,但每个人都在内心里不断欢呼:“新中国得救了”“中国共产党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