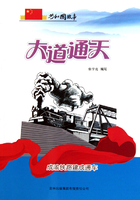张国荣先生:你好。很抱歉我不能像别的朋友称呼你为“哥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近到那一步,我不能单方面地装作和你很熟。至于你的英文名“Leslie”,我也念得不利索,我的英文发音实在太烂了。因此,我只能称呼你为——张国荣先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正是你在香江乐坛叱咤风云的时候,可那时我的年纪太小了,目光还紧紧地盯着百货商店玻璃橱窗里的玩具不肯移开,无暇顾及山那头的世界。当我后知后觉的时候,你惊天动地的三十三场告别演唱会早已尘埃落定,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乐坛也变了模样。四大天王粉墨登场,接过了你的枪,而你更多地出现在荧幕上:《霸王别姬》的程蝶衣,《东邪西毒》的黄药师,《阿飞正传》的旭仔,《倩女幽魂》的宁采臣……小时候囫囵吞枣地看完,长大后又翻出来细品,这才慢慢地知道先生你的妙处。娱乐圈里美型男很多,但你比其他的美男子多了一种东西——气度。无论出演怎样的角色,你都能保持这一份绝代公子的雍容优雅,如你的英文名“Leslie”那样风度翩翩。因此,当我读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时,一直把书中的主人翁光源氏想象成你的模样,只有先生你的长袖善舞,才能展现平安王朝的壮丽画卷。戏里戏外,程蝶衣都是跨国界的。
弹指一挥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这十年中,特首从董建华换成了梁振英,中环天星码头也升级到了第四代,自由行向内地普通民众开放,大屿山新开了全球第五家迪士尼。香港仍保持着亚洲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铺租贵绝全球,每平方尺月租2800元力压纽约第五大道。当“非典十年”的报道开始充斥着电视、杂志、报纸等媒体时,我们知道,先生的十年忌也到了。
大伙儿对先生的怀念,在这十年中是从未停止过的。有人戏称,每年的四月一日总是有那么多的人“一岁一哭荣”,而今年又逢十年,按照中国人对五、十的整数的特殊感情,各种纪念活动更是层出不穷。不少人对此冷嘲热讽,指出很多人对张国荣的思念不过是附庸风雅,实际上他们甚至连一首张国荣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对先生思念的质疑,我想黄泉之下的先生是绝不会介意的。且不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的事自然让后来人评说;更重要的是,以先生的秉性,在世之时对外界的流言蜚语早就置若罔闻了。最初和谭咏麟在乐坛斗得天昏地暗,被谭咏麟粉丝送冥币有之,上台领奖演唱被起哄被嘘被喝倒彩有之;宣布暂别歌坛,开告别演唱会,被外界骂噱头骂炒作骂借机搏场数,七年之后复出又被人家骂自打耳光,你总是一笑置之;对于狗仔队穷追不舍的同性之恋,你同样处之泰然。面对偷拍时甚至大大方方地牵着唐先生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所以,你怎么会理会现在的人们要对你说些什么呢?其实,早在二十五年前,你的《沉默是金》就宣告了沉默将会是你一生里最伟大的美德: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
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
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
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
但觉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
抹泪痕轻快笑着行
——张国荣《沉默是金》
在先生的许多歌里,我尤其喜欢先生自己的创作,包括这首《沉默是金》。作为一位多才多艺、天赋极高的艺术家,写歌对先生来说自然不是难事,且当时香港的一众天王们都有不俗的创作能力。但其中,谭咏麟、林子祥有丰富的玩乐队经验,陈百强更以创作歌手的身份步入乐坛,相比之下并没有接受正规音乐训练的先生却能在作曲上建树颇多,以“我手写我口”的方式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我们除了再三惊叹“天才”外,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2000年,香港作词作曲家协会成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ASH,先生受邀担任协会的首位音乐大使,便是先生音乐创作力的最佳印证。
先生是圈内公认勤奋好学之人,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能识五线谱、会弹吉他和钢琴的,但这并不重要。你写的《沉默是金》,作为你的创作中少有的用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歌曲,像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的姑苏慕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本应是这首歌曲的合作者许冠杰最擅长的方式,使得我在很长时间里以为这是来自许冠杰的曲子。1989年,你以告别演唱会为题,写出《风再起时》,歌中那一份从容淡泊,怎教人相信你会离开这个你所钟爱的舞台呢?
先生写歌的技巧是越发精进的。看电影《夜半歌声》,听到同名主题曲的时候,心里一直想,这首电影主题曲真是神来之笔。后来偶然知道是先生所写,从和声的表现手法来推测更有可能是先生在钢琴上边弹边唱所写出来的(不是演戏哦),更加钦佩。黄磊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是电影《夜半歌声》刚开机的某天夜里。当时他和先生走出北影大棚,在门口的传达室里抽烟,先生问他,听过电影主题歌了吗?黄磊说,还没呢。先生说,很好听的,我唱给你听。于是就唱了起来: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我能想象这个戏剧化的场景。可这对于先生来说,只是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
唱自己喜欢唱的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这是先生重返乐坛后的期望。先生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你最有生命力的歌曲都集中出现在了从艺生涯的后半程。许多歌曲都打着“非你莫属”的标签,若是交由他人演唱《怪你过分美丽》《红》或《路过蜻蜓》等曲目,总是有些怪怪的。
当然也少不了林夕。他能称得上与先生心有灵犀吗?“对我来说,张国荣的离去意味着我写某种东西的机会永远没有了,我很难说明是哪一种东西……写作的时候就像在一个没有边际、没有岸的海里游泳一样,这种体验在他逝去后就没有了……某些艺人会给我一些生命力,因为这种生命力,我可以写得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个人不在了,那一部分生命力就永远失去了。”林夕的这番溢美之辞绝不是场面话。他给许多歌手写的词,有很多都已成为传世之作,但大家会想到,这是林夕的词,只是借某某歌手的口来唱出。先生与林夕的结合却不一样,你觉得这是张国荣本来就想说的话,或者这些词藻已经漂浮在张国荣的四周,林夕只是轻轻地把它们采摘下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先生希望林夕从一句电影对白“I Am What I Am”中衍发,伸出枝干,长出叶蔓,而我们后来知道了它来自1983年的百老汇首部同志音乐剧《假凤虚凰》(La Cage Aux Folles),以及这部音乐剧更早的蓝本,一部首映于1978年的著名法国同志电影。这首歌有普通话、粤语两个版本,但先生显然更喜欢普通话一版,其流传度也最为广泛。在你的“热情”演唱会里,你在演唱这首歌之前,对所有人说,生而为人,除了懂得如何去爱他人之外,最重要的是懂得欣赏自己。你把头发散开,一身白色的睡袍式打扮,演唱时几近忘我的状态,这感觉更像是向世人布道。那一刻,你就是主。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何谓幸福,秒秒在变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张国荣《我》
从技巧来说,《我》是先生写得最好的一首歌。前半部分娓娓道来,尽量克制,没有明显的旋律起伏,大量的半音、不稳定音;在进入副歌之前,一个乐句“就站在光明的角落”像引桥,让情绪直奔高潮;在最尽兴之处,旋律又并非满地倾泻,而是在宽广的高原上空不断回响,更体现了先生所要展现的君子坦荡荡。而林夕的词让歌中没有了林夕,他已和先生合二为一,在老妪能懂的白话里,无须动用任何一个生僻字就能描绘出个体生命的壮美。合着钢琴与管弦乐队,奏出了这首属于先生的毕生最强音。但《我》是早已超越技巧的。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先生在世界走过这么一遭的永不磨灭的印记。对于“我”的思考,没有瑟瑟缩缩,也没有任何自大。先生和许多年轻人不一样,没有高呼“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不需要刻意地强调自己的存在感,以此和世界对抗。在洗尽铅华之后,与其说先生是把高度的自我评价放大到了生存哲学的意义,不如干脆说先生已经放弃了自我评价——而在此之前,先生早已放弃了他人的评价。到底什么是快乐呢?快乐是否就是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物质富余呢?快乐还有其他途径吗?我能够不管所有人的目光,只是为自己而活吗?先生说,我可以。于是他卸下了妆发、衣物、语言、心灵的一切甲胄,与大家坦诚相待。我就是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反正我就喜欢这样的我。
遗憾的是先生败给了抑郁症。十年前,大家都还不懂抑郁症到底是什么,还以为这是几句“唔准唔开心”就能打发的小情绪。纵身一跃,纵使再坚强的泡沫如你也免不了破碎的命运。十年,ADecade,就像斯蒂芬·金《黑暗塔》中罗兰所说的,“无法描述这个死气沉沉的名词中包含的变化:浪漫这一特质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它残留的肉欲的阴魂却不散;一个靠着繁文缛节和纸醉金迷在苟延残喘的世界……”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大家会更加想念你了吗?
先生若在天国俯瞰,说不准会凭歌寄意:“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纳也不必扫兴。”
2013年4月1日。
每个选择都有遗憾,每个遗憾都有转机。他还有《刚点起烟车就来》,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揭示生活中捉摸不透的戏剧色彩。
2012年5月14日,方所书店的活动策划负责人徐小姐告诉我,今晚的林一峰分享会是方所“创作者现场”创办以来,到场人数最多的一场。我这才算是小小地舒了一口气。
一个多月前,当我们确定了要办这场见面会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不是周末,来的人会不会很少啦;讲座的主题该怎么定,才可以让林一峰畅所欲言,台下听众也能乐在其中啦;现场演唱的部分该放在哪个环节,才会动静皆宜不冷场啦;等等。直到活动临开始的前几天,又传来林一峰为母亲下厨时不幸切伤尾指,到医院缝了五针的消息,那一峰岂不是不能弹吉他了!?大家还愿意来听他聊天吗?
显然,我低估了林一峰的影响力。即使他的“李吉他”和贴满了“小心轻放”的琴盒静静地躺在舞台一角,但光是听他扯家常似的把做音乐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已然让到场的300多名乐迷心满意足。林一峰也自言,很少有机会能像今晚这样,通过音乐之外的途径和大家分享他想说的话,也算是因祸得福。别忘了,除了作为歌手、发行了十多张唱片外,林一峰还是一位旅行作家,至今已出版了六本书。记得有一次他就自己的第五本书《游子意外》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这本书是否是你那些未能谱成歌曲的旅途心情札记?一峰很明确地否认:“其实我是一个搞文字的人。我童年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专栏作家,只是阴差阳错地跑去做音乐。我的歌最重要的是歌词。我的思考方式是先有概念,然后再有文字,最后才是音乐。”一峰在旅途中只会带着iPod、纸和笔,那些在欧洲街头一路弹着吉他唱着歌的画面,只存在于MV里。“我才不会带吉他去旅行呢,这么重!”所以,要不下回干脆我们就在这儿堂堂正正地做一次他的新书分享会吧!
第一次听林一峰的歌是《重回布拉格》,在十年前。有的城市只听名字就觉得有魔力,唇齿间的磨擦、声带的抖动就足以让人心驰神往。布拉格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歌德说,它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尼采说,它是神秘之代表。米兰·昆德拉以它作为帷幕,写下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布拉格之子”卡夫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旧城区的布拉格广场度过的,“这个狭小的空间限定了我的全部生活”。还有德沃夏克,这位把整个艺术生涯都献给了布拉格的音乐家。1993年12月16日,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连同帕尔曼、马友友、菲尔库斯尼、斯塔德等一干音乐大师,在布拉格斯美塔纳厅奏出德沃夏克的最经典作品,交出了一张现场录音作品《德沃夏克在布拉格》,唱片封面上的查理大桥和布拉格老城黑白照片就那样地震慑人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整座城市都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布拉格,这是只来一次远远不够的布拉格。因此,林一峰通过吉他和弦乐轻轻地吟唱着:
重回布拉格 没有变的古城
经过繁忙咖啡店 像看到你背影 但我很清醒
为了想起当天某些事 还是设法放弃当天某人
心里尚有遗憾 未免难尽兴
——林一峰《重回布拉格》
这首歌收录于他的旅行三部曲第一辑《游乐》中。翻开歌词本的第一页,便是一张布拉格的标志性建筑查理大桥在夕阳中的照片。林一峰把镜头对准了圣·克里斯托夫的雕像——桥上30座巴洛克雕塑之一,剪影充满了历史的沉淀和静谧。专辑里的歌几乎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一峰在歌词本中也标注了每首歌创作的时间和地点。《重回布拉格》当然写于布拉格,时间为2002年的7月;另一首《离开古城》同样写的也是这颗伟大的“欧洲之心”,但时间却是整整两年前,所以后来才会有“重回”一说;《未完舞曲》写于2001年8月的委內瑞拉;《Could We Ever Meet》写于2002年8月的瑞士中部小镇阿尔特多夫;《Vancouver Skyline》写于2001年6月的美国孟菲斯;《应该拍下照片》写于2002年7月的德国慕尼黑。只有《离开,是为了回来》是写于他的家,2003年的香港。从创作时间来看,这是一峰在走遍了欧洲、美洲后,对旅行这件事的总结式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