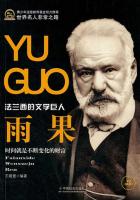国破方知人种贱
20世纪之初,最为流行的事情就是出国留洋,当时日本欺侮我们,让我们受辱,但是国人对日本倒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绝大多数都是去日本,去那里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能。苏曼珠、李叔同、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包括学军事的蒋百里蒋介石以及为革命而流亡的孙中山等,都是在日本找到栖身之地,可以说,日本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和军事基地。
1904年春末夏初的秋瑾女扮男装,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据说吴芝瑛又倾囊资助,并在北京陶然亭为她饯行,并赠一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吴芝瑛、秋瑾,后来还有一个徐自华,三个奇女子,锵锵三人行,传一段红颜佳话。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秋瑾的老公在忙些什么?一个女子,为何如此热血澎湃,为何抛家别子?从家庭的角度以及秋瑾对自身对妇女的看法来说,我们已经完全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她更有自己的想法,这可由她的诗为证——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这就是把个人的解放跟民族的解放纠结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称秋瑾是女侠,这个侠并不是她真的去杀人放火,而是她的精神和气度。不过现在也有一种佐证,说秋瑾本来是想去美国的,但后来还是去了日本,究其原因还是日本一衣带水从距离上费用上更为现实一点吧,所以她选择了日本。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她去了美国,那还会是后来的秋瑾吗?据说她去美国是想学法律的,如果学了法律,一切真的依法行事,那还会有反清之义举吗?秋瑾在准备出国之前,已经在学日语和英语了,说明她是做好了两种准备的,或者说当时还在为去哪一个国家而犹豫。同样的,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录中,完全颠覆了王廷钧的形象,在以前的描述中,丈夫是千方百计阻扰秋瑾出国的,事实上他反倒是在服部繁子夫人面前恳求过她,让这个日本女人带秋瑾去日本。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理解,既然要去游学,那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还是舍远求近吧。
到日本后,秋瑾恶补日语,并结识了如下名人,他们是就是黄兴、陈天华、陈其美、陶成章、张静江等——这些人都是中华民国的牛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先去学医,后来是弃医从文。文也好医也好,那都是一门技能吧,特别是理工之类的,而秋瑾学到的就是两个字——革命。
那么从个人的潮到时代的潮,怎么从出人头第到敢于反对朝庭,这个心理的转变,我觉得还是缺乏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吴芝瑛只是让她认识到了女性要解放自己,但这个解放可能是身体的解放,也可能是精神的解放,但不一定就是要去担当民族的解放大义,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黄兴、陈天华以及徐锡麟这样的革命者,遂使一个女子,一个如林黛玉般的女子不是只写写闺房诗,穿穿西装,而是红颜一怒为天下啊。
革命在当时的具体含义就是结社和办报,据我们知道,她与陈撷芬一道重组了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又与刘道一等组织了反清秘密团体“三合会”。注意,当时在秋瑾等一批革命志士看来,满清统治就是“夷族统治”,所谓反清复明即是这个意思。包括同为绍兴人的刘大白,本姓金,但也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改姓为刘,因为刘,因为刘邦,才是汉室的正统啊。秋瑾创办了《白话报》,发表了《演说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当时秋瑾进的是一所叫实践女子学校的,由于这是一所校规很严的学校,据称“如没有保证人的保证,就不能单独外出或单独与外人会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许出校门二次,且外出和归来都必须向宿舍管理人报告等等”。那么秋瑾显然对学校的制度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一开始是说伙食不好,反正找了很多理由。
1905年初,秋瑾回国省亲,据说也做一些类似于“中介”的事情,她奔走于沪杭绍之间,重要的史实是和蔡元培见过一面,并参加了光复会。光复会是什么组织,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暗杀组织,是以暗杀清廷官员为己任的。秋瑾随后又于当年的7月份再度赴日,因为钱少坐的是三等舱,到日本后就生病了。比较巧合的是,她这一次入的仍然是同一所学校,因为她日常居住和学习的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分校就在东京的赤阪区桧町十番地,与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会场在同一条街上,这样的近水楼台,使她的加入同盟会好像也成为一种必然,她也被推为浙江的主盟人。
这一次不是初来乍到了,秋瑾后来对实践学校的教育多有批评,甚至对校长本人也有言辞激烈的批评。当时的一个大事件是,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使得在日留学的8000名留学生大愤,秋瑾激烈地反对这个规则,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以洗国耻,并组织了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是时,取缔规则风潮起于学界,学生盛倡归国主义,瑾亦主张之,因结敢死队,瑾又为其指挥,纷扰者匝月。”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于是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2007年群言出版社版)一书对这一段有这样的记述——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公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可是第一次披露秋瑾和鲁迅之间的正面冲突。由此看来,在留日学生中也有两派,一派主张回国,一派主张留在日本学习。要知道鲁迅和许寿裳都为官费留学,而秋瑾等是自费留学,这是从经济角度讲的。而从政治理想上来说,鲁迅也热血沸腾过,也曾参加了光复会,但真的当暗杀任务落在他身上时,他还是没有去执行,这正是鲁迅可爱而复杂的一面。而关于秋瑾要杀鲁迅一事的背景,包括周作人和其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但从没有说到秋瑾和鲁迅的正面冲突,没有敢提要害的部分,可能还是为名人所讳吧,因为这俩人都是名人且同为绍兴人。而鲁迅先生本人好像也没留下片言只语,或者是我们看不到,如果照鲁迅先生的脾气,他不会不记的,至少会记在心上的。秋瑾的形象后来被先生写进了小说《药》里,这是更为深刻其实也是更为悲观和绝望吧。至于说鲁迅对秋瑾的正面评述,那也是来自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间接引述,只可略备一说。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l号租了房子,开始筹办《中国女报》,这自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只是办报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秋瑾只得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杯水车薪。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到湖南的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秋瑾娘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不和,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她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所以后来有人说,秋瑾为了革命完全是不择手段了,而鲁迅想着老母、想着朱安、想着弟弟和弟媳,即还想着人间的一切烟火,所以让他去参加暗杀行动,他必是有所顾忌的。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接下去的事情我们知道了,秋瑾回到了大通学堂,这是反清的一个秘密基地,本来她是要和在安徽的徐锡麟形成一种呼应的,秋瑾是要发动在浙江等地的起义的,但1907年的7月6日,安庆发事,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据说到了10号这一天,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到绍兴,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这一点很让人不解,她为什么要束手就擒呢?有人说她以为大通学堂不会暴露,虽然她做了转移枪支的行动,也烧掉了秘密文件,但也有人说她早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或者说因徐锡麟的就义而让她感到彻底绝望。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她必须为革命而捐躯,否则她觉得她对不起那些义士,也对不起刚刚被砍头的徐锡麟。至于她和徐锡麟之间,除了革命大义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感情牵挂,这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也好,历史的谜团即使永远是谜,也是不错的。官府来抓她时她没有反抗,抓她那天是13号的下午4点,而她被斩首是在15号的凌晨,这真是“从严从快”的典型案例了。她最后的绝笔是先写下了一个“秋”字,这本是她的姓啊,审判官再逼她写,然后才是“风秋雨愁煞人”6个字,要知道那是最热的夏天,是7月15日啊,所以秋瑾之“秋风秋雨愁煞人”已经超出了对时令季节的感慨。这一年她33岁!
今天这个年纪的女子,好多还在为婚恋发愁呢,那也是另一种秋风秋雨愁煞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