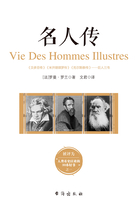后人说,许广平的才华不如萧红,那只是跟著名的女作家相比,但在那一帮女生中,许广平的才华还是相当出众的。笔者后来去厦门大学,那里也搞了一个纪念室(估计中山大学里也应该有吧),那里贴了好多许广平和鲁迅的照片。其中以鲁迅的刺猬头最为招人注意,其实鲁迅大多时候也是颇为和善且休闲的,只是不同的照片反差比较大,相比之下,许广平倒都是安安静静的,无论是单个的还是跟先生在一起的,还是不脱学生气,这可能正是鲁迅喜欢的原因之一吧。
只是鲁迅和许广平一开始的交往,还是要藏藏掖掖的。因为这里是有个名份问题的。
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许广平的身份是鲁的助教助手,因此在同一幢房子里,鲁住三楼,许住二楼。这当然是做个人看的,虽有瓜田李下之嫌,但还算是隐蔽着的。
终到上海正式同居后,许广平的身份仍是助手。同居一年多之后,鲁迅介绍许广平时,还是以助手的身份。虽然圈内人早就知道了。
朱安是妻,且还健在,那么许广平算什么呢?妾吗?那时是有不少妾,名义上的和事实上的,但鲁迅和许广平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两人相爱了,在相爱之始却还要避人耳目,原因就是鲁迅的名气太大了,那个时候就是一面大旗,而不是在其死后。所以鲁迅得小心翼翼,所以我们要看鲁迅和许的广平《两地书》。
看了《两地书》,如果我再感叹当代人不会写情书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看了《两地书》,我更以为看原作的重要性了,因为此前,包括此后,有多少人说此书的好。我也以为好,但我以为的好跟别人以为的好是不一样的。
大约二十多年前,就有老师对我们说“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时说到,鲁迅称许广平为小刺猬,许广平则称鲁迅为小白象,当时身上没有起鸡皮疙瘩,但脑子里还是闪过肉麻一词的,但是当我今天看完两地书的原件之后,肉是麻不起来的了,精可能是会神起来的了。
有一点还有注意,两地书在鲁迅先生在世时就公开出版过了,这算是比较高调吧。只是出版时涉及到一些人名等敏感问题时,个别人名都改掉了。好在先生心细,他专门抄了一部原稿,拟给海婴当礼物,这样的父爱自然是伟大的,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原信部分,所以也就更为真实了。
所谓真实,谈情说爱如果还作假,那就很无趣了。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当然,他喜欢针砭时弊,说人家的不是,这在信中也都很真实。比如说起厦门大学的不是,我估计今天厦大的人大概只把鲁迅来厦大任教当作是一件光荣且骄傲的事情。这个海边的大学,真是漂亮得很,尤其适合游泳和谈恋爱。
还有信中那么多的应酬往来,饭局,说北京的饭局比上海的要多,这在今天也是如此。还有时不时要说一下心中的不满。比如说到废名——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
其实废名也是一名家,而不是废物也,能跟鲁迅扯上或叫上板的,或者能吠上几声的,都是不容易的。
家事、系事、校事、朋友事、社会事,包括工资待遇问题等,还有自己喝酒吃饭的量,胖瘦等,先生都跟许广平说,这才是最为真实的部分。所以看两地书,跟看先生的小说和杂文其实是一样的感觉。再看广平怀孕和生育之后,称海婴为狗屁的种种,一个母亲的心思全出来了。海婴生病看病等,事无巨细,有事必录。还有两位分隔两地时,似乎作息时间也无规律,鲁迅是经常睡一觉起来后,有时是凌晨一两点,就给许广平写信了。文人生活的无规律,也可略见一斑。
很好玩。也印证了一句话,无情未必真丈夫。这一对真心相爱的人啊,当年过得是也是快乐的!虽然鲁迅不敢休妻,他说她是为了母亲,而且这种内心的隐痛,始终在他心中的。两地书中,鲁迅写到母亲的篇幅还是不少的。
鲁迅去世后,有关方面去朱安处找先生的遗物等。朱安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也是先生的遗物。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如果能写回忆录,或者是由她口述,或许会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鲁迅。鲁迅去世时,朱安在北京的宅院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她多次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据说鲁老太太去世后,她的生活更为困窘了。周作人曾劝她可卖掉鲁迅的藏书来度日,但她似乎没有这么做。面对鲁迅追随者的责问,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朱安还有另一段话,不知出自许寿棠还是谁,此话也甚为经典——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
据说,朱安是非常喜欢海婴的,视同己出,这倒是可以理解的。朱安于1947年去世,享年69岁。
所以两地书从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个第三地的点存在的,她有时像蜗牛,但绝对不是黄鹂鸟。现在想想也真是,当年怎么没有人去采访朱安呢,是没有想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看来那个年头的新闻记者,自由有余而八卦不足。
回到小白象致小刺猬的两地书,我喜欢鲁迅这样的话——
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一个人的训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你的作工的地方,那是当不成问题,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好就好在终可以在信中说——管他妈的!再看——
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那里会明白呢。我到这里一看,更确认我们并不渺小。
这两星期以来,我一点也不颓唐,但此刻遥想小刺猬之采办布帛之类,豫为小小白象经营,实在乖得可怜,这种性质,真是怎么好呢。我应该快到上海,去管住她。(三十日夜一点半)
这才是情书。此种语句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而纵观两地书,以谈人生谈教育谈苦闷始,以谈琐事谈行程谈细节终——我以为这也是人生和恋爱的真谛。用今天的话来说,一开始先像于丹说论语说庄子一样,到最后就是亲子话题了。
近年来鲁迅研究中的旁门左证也越来越多,一方不断找出新证,一方则强力反弹。所谓新证,基本都是猜测而已,而反弹的一方则腔调颇老。比如说鲁迅狎妓说,从仅有的日记中看,有如下记述:“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反驳者认为。这一妓乃歌妓,如真是嫖妓,哪有全寓十人出动的,且这是指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很显然光看这文字是站不住脚的,但反驳者由此认为,“这种谣传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人格,只能暴露出造谣者内心的阴暗。”
我倒是以为,鲁迅如果真的有过狎妓的行为,也无损于其人格。陈独秀、胡适之、郭沫若、郁达夫等,当时都有过此种行为,那后来不也都改正错误了吗?还有比如说到邵飘萍,现在还有人说他去狎妓是为了采访的需要,那不知还能不能瞒得了小学生的智商。
当然现在拿不出新的证据说鲁迅先生狎妓,那就是没有!
另有一说,比如说鲁迅日记中的“濯足”即是他自慰或其他性行为之说,猜测得甚为有趣,但反弹者也说得有理。如先生日记中大约半月或几个月记濯足二字,但在先生临终前的一周,即1936年10月12日,也记有濯足,反驳者以为那时先生在发烧,病情严重,所以无性生活之雅兴的。
还有暗恋萧红说,许羡苏是女朋友说,跟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有染等,有些已经是老调重弹了,这些跟两地书有关系吗?
我不想用鸡和鹰的比方来说鲁迅,我赞成一学者所说的,鲁迅和许广平当年离开北京,那是一次伟大而尴尬的私奔,同时我也以为,朱安堪称一个伟大而真实的悲剧人物。我所说的伟大,并不因为他是鲁迅的妻子,而是说像朱安这样的女子,是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牺牲品。
先生当年的那些女学生,在八道湾先生家时,有没有见过朱安,印象如何,有没有过交流?照理说许羡苏会跟她有很多交流的,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文字。
至于说鲁迅先生的论敌之一那个高长虹,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暗恋过许广平,仅此而已。今天来看,鲁迅先生当年论战的对手,汉奸大坏蛋的极少,大多也都是文化名人,先生不要看的那些人,比如像徐志摩,那一点也不损志摩之形象的。文人相轻,自古有之;文人抱团,也自古有之。在相轻和抱团之间,你把自己的文章做好,那就是最大的本事了。毕竟光是靠骂人,那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的。先生的小说,先生的随笔,先生对中国小说的研究,还有他收藏的拓片等,至少都是前无古人的。据说先生收藏的6000多张拓片,至今也还无人能整理出来。
鲁迅先生,个子虽矮,精神伟岸,其情之悲之烈,皆在两地书。
周氏兄弟,一代文豪,虽失和为敌,但也不影响他们各自的伟大。只是他们的后代,至今尚无往来。其中一后辈说,似乎没有必要再往来了。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当年为爱情而从日本远走台湾,也是一轰动事件,看来其精神颇得爷爷的遗传。
听说在王光美的安排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后代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我也知道这种说法是颇为夸张的,但至少代表了某些人的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