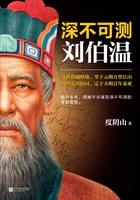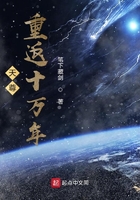作为语文老师和语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当然,夏丏尊在一师的更重要的一个身份,便是作为“金刚”的身份。查经校长日记,提及夏先生有26处之多,当时是跟王赓三老师一起作为经校长的亲信和得力干将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夏丏尊和经亨颐同为绍兴上虞人,有着乡党之情。所谓乡情,如果同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不算什么了,那如果远在省城,又在同一个单位共事,那这个感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口音、喜好等,这大概也是绍兴帮的一个外因吧,因为内因必定是共同的志向以及对世界潮流的看法和把握吧。而在“四大金刚”这个称呼以外,夏丏尊和经亨颐、陈望道和刘大白一起,还有“五四四先锋”之称的。所谓先锋,大约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么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学生之新已有施存统之《非孝》为例,那么老师之新呢?还是丰先生记了一笔——他(夏丏尊)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多数学生,对夏先生从未有过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报,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师的《校友会志》第一号上写道——人之虚伪心竟到处跋扈,普通学生之作文亦全篇谎言。尝见某小学学生之《西湖游记》,大用携酒赋诗等修饰,阅之几欲喷饭。其师以雅驯,密密加圈。实则现在一般之文学,几无不用“白发三千丈”的笔法。循此以往,文字将失信用,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矫此颓风者,舍吾辈而谁?(《学斋随想录》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
看看,一百年前一个教师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就不只是一个简单应用的问题,而是放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我们现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还有点寻寻觅觅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后的人看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文字,当看到“神马”和“童鞋”时,是不是以为又产生了新的通假?而且我们现在又以“误解”为乐趣,这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荐做舍监一样,据说他当国文老师也是自荐的结果。他还说:“文字毕竟是一种人格的表现,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热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细密的文字,先须具备细密的性格。不去从培养本身的知识情感意志着想,一味想从文字上去学习文字,这是一般青年的误解。”
从夏先生对语言文字的执著,可以佐证同是金刚的陈望道为什么后来成了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党派的领导人。至少在陈望道看起来,语言学家的贡献是不亚于政治人物的。
中国现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过中学教师的不少,像鲁迅、叶圣陶朱自清等,几乎不胜枚举,但后来一有机会就去大学或者更好的岗位了,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晖中学为何后来名人们也都纷纷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请夏先生去大学任教,他也是去任教过,但他反而喜欢教中学,这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例子,他觉得教中学更为自在。
作为语文老师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译作《爱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创办《中学生》杂志,以及后来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别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都是发在《中学生》杂志上的,今天来看这个杂志,就是一课外读物,夏先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道——
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的预备,同时又为初等教育的延长,本身原已够复杂了。自学制改革以后,中学含义更广,于是遂愈增加复杂性。
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徬徨于纷叉的岐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疑答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学生》创刊号)
注意,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课外读物的创刊辞。后来我们看夏先生发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还是在跟中学生在谈人生的,那个时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只教知识,不教文化,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叶圣陶等诸位先生看到的问题,这也正是他们要办中学生杂志的初衷。所以这还真有“徬徨于纷叉的岐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个语文老师,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家,在夏先生这些身份上,我最为看重的应是“语文老师”,因为这才是关乎千千万万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办《中学生》的时候,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叶圣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国文百八课》和《文心》,这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件造福后世的事情。因为就语文和写作而言,人们公认的有一个怪圈,即会写文章的人不会讲章法,会讲理论的人,又往往拘泥于理论而写不出好文章,这跟理工科是不太一样的。以前我们学习语法修辞和逻辑时,也有一观点,以为这跟写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看多了“文章写法”一类的书,往往提起笔来不知写些什么。那么夏丏尊叶圣陶这两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们不仅是儿女亲家,也为无数的中国母语的儿女们提供了一种滋养,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国文百八课》其实都是源于《中学生杂志》,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叶圣陶有几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们在开明做出版时才会念念不忘中学生的国文学习和写作。而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遇到的问题,在今天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变本加厉,严重的文风浮夸,不仅是语文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是头痛医头不仅没有把头医好,连脚痛等病也都出来了,而且这是全身心全系统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界思想界,似乎已经无力顾及此点了,虽有作家学者和教授也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但能像当年夏叶等全身心投入的,则还是少至甚少。因为现在的学界也是一个名利圈,中学语文的圈似乎远不如大学来得大,所以混在大学的多,能呆在中小学的就不多了。大学教授呛一声,至少网上的效应也尤如“叫兽”一般的响动了,但中学教师,除了2008年大地震后范跑跑叫了几声,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可悲之处。
而更为可悲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化人不得不再搬出民国教材来说三道四一番,殊不知天早就变了,心态也早就变了,即使是你把所有国学都拿出来耍上一遍,又还有什么用呢?把治标当作治本,或者根本不提治本,那是永远苦海无边的。
1934年的5月4日,陈望道先生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为实在——哪里有这样平易近人而又系统的书?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自己也在中学里教过五年国文,觉得有三种大困难。第一,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第二,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第三,作的方面,总想创作,又急于发表。不感到实际的需要,读和作只是为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戏。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总想创作,最容易浮夸,失望;没有忍耐而求近功,实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书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来谈写作的,这是我以前所没有看到过的,不过你看今天的新闻,包括纪录片的做法都讲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现,而这一点先生们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设置了一个老师王先生,两个学生乐华和大文,通过他们的故事,来谈国文学习。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就讲乐华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鲁迅先生的《秋夜》,他们便开始讨论“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还有“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俩学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讲给他们听,特别讲到,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写的,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一题的来历。
《文心》就是这样,一篇讲一个问题。可以想像,对于中学生而言,它是有极大地帮助的,而对教语文的老师而言,这种启发或许会更大,因为全书三十二篇,涉猎的面很广,有讲阅读,也有讲写作的,讲写作又分好多内容,而讲阅读的,又得结合当时的时势,结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很有深入浅出之感,真是得感谢夏叶两位先生这么有心这么有趣这么坚持这么认真地在做这么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而且据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此书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夏先生的女儿满姑娘和叶先生的儿子叶至善喜结连理。
而翻阅70年前的《国文百八课》(实际上是七十二课,因为没有编完),然后比较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和体系,是能引出不少新话题的。比如就所选的作者来说,那当然没有我们1949年之后成名的作家了,而在五四后的那一批作家中,像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徐志摩等当然都赫然在册的,所不同的是,鲁迅只选了四篇,它们分别是《风筝》、《秋夜》、《鸭的喜剧》、《孔乙己》,这也就是说没有选鲁迅的杂文,而选了先生的散文和小说,而今天为我们熟知的胡适(三篇)、蔡元培(四篇)等人的作品却占了比较重的比例,当然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王光祈,包括孙文、宋庆龄、陈布雷等人的文字也入选了,但是并没有选蒋中正的文字,这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也有不少跟今天的教材相同的篇目,这主要体现在文言文和古典诗歌中,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墨子》中的《非攻》篇,《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刘基的《卖柑者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魏学洢的《核舟记》、林嗣环的《口技》等,还包括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水浒》中的《景阳冈》等名篇,这也说明我们对古文名篇的看法,这七十年来的标准也没有基本改变,包括孔孟的基本篇目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也意味着爷爷辈和孙子辈学的是同一篇文章,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夏和叶的选本,起到了现代语文教育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我没有看到更早更全的选本。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他们所选的同时代的现代作家中,是以南方作家为主,包括丰子恺、沈定一(选了其代表作《十五娘》,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夏丏尊没有选自己的原创作品,只选了其译文,至于叶圣陶,那是有原创作品的。
《国文百八课》在编辑大意里说:“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
作为语文老师和教育家,夏先生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尤其是这两本书都各有侧重,包括他还跟刘薰宇合作过一本叫《文章作法》的书。一个作家来编教材,来讲如何学语文,如何写作,这目的还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学生语文学习和写作的问题。而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除了从主义上来改造中国之外,还有不少从语言的角度切入,这大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陈望道先生后来会毕生研究语法,而政治领袖如毛泽东也创造了他的那种“毛体”,因为在“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就甚为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