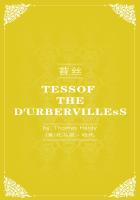与梅新的短暂恋爱使白百合陷入更深一层的孤独,她住在十八层的高楼上,除了到单位去上班,她很少出门,不愿与人交谈,没有朋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时常一个人斜躺在席子上,头发散开来铺了一席子,像一张又乱又麻的网。她想生活原来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情,让她自己给弄复杂了。她把胳膊垫到头底下,撑起一条腿来,电风扇吹过来的风从她的腿弯处吹进来,把她的裙子一掀一掀的,然后,就十分彻底地把她的裙子给掀起来。
五
白百合陷入一种坐立不安的非常状态,时时刻刻担心那架红色电话会响。从表面上说她是害怕电话铃响,实际上在她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她感觉梅新也许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给她打来电话。
一只蚊子在屋里飞来飞去,屋里开着日光灯,蚊子的行踪白百合看得清清楚楚她躺在席子上,一直盯着那只蚊子在房间里打转,这时候,她清楚地听见有人敲门,白百合趿拖鞋走去开门,打开门一看,却见门外空无一人。
这时候,电话铃却如警报般响起来。
白百合赶过去接,电话里却没有人声,白百合“喂”了半天,对方却不出声,白百合甚至听到那人呼吸的声音了,过了一会儿,那人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这种怪事接连不断地发生,白百合想,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监视她的行踪,打个电话来试探一下她在不在家。这个人会是谁呢?梅新吗?那个彬彬有礼的房主吗?还是那个常在电话里讲小凡的故事的忧郁男人毛英雄......白百合感到恐惧,她仿佛感到暗中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她。
白百合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的时候,唯一的爱好是爱摆弄各种各样的玻璃器皿,酒具,水具,孔雀蓝的玻璃瓶,大号的啤酒杯,小号的咖啡壶,她喜欢把这些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摆在地上,然后坐在当中一边欣赏一边擦拭它们。
这是一天中最宁静的一刻,手里的蓝绸子又软又滑,这是白百合从旧窗帘上扯下来的一块,面积很大,颜色虽说有点褪了,但还是很浓烈的蓝,印在玻璃上有一种很鲜湿的感觉。新窗帘已经买了,一直还没有挂上,窗子裸着,到了晚上像被挖去一块墙的黑洞,月光白晃晃地照射进来,清冷,无望,远离尘嚣。白百合只穿黑白两色的衣服,上班时间大多数只穿黑衫,白袍子留给晚上穿。她想她生活中应该多些色彩和内容,所以这次买新窗帘她索性买了最花的一种----那种大朵大朵交织在一起看久了会令人头晕眼花心跳气短的图案。
白百合觉得,每一个玻璃杯都像一个有个性的小人,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情,白百合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那样冷漠,而人与物之间反而觉得亲近。她抚摸着每一件东西,心里感到宁静,而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会无端地感到紧张、害怕、无所适从。她喜欢在办公室躲在隔板后面那种感觉,没有人看得到她,她也看不到别人。在家中反而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私人电话登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就像是私人的生活空间被人掀开了屋顶,是个人都可以往里面看一眼。
电话铃又响了。
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了一大堆莫明其妙让人肉麻的话。
下一个电话是“垃圾人”打来的,他的声音很特别,白百合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白百合仿佛看见,“垃圾人”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闪着绿莹莹的小眼睛唾沫星四溅地大讲下流话。
白百合扣下电话。
电话铃再响,白百合不接......
电话铃疯响,白百合还是不接......
她捂着耳朵赤着脚在房间里疯跑,撞倒了不少玻璃酒具,发出啷当好听的声响。
玻璃碎片四处飞溅,白百合的脚底板被割出血来,但奇怪的是她一点不觉得疼,反倒觉得痛快。白百合打开电视,看到电视里有个女人在跳白绸舞,白百合揉揉眼睛,疑心电视机出了毛病,黑白颠倒相反。果然,跳舞的女人脸是黑的。
白百合是接到恐吓电话之后失眠的,从声音可以听得出来,还是那个“垃圾人”在做怪。
“垃圾人”说,我就住在附近,我每天都在跟着你,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垃圾人”的话立刻产生了“化学反应”,白百合的心理变化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第二天早晨白百合刚走出家门,就听见邻居家的防盗门也在咯啦咯啦响,没等白百合看清楚是什么人,那边人影一闪便不见了,楼道里显得又静又奇怪,好像刚才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的发生,只不过是白百合头脑中的一种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幻觉。她现在已弄不清幻觉与真实的临界面在哪儿,她有时站在幻觉中看真实,有时是站在真实中看幻觉,这就像镜里镜外的关系一样,无论从哪边看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总是相等。
电梯里有一个男人目光阴森地看着她,白百合赶紧低下头去,觉得浑身上下冷起一身鸡皮疙瘩。白百合上班的地方离住的地方要倒三趟公共汽车,在每一趟车上都会遇见类似的情况,她感到别人目光异常,别人也觉得她目光离散、神情恍惚,她的目光一和别人的目光碰上,她便心慌得厉害,以为大难临头了,跟踪她的人也许就在身边的人群里藏着。
白百合觉得,“垃圾人”的话就像在她的生活中丢下一颗定时炸弹,所有的阴谋都已酝酿成熟,危险像定时炸弹上的秒针正在滴滴哒哒往前走,离她越来越近了。她压制着紧张情绪,故做慎静,她跟办公室的同事微笑着打招呼,别人也微笑着说一声“来啦”、“早啊”,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井然有序的样子,其实,这正常的背后越加隐藏了一种危险情绪,就像纸中包着的火,比暴露在外面的明火还要危险。
这时候,一个穿黑衬衣、打着一条血红领带的男人从隔板后面一闪来到白百合面前,他声音悄悄哑哑,面露神秘之色,道:
“昨天晚上睡得好么?”
白百合立刻警觉地瞪圆双眼问道:
“你什么意思啊?”
由于紧张过度,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抖,一双眼睛凹得很深,双眼皮上面又起了很深的一道褶,眼睛下面浮肿发青。办公室里开着日光灯,一上班就开灯是这里的人的习惯。白百合在这剌眼灯光照射下整个人薄得好像一片纸,脆弱,冷漠,不堪重苛。
小张俯下身来好像要把她看清楚一些似的,白百合看到的不是小张本人,而是小张的影子,他弓身下腰的动作可是把她吓了一跳,那影子像一匹扑过来的瘦狼,白百合神经质地吼道:
“你要干什么!”
“百合,是我小张啊,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这时候,小张发现白百合的眼神很奇怪,像看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看,他不由得倒后两步,屁股顶到了隔墙上,发出吱嘎怪响,好像什么东西在瞬间裂开来,并且裂纹还在向纵深处发展,事态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
白百合把发散的目光聚拢来,忽然间双眼一亮,压低嗓门小声问小张:“哎,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
小张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不知道白百合到底怎么了,但他却能够感觉得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想,对待这种人还是躲着点为好。他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
他这一明显回避的态度引起了白百合的注意,她想,半夜三更打电话、吓唬她、说要跟踪她的那个男人一定就是小张。小张多年来一直追求她却未有结果,所以才出此下策。激情导致疯狂的境界,这是必然的。白百合觉得自己迷乱了多年的思绪倾刻间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她坐在日光灯下,望着手里拿着的一支桔黄杆的铅笔,她晃动铅笔的时候铅笔在空气中遗留下无数桔黄色的印迹,仿佛有许多支笔的存在,但定下来一看实际上只有一支。小张便是那唯一的一支“铅笔”,其它几个打匿名电话的人统统不过是小张的化身。
这想法使白百合兴奋得牙齿格格直响,好像在一瞬间受了凉,禁不住在打寒颤,可脸上却在一阵阵地泛着潮红,用手背贴上去试试,烫得吓人。
谁都没有看见白百合那天坐在日光灯下,一动不动地呆了一整天,她不接电话,对发过来的传真视而不见,连午饭时间都错过了,她却毫无知觉。她沉醉在那种冥想意境里,脱离了周围的一切,思绪走得飞快。她想好了几套反跟踪方案,她想她一定要让那个阴险的“垃圾人”在阳光下暴光。最后,白百合抿起嘴来笑了一下,脸上的潮红像海潮一样褪下去了。
六
反跟踪行动对白百合来说有一种创作的快感,她从来都是一个生活中的被动者,精神状态孤僻、冷漠、脆弱,生活中确乏明确目标,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唤起她的激情来。但是现在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她忽然变得勇敢起来,精神抖搂,两眼放光,她爱穿黑衣服,那种黑并不是完全的黑,而是黑暗之中又有着暗哑的反光,又亮又暗,她走起路来很快,像风中摇摆着的一棵树的影子。小张每回见到她,都要找个理由回避她。而小张越是躲着她,白百合越是觉得他心中有鬼,这个互动的过程就像一个正反馈的过程,雪球越滚越大,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小张以为是因为他最近新交的那个女朋友满江红调起了一向高傲的白百合的胃口。女人就是这样,没人跟她争的时候她左一个不好右一个不要的,对男人爱搭不理,你跟她磕头作揖她还嫌你贱,可当你甩手把她撂一边的时候,她又忽然来了情绪,反过来缠你。
有天下午处里开完例会,白百合用圆珠笔捅了捅小张的胳膊,压低嗓门小声对他说:
“嗳,待会儿开完会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