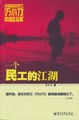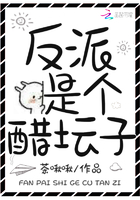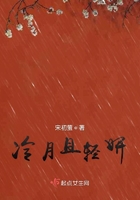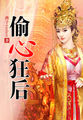夜晚的维多利亚海湾是精致飘逸而多彩的。霓虹璀璨之时,世贸中心、时代广场、会展中心……每一幢建筑物都有各自的风格。夜晚的灯光璀璨如钻石,不一样的流光溢彩,显出简洁绚丽的后现代感。香港会展中心南翼的白墙被七彩灯光照亮,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装扮使得这幢外形和悉尼歌剧院有几分相像的建筑物分外妖娆而夺目。
在太平山顶,还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全景,最好是步行上山,一路上有登山小径,蜿蜒曲折于山间密林中,路上时不时有穿着得体的香港上层居民牵着血统高贵的大狗一起漫步上山,路的两旁,散布着香港富豪的豪宅。
在太平山顶可以俯视香港全貌——可见鳞次栉比的高楼。本来,都市化的上海的街道就不太宽阔,而更加都市化的香港的街道比上海的更窄,有些楼群之间的间隔几乎只有一两米。往往走几步就是一个十字路口。香港清晨的街头是匆匆而过的白领的身影,上海白领的脚步则略微显得从容。
上海人,香港人
人是都市风情的别样演绎,看一个城市的特色还应该看这个城市里的人。
上海人是精明而讲究体面的,上海人可以家里吃不上什么好饭菜,也要穿一套体面的熨烫得没有一丝皱褶的衣服上街;香港人是务实的,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上,因为生存,有不少人要打两份工,他们为了拥有自己的楼房不惜日夜工作。金钱成了不少香港人的唯一生存目的。爱拼才会赢的香港人,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神话,所以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才会聚集着如此之多的富豪。
香港的女子并不亚于男子,都说香港女人是真正的半边天。香港很早的时候就有职业妇女了,她们是一些义结金兰、终身不嫁的女子,叫作“自梳女”,她们往往在纱厂里做女工。记得有本电影叫《自梳》,是刘嘉玲和杨恭如演的老片子,电影演绎的情节相当的真实。现如今的香港摩天写字楼里不知道有多少白领女性领着一份不亚于男人的工资,还有不少驰骋于商场,成了叱咤风云的商界女强人。不过相对上海来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女人以自己的精致和干练让香港女人羡慕。
生在香港、成名于上海的程乃珊女士曾经说过,香港白领女人比上海要足足迟了半个世纪。上海在2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女速记、女接线生。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上海首次招航空小姐,长长的队伍是美丽的奇观,最后选出的航空小姐中有三个是香港来上海读书的大学生。那时的香港女性流行北上,具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是她们向往的地方。那年月,香港女人学上海女人的打扮,她们来上海做头发,买衣服。学会像上海女人那样穿绣花的竖领旗袍,直到今天香港上流社会的女子还是很“中意”旗袍的,她们会穿着“国粹”在各种正式场合或者晚宴上出现。现如今香港白领丽人的素质和上海的也大致相同。
香港是个免税的港湾,集中着众多国际名牌的大小商店,成了上海白领女士向往的购物天堂。常常有在上海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小姐乘着香港各大商场每年春夏季和圣诞节前夕打折之际来香港,狂购一通世界名牌。她们一般攒足了钱和休假的时间,据说这样买下来,省下的钱刚好是来去的机票费。
不少香港女士爱讲上海话,这是香港最近的时尚。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金融、贸易地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两地间的亲密感。两地语言的相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两地的文化有某些类似。
香港的电影和上海的通俗小说
香港的徐克和王家卫这两个响亮的名字让电影业这个香港典型的商业文化锦上添花,而一代代风靡东南亚的影视男女巨星的名字也为这个都市增色不少。香港是一个偶像辈出的社会,小小香港,六百万人口,到底有多少歌星、影星恐怕一时谁都难以说清。路过香港大小街道,稍微好一点的城市街区中就有大牌明星——刘德华、梁朝伟、周润发、古天乐、成龙、关之琳、刘嘉玲、张曼玉、林青霞、TWINS、张柏芝们的府邸。在香港能感觉到明星如云的气息,他们的着装,享受、消费,甚至是他们的绯闻影响着多少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明星和他们的电影一起成为香港商业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香港电影业为香港提供将近6000个工作职位,单是电影录像带、镭射光碟等出口总值就将近上亿港元。香港在世界电影工业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最主要的电影输出地之一。相对香港来说,上海的电影业曾经是香港的指南,三四十年代的蝴蝶、阮林玉、周璇……影响了多少后来影视人的审美风格。时至今日有不少香港演员的祖籍也是上海。如今还有不少香港电影的取材背景是老上海。很多港星也喜欢在上海的大小秀场上出现。当今的香港电影业相对上海电影业来说有点青出于蓝的味道。和香港电影影响力可以相媲美的是上海的通俗小说。上海的小说家中虽然没有如香港金庸之类的巨擘,但是上海的小说家也有相当出名的,比如王安忆,比如陈丹燕,比如施蛰存、格非、孙甘露和安妮宝贝以及宁财神和韩寒。有不少国内人年轻人是读着他们的小说长大的。所以说,上海文人的海派风格对年轻人的影响力是不亚于香港影星的。
香港和上海在竞争中接近
相类相通的香港和上海,两座姊妹城市,不仅有合作,也有竞争。上香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中央对上海的政策倾斜也是对上海的一种扶持。政治支持,物质基础,基础建设上的扶持,将使未来的上海中心地位更加突出。而香港的成功,完全依靠私人企业,自由市场和开放精神,有私人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所以上海和香港的竞争其实是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城市竞争。
而两座相近而又不同的海港姊妹城市在竞争中更加亲密。
上海百乐门
这是一个雾蒙蒙的上海夏天的早晨。因为前一天刚下过雨的缘故,空气很是湿润,街上行人不多,即便有也是夹着公文包匆匆赶路的。我从静安寺赶去地铁口坐地铁。那段时间,我在帮上海香港商会做一期迎接香港回归15周年的特刊。
路过百乐门,一个穿旗袍夹公文包的女人,突然闯入了我的视线。满脸严肃,齐耳短发,无袖包颈,露出两条圆润的胳膊,皮肤白皙,腰肢扭摆得恰到好处,在一群行色匆匆的人当中,很是与众不同。然后,这个女人一拐,走进了百乐门。这么一大早,百乐门居然有人。
于是我很是感叹,想当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构建的Paramount 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开张典礼上,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出席发表祝词。张学良、徐志摩他们是那里的常客。陈香梅,陈纳德和卓别林夫妇都曾经走进那扇旋转门。被日本人枪杀的歌女陈曼丽的故事,让百乐门因为血腥而更加身世迷离,这所有的所有,都让我好奇。遐想着一直风月的百乐门里,是否依然有着一如往昔的别样风情。
因为赶路,我无暇顾再去追踪那个女人。
坐上拥挤的地铁,两三站后,我到了采访的地点。
那天的采访对象是上海庄臣的香港董事长。他在那里拉拉杂杂地聊了很多,无外乎香港回归后香港人变化很大,但是这几年,香港人的地位在大陆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之类的。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着。我的助理小林,一边忙着记录,一边抽空前前后后拍着照。我一边跟董事长聊着天,一边想着百乐门,以及门口的那个穿旗袍的女人。这个传说中上海滩最风月的场所,如今怎样呢?
中午,我的朋友香港钻石商人吴和他的妻子简,邀请我在他们自家开的饭店里共进午餐。他们让我点大龙虾。但是我只点了一碗香菇肉末意大利牛奶米饭。米饭很香,肯定比大龙虾落胃。简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台湾女人。但是岁月在她的脸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白皙的皮肤,完美的身材,不施任何脂粉,娇嫩得如同二十七八岁的少妇。简原来是台湾一家杂志的主编。她曾经跟我说过台湾易经大师教台湾小孩从小用耳朵听字的故事。简的传奇故事很多,她接触的传奇人物也很多。他的先生,香港钻石商人吴的人生更是经历丰富,他在百事可乐任大中华区总裁的时候,和他的伙伴一起捧红了后来红得发紫的周杰伦。而他年轻时与梅艳芳和陈奕迅同台过的照片里,那帅气的模样,至今让他无比骄傲。
直觉告诉我,眼前的这两位朋友,多多少少跟百乐门有关。我得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一点有关百乐门现在的消息。
但是午饭的时候,简没有直接跟我说,而是卖了一个关子。
晚饭后,我们在一个日式小酒吧里,和简和吴的朋友,梅艳芳曾经的化妆师香港人ALICE在一起吃烧烤,喝饮料。简也没有说什么。
直到他们两个都离开后,简才在一家欧式咖啡店里,跟我聊了起来。她跟我说,百乐门现在的老总是一个台湾人,跟她有几分熟识,但是因为道不同而未相与谋。而她的好朋友著名影星林青霞常常去那里跳舞。然后她很热情地对我说,什么时候邀请我也同去。
其实,林青霞在百乐门舞厅,被狗仔发现,和一名年轻舞师跳舞,吃夜宵的消息早已见诸报端。50多岁的林青霞,在百乐门的舞台上,旋转,欢乐,恢复了年轻时的情态。至于她的婚姻,也随着舞池的灯光而变换成了另外一个话题。
而简如此简单的陈述,让我略微有点失望。因为无关风月也没有太详尽的故事。而且这些陈述明显已经经过阳光暴晒,被岁月漂白,单纯明媚的如同简的眼睛。
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回到杭州后,有段时间常常接到钻石商人吴的微信和手机留言,一会儿要求我视频,一会儿要求我跟他的朋友聊天。我觉得他很可爱。
后来,我再度因公出差上海数次,但是都没有去打扰这对夫妇。而百乐门那扇充满神秘感的旋转门,我也没有轻易推开。我怕里面走出一个剪短发,穿旗袍,夹公文包,满脸严肃的现代上海女人;更怕那岁月的尘埃如同发黄的书页般,掀开的都是易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