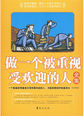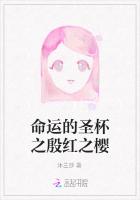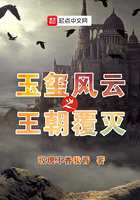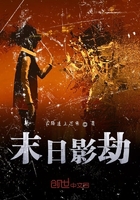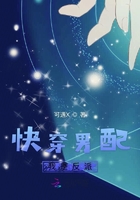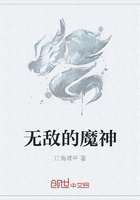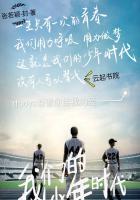他一生浪迹四海,1942年寓居香港;1950年赴印度展出作品,住印度大吉龄年余;1952年在南美巴西定居,此后又去欧美、日本写生作画……1983年4月2日在我国台湾省病逝。
他就是举世闻名的国画大师、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先生。
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他是家中的第八个男孩,原名张正权。他自幼跟母亲学画,从小就表现出这方面的天赋。
张大千12岁的时候,父亲因事错怪了他,他一气之下,和邻居家的一个小伙伴负气出走。当天晚上,他们便来到15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两个人蜷缩在人家的屋檐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两人肚子饿得咕咕叫,身上却没有一文钱,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张大千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拖着伙伴,走进一个农家小院,对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汉说:“大爷,我给你老人家画花鸟、写对联,要不要?”
老汉一听这孩子口气好大,来了兴趣,乐呵呵地跟他打趣:“收不收钱呀?”
“不收钱,就是我们肚皮饿了,画完之后给个饼吃。”
老汉更乐了,他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想看看这个毛遂自荐的孩子到底有啥本事。老汉找出两张红纸,要张大千写一副对联。张大千略一沉思,然后挥笔写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是他从城里一家饭铺的柱头上看来的。老汉一看心里一惊,他从没见过哪个小孩子能写出如此工整、秀气的字,当即叫儿子买来几碗面给张大千和他的伙伴吃。这桩新闻在村里不胫而走,老汉的院子里很快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
张大千吃饱后,兴致更高了。他在院子里的八仙桌上,时而写字,时而作画,不一会儿就创作了一长串作品。村里人开始对这个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孩子刮目相看,并纷纷上前求画、求字。
这是张大千第一次独自用笔解决吃饭问题。
1912年,从未进过学堂的张大千,背起书包,跨进了内江的华美初等小学堂。
每天晚上,他都伏在雪亮的汽灯底下,先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然后跟着母亲学习绘画。这时,他已经不再满足于画工笔画,还经常照着家里细瓷碗上的花鸟、山水,试着画一些写意画。为了使他更快地提高绘画水平,1914年,父亲决定送他去重庆曾家岩的求精中学学习。
在中学里,身穿蓝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的张大千,看上去简直太土气了,城里那些穿洋布学生装、蓄着漂亮的学生分头的同学经常嘲笑他又土又傻。
但很快同学们便改变了对张大千的看法,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绘画水平也没有人能与之相比。
4年之后,张大千离开求精中学,东渡日本求学。载着他远行的大船,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晨雾中。船儿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轻轻摇荡着,张大千的心也在轻轻摇荡……
到了日本,张大千先去东京,同在那里的二哥见面;然后又去日本古城京都,考入京都艺专,学习染织。平时没事,他最爱到市里闲逛,经常光顾书店和画店,家里寄来的钱,他大都用于购买各种美术书籍。当然,最使他受益的,还是在日本打下的写生基础。
有一次,二哥约他去富士山,他看见许多日本画家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写生。二哥告诉他,东洋和西洋学画的人,最爱用这种方式来提高绘画技法,搜集创作素材。
这以后,张大千也学着去郊外或公园写生。跟别人不同的是,他从不用铅笔写生,而是用毛笔,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求学归来,受聘于上海基督公学。不久,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当地名士曾熙,并拜在他的门下。曾熙字子辑,别号农髯,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善写隶、篆、魏碑各体。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他给了张大千很大的帮助。在良师的指导下,张大千晨晓即研墨,深夜还挥毫,书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期间,张大千突然爱上了戏曲艺术。他经常去看戏,还和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等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一生泡在戏院里的时间,仅次于作画写字的时间。
在曾熙的介绍下,张大千又师从李瑞清先生学习书法。学书之余,两位老师对绘画的一些见解,也使他受益匪浅。
在李瑞清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张大千开始研究、模仿八大山人的墨荷和石涛的山水。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他便将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绘画技巧全部掌握了,甚至还惹出了一桩以假乱真的“公案”。
有一次,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来李瑞清家与其切磋画技,在观赏石涛真迹时,黄宾虹对其大加赞扬,不想站在一旁的张大千竟然脱口说出一句:“石涛的画我也能画!”
黄宾虹抬头一看,见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便未加理睬,而是低下头继续兴致勃勃地赏画。
大约过了四五天,黄宾虹先生又来了,刚一进门,就兴致勃勃地对李瑞清说:“今天,我花钱不多,就买到了一幅石涛的真迹。”他边说边将画铺到案几上。谁想,站在一边的张大千又说出一句让人扫兴的话:“这算什么真迹,是我的仿作。”
黄宾虹气得浑身乱颤,说不出话来。李瑞清先生也气得大声斥责道:“休要无礼!”
“这的确是我画的,揭开这幅画的右下角就知道了。”张大千边说边撕开绫边,宣纸右下角果然有一个记号。这一下,两位先生都怔住了。
原来,张大千前几天受了冷落后,便关起门来临摹石涛的画,然后从中选出两幅得意之作送到城隍庙的一家画店。这两幅画经过裱褙师傅的一番认真处理,俨然成了石涛的真迹。谁想黄宾虹在逛画店时,不小心上了这个毛头小伙子的当。
当时张大千学画需要很多钱,而家里能提供的钱款十分有限,于是他便仿制了一批石涛字画,不仅笔法像,连纸绢、款识、题咏都相当考究,使人难辨真假。不少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和喜爱中国字画的日本人,甚至一些书画收藏家,都纷纷争购,这使张大千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
1925年夏末秋初,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第一次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作品以山水为主,另有花卉、仕女,不多不少,刚好100幅。
展览开始不久,便从门外传来一阵阵私家黄包车的铃声,张大千一撩长袍,兴致勃勃地迎了出去。只见上海书画界的老前辈们,正斯斯文文地走下车来。在展厅里,他们对张大千的画赞不绝口,很多人还以高价购买了他的画。
这次画展,奠定了张大千在画坛上的地位,坚定了他走职业画家道路的决心。
在这之后的几年间,张大千又在苏州、北平、南京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形神兼备,自成一家。这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震动了中国画坛,给张大千带来了更大的名声。
海明威
美国文学家
(1899—1961)
1961年7月2日,墨西哥城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这天是星期天,人们照例拥到斗牛场去看斗牛表演,这是全城人重要的消遣方式,人们期待着能有一场精彩的斗牛表演使自己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在斗牛表演的间隙,一个报童突然奔到观众中间,口中大声叫喊着,手里挥动着报纸,报纸上有两行让人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
海明威自杀!
丧钟为海明威长鸣!
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场,斗牛场里顿时一片死寂,人们似乎都被这消息惊呆了:不,不可能!海明威那么强壮有力,从不向任何人、任何困难低头,他怎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告别这个需要强者的世界?
但,这却是真的。
就在这天早晨,海明威用自己最喜欢的那枝猎枪击中了自己的头部。在非洲打猎时,他曾用这枝枪击中过羚羊、鬣狗甚至狮子,现在他又用这枝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证明了自己是坚强的,坚强得足以打败病魔,拒绝命运安排给自己的死亡方式和时间。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性格决定命运,海明威这种孤傲、宁折不弯的性格从他童年时期就养成了。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于美国北部的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名叫橡树园的小城,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的父亲克莱伦斯?海明威是个医生,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在自己的两大爱好——钓鱼和打猎上。海明威的母亲则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专门的音乐教育,她看重的是文化修养。
也许因为海明威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所以父亲和母亲都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于是他们各自都努力按自己的方式来培养教育他们的继承人。海明威3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买了一根钓鱼竿,而没过多久,母亲则送了他一把大提琴;父亲每到星期天都要带儿子去森林里打猎,而母亲却拉着海明威去教堂唱诗班;海明威过10岁生日时,父亲的礼物是一枝一人高的猎枪,母亲苦心准备的则是讲究礼仪、合乎传统的生日宴会。
对于一个天性活泼好动的男孩来说,森林、小溪和飞禽走兽显然比音乐更有吸引力,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地乱跑乱叫比在教堂里或宴会上规规矩矩地行礼更舒服,所以他常常同时得到父亲的夸奖和母亲的批评。
不过海明威显然不把这些夸奖或者指责放在心上,照样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最愉快的时候是在他家的夏季别墅度假。那是一个宁静偏僻的荒野地带,没有橡树园的那种文明的约束,他可以赤脚在地上奔跑,向飞起来的野鸭开枪,或者坐在溪水旁,等待着巨大的凸眼狗鱼上钩。而大提琴呢,则静静地倚在墙角,如果母亲不催促,他连碰都不去碰它。
也许正是这无拘无束的生活,给海明威的成长创造了文明社会中难以提供的条件。大自然的宽广、多姿、奇异,自然界生物间的生存搏斗,使他没有成长为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而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斗士。一件小事使他终身难忘。
一次在森林里,他忽然听到一阵响声,扭头看去,发现一条并不很粗的蛇捉住了一个比它粗一倍的蜥蜴,正张开大嘴,吃力地把蜥蜴往肚子里吞。蜥蜴挣扎着,每当那条蛇停下来喘气的时候,蜥蜴就挣扎着从蛇嘴里退出一些。但是无济于事,15分钟之后,那条蛇满足地把头缩回到它盘卧的地方,在它的肚子里,仍然活着的蜥蜴还在乱踢乱跳。
海明威呆在那里,像被电击了一样,忘记了恐惧,也忘记了离开。他忽然模糊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不论大小,不论强弱,都不是必然的强者和弱者,而胜利和灭亡却是如此的惨烈,又是如此的简单。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他已经决定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做一个强者。
14岁的时候,海明威升入了橡树园高级中学。他比同龄人高大,肩膀宽阔,脖子短粗,像一头小公牛。
一天,在《芝加哥论坛报》上,他看到了一则拳击训练班招生的广告。他高兴极了,马上回家请求父亲允许他去报名。像往常一样,这件事又引起了父母的争论,父亲自然是极力赞成,而母亲却毫不犹豫地投了否决票。母亲认为,海明威虽然功课很好,但他花在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太多了,而在学业上、尤其是在音乐上下的功夫太少了,更何况拳击又是那么一种危险、激烈而又难看的运动。“我的儿子以后应该是个音乐家,而绝不当一个什么拳击手。”
海明威当然不死心,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软磨硬泡,甚至以离家出走相要挟。奋斗的结果是他终于能去上第一堂拳击课了。
海明威来到拳击训练班,拳击教练看了看他,招手叫来了一个魁梧的年轻人,他叫扬?奥赫斯,是中量级拳击手中的佼佼者,拳击教练让他们俩先打两下试试。这位职业拳击家瞟了一眼海明威,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吧,我先陪你轻轻地练两趟。”海明威没有说话,戴上手套冲上去就打。
拳击家开始只是防守,或者不轻不重地出拳打几下,但海明威越打越猛,拳击家也不得不全力应付,到后来,拳击家似乎也忘了这是一次试探性的陪练,真的动起手来,大有一决胜负的味道。
一分钟后,海明威躺倒在地板上,鼻子破了,满脸是血。
回家的路上,海明威懊恼地对和他一起来的同学说:“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打?你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不过我无论如何要试一试。”
第二天,海明威鼻子上贴着纱布,眼睛底下又红又肿,又出现在了拳击场上。
20个月过去了,别的同学早就纷纷退出了拳击场,而他仍在拳击场上苦练。他一次次地受伤,头部挨的一拳,严重地损伤了他的一只眼睛,医生担心他的另一只眼睛也要受影响,母亲为此忧心忡忡,但无论她是吵闹还是哭泣都不能使海明威离开拳击场。
更使母亲发愁的是,海明威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拳击。在足球场上,也常常可以见到海明威在拼命地奔跑,在这里,他也像初登拳击场一样,奋不顾身,竭尽全力,腿撞伤、头碰破几乎是家常便饭。这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不放过让自己经受考验的任何机会。而在这种时候,母亲对他的控制力显然是越来越微弱了。
能让母亲感到一些安慰的是,海明威的功课一直很好,他不仅在拳击场和足球场上出人头地,他所喜欢的几门课程的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第一,尤其是他的写作才能,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
他的教师们后来回忆起那时的海明威,曾说过这样的话:
“他是当然的优等生,在文学表达方面很有天赋。进校头一年,他对于现实中的惊险场面就怀有无穷的兴趣。”
“我记得,他在课内写的东西完全与众不同,在我看来简直不像布置的作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海明威又迷上了写作。1917年,他在《写作园地》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赛皮?金根》,描写的是一个行凶和复仇的流血事件。其暴力的主题、简明的结构以及人物对话的方式,完全就是后来标准的海明威风格。
作为校刊的编辑,海明威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5月间写了大约24篇故事,这些故事构思巧妙,题材丰富,写得洋洋洒洒,他也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似乎有迹象表明他准备一辈子走这条路了。而他的母亲却对这一点根本不喜欢,她很重视儿子的学业,却反对他去当一个整天东跑西颠的新闻记者或者在一间零乱的顶楼上当一个饿肚子的作家。但这时她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海明威了,这头小公牛已经长大了,越来越不安于橡树园那种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生活,渴望着刺激,渴望着冒险。他要去闯世界了。
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海明威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好的冒险的机会。这时他刚刚拿到了中学的毕业文凭。他和几个同学立即赶到兵役局,要求参军。
遗憾的是军医只是朝他简单地瞟了一眼,就把他推到一边——很简单,军队不需要眼睛受过伤的青年,就算是海明威也不行。
海明威沮丧透了,但他下定决心,即便当不上兵也不再留在家里了。他简单地对母亲说要去堪萨斯找工作,就离开了家。由在堪萨斯经商的叔叔介绍,他当上了《堪萨斯明星报》的见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