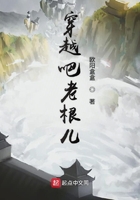???????????第七章
他们都说汪北对白靳而言很重要,甚至煞有其事地把当初汪北追白靳的事迹以及两人在一起后是如何的腻歪绘声绘色地讲给白靳听。
他默不作声地从别人口中听着他的过去,他想这感情也不过如此。似乎分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过低迷,记忆中那一年自己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过得很是颓废,甚至从心理上对活着有些厌倦。确实是厌倦,这种感觉如今回想起来仿佛昨日之事历历在目。每每想到这里,白靳总是感觉到好像有什么细节被自己遗忘,如何都想不起来。
旁敲侧击地想从莫祁口中得知一些有用的消息,莫祁告诉他的原因是当初汪北执意要跟白靳分手甚至以自杀逼迫他,初尝爱情滋味的他心理过于脆弱于是不断给自己催眠暗示忘记这些事情,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愿意在他面前提起汪北。
白靳听着这一套说辞,眼神中写满了质疑。
一个人的心理建设是很难被摧毁的,挫折承受能力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大的变动。白靳认为莫祁口中所发生的那些事并不能对自己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些事对自己造成了程度较大的伤害以至于身边的人统一口径编造了一个谎言。
白靳躺在床上想着这些日子里发生过的事情。
温姝的出现在他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一层细细的涟漪,光是静静地看着他,不用讲一句话,就有一种细腻的舒心。
他有些理不出对温姝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对她有好感。他以为只是好感而已,可是当白夫人在电话里询问他是否有喜欢的对象时,那一刻他脑海里出现竟然是温姝带着七分认真三分玩笑说“我上辈子一定认识你”的模样。他自己都有些诧异自己会突然想到她。
忘了是谁说过感情就是在一点一点想念的堆积中逐渐深厚的。
白靳向来不喜欢事情发展脱离预想的轨道的无力感,可是在想温姝这件事情上,他有些放任自己。如果始终要有一个人,白靳想,他希望是她。
她的唇比他预想中的更软,凉得没有一点温度。如果不是真切地感觉到唇上的触觉,白靳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一边轻咬着温姝的唇,一边观察着她的神情。温姝的睫毛很长,他观察到她眼睛有片刻的失神,随即瞪大了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他。
他不禁勾了勾唇角,低低笑出声:“我迷人的道格拉斯,别拒绝我,我给你时间适应,嗯?”
她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她眼神慌乱,看都不敢看他,骂了句“登徒子”就推开他跑了。
想到这里,食指不禁抚上唇,眼角温柔。拿过手机给那个熟悉的号码打过去,想着她会不会接,接了又会怎样开口,她应该还是有些生气的。不出意料地听到了“不在服务区”的提醒。
明天去找她好了。
白靳闭上眼,也许汪北是他少年一时的心动,温姝却让他有一种迟到多年的心酸。
人的思想很奇妙,白天里时刻紧绷运转,操作意识行为;夜里就像放松警惕的守卫,又如被开了锁的潘多拉魔盒,无数掩藏多年终日不见生气的秘密无声叫嚣着。
即便精神力坚定如白靳,也有放松的一刻,更遑论事物的本质并非如外界所表现的一般。
梦里浮现的景象是在一间病房。他感觉在梦里他的意识与行为是分离的,他如同一个路人旁观着梦里发生的一切。
病床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输着液体药品的女人,她的左手腕上缠了厚厚的纱布。
白靳站在病床前看着她,声音毫无暖意:“这就是你想要的?”
女人的眼角落下泪,干裂的双唇上下翕合,声音嘶哑而无力:“阿靳……是我做错了,”她看着白靳冷漠的眼神,说:“但是我不后悔。”
此刻梦境发生了变换,由病房转移到喧闹的市区,白靳看到路道中央围了一群人,他们脸上有慌张有无措有惋惜。他恍惚地走过去,脚步虚浮而无力,眼前看到的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生。她躺在冰冷的街上,受伤的地方流淌出的鲜血浸透了她的衣衫。
这一刻仿佛所有的感官都开始枯竭,他什么也听不到,眼前是一片猩红。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助与哀痛涌上心头。
胸口突如其来的尖锐的疼痛将白靳从梦境拉回现实,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窗外清寒的月光照在白靳脸上,额头上的冷汗清晰可见。他用力地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调整着梦境中尚未消失的情绪。
梦里的场景并不是他第一次梦到,三年前他还在读研的时候几乎夜夜侵袭他的梦境。白先生担心他为他联系了一个有资历的心理医师,起初的半年里经常半夜醒来,后来渐渐的不再做梦。
不知为何最近总是梦到那些事情,让他疑惑的是那些场景现实里从未发生过,而且不管经历多少次梦境,那个受伤的女生的模样始终看不清。
白靳定了定神,去看时间,离天亮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他想有再去拜访曾经辅助过自己的心理医师的必要。不止为自己,也为温姝。他不能允许自己带着过去不确定因素去接近她,这些不确定因素甚至会在某一天令她受伤。
三年前许策受父亲故友之托为其子进行深度催眠,他非好事之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就应了下来,只是他没想到催眠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对方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其意志的坚定、潜意识里的警惕是他所见过为数不多的。若不是之前所经历的事情令他的心理建设裂开了缝隙,即便是许策也无法保证全然完成催眠。
催眠的过程相当费神,许策至今都记得在那过程中那人潜意识里对催眠的极度抗拒,有几次竟然清醒将他撂倒。当催眠接近尾声的时候,许策注意到他茫然失神的双眼通红,溢满泪水。
许策漠然地看着他,说:“若你真的在意,这催眠终有一天会失效。”
当他接到白靳电话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催眠失效了,只是没料到那么快。在他接手的病例中,经过深度催眠的除非遇到契机,一般情况下至死都不会记起,更何况对白靳催眠的时候他按照白先生的要求对他的意识进行了改动。
白靳出现在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刚坐下没多久。
许策看着白靳,礼貌地一笑,“你比预料的要来得早。”
白靳听到这话后并没有什么表情变化,这让许策心里对他的评价又高了几分。看来这几年反而让他的心理建设比之前更加坚固了。
许策心里暗暗有一种遇到猎物的兴奋,他开始期待着下一次对他进行催眠的场景。
白靳注意到他眼神里莫名的狂热,心里预感到当年的事并非如他表面了解的那样简单,开门见山地问许策:“既然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作为当年接手我病症的医师,你一定了解那时我心理问题所在。”
许策胳膊肘撑在办公桌上,双手交叉,“我和你父亲有过协议,但是内容我不能告诉你。”顿了顿,接着说:“不过作为我的病人,你有权利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当初白先生找到许策跟他讲了讲白靳的情形,至于所述内容的真假他没兴趣知道。白先生说,白靳的女朋友以自杀逼迫他分手,两人发生争执导致她出了车祸断了一条腿出国医治去了,白靳从那以后日日酗酒,甚至自杀。白先生实在不忍心看白靳毁了自己就找到了许策。
许策将白先生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白靳。
白靳听着与莫祁所讲一般无二的旧事,未置可否。
回学校的路上白靳心里弥漫了一股浓浓的无力感。
我一直寻找着真相,可当他们把真相在我眼前摊开告诉我这就是真相,我该用什么理由告诉自己这些都是虚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