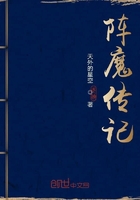我第一次知道欧冠的时候,也是春心萌动的时候。
聂晟比我年长两岁,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兄妹”。
在家里,尤其是在聂晟面前,我一向把自己看得很高,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骄傲得过了头,虽然认识是一回事,但改变是另一回事。年少的倔强就像太阳的光芒,让人猝不及防又会刺痛。就像每次我和聂晟针尖对麦芒的时候,谁都不肯先低头服软,最后常常不欢而散。
我们都是自我的,我并不喜欢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用聂晟的话来说,我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我欣然接受,虽然这比喻烂透了。
懂事那年我就觉得我和聂晟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无法改变的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从年少时,我就想象着自己的十五岁,自己会是怎样的光景。于是我会趁妈妈不在家翻出她新买的高跟鞋套在脚上,会对着镜子试穿她的裙子,来回走动,摆各种造型,幻想自己是聚光灯下的明星。
我想,我的十五岁应该是花一般的年岁。
小的时候,总羡慕邻居家的姐姐,她穿的裙子有好看的蕾丝花边,没有幼稚的卡通图案,没有装模作样的小口袋,头发也不用束成马尾,胸口的衣领微微拉低,露出好看的锁骨,美丽得如同花蝴蝶一样。
她在脚趾甲上涂各种颜色的指甲油,不穿丝袜,在鞋子里露出可爱莹白的脚指头,真是美丽极了。
我轻皱着眉头上下打量她,眉心用口红点出的美人痣皱成了水中的月亮,她弯下腰笑着问我:“小西屿,姐姐漂亮吗?”
我眼睛眨也不眨:“姐姐真是太漂亮了,可是今天又没有过年,姐姐为什么穿这么漂亮?”
她神秘一笑:“谁告诉你只有过年才能穿漂亮衣服?姐姐要去约会,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她离开后,我一直傻傻地想着她说的约会。那时候的我,读不懂约会的意思,但看她那么开心,还能穿好看的衣服,应该是和过年一样的好事吧?
约会。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词啊,我偷偷地想,她说的长大是多大,是不是也要像她那么大才可以约会?那时候的我怎么就没有去问问聂晟呢?或许他偷偷约会过,我不晓得而已。
或许只有天知道,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现在我十五岁了,已经读高一了,裙子上再没有卡通图案,虽是短发,却也不用束成马尾,偷偷拿了妈妈的指甲油涂得花里胡哨去约会了。
我要约会的那个人,是我们学校的风流人物,注意了,是风流人物。
我在课间操的时候见过一次,他迟到被老师罚站,但是他有很多跟班。我想,这真是一件很拉风的事。但是可悲的是,他和聂晟一个班。
在聂晟的眼皮底下作案,我想,我必须要假装和他冰释前嫌,这样他才不会告密。
那一天,我辗转反侧到凌晨,越睡越精神,心里百爪挠心,痒得难受,这感觉比考前综合征还要严重。我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拖鞋摩擦着地板发出沙沙的声响,我庆幸爸妈都出差去了,丢下我和聂晟自生自灭。
我想着我该怎么去贿赂聂晟。
睡不着肚子又开始咕咕叫,我打算起来弄点儿吃的,打开房门我就看到聂晟窝在沙发里看球赛。他把声音开得很小,我只看到荧光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映出完美的侧脸。
我猛然回神儿,这是一个多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其实偶尔我也是可以和他共存的,当然这种机会不多,那就是我有求于他的时候,我也是能忍辱负重地坐下来和他一起看的。虽然我完全不理解这个一堆人在画好的框框里绕着草坪跑来跑去,又推又撞,还半天进不了一个球的运动,乐趣在哪里。这跟我热衷的篮球差别实在有些大。
我款款地飘到他旁边,极其淑女地坐下,硬生生地挤出一个笑来,不用照镜子我都能知道当时的自己有多谄媚。
“聂晟,看球赛呢?”
“嗯。”
“好看不?”
“嗯。”
“那个……”
他没作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其实是无视我。我看他不主动跟我说话,就又拨弄了一下心里的小算盘,想想至少要等到一个他需要分享快乐比如进球,或者宣泄不满比如犯规了裁判却视若无睹的时候。
但是等了许久,都没有出现我设想的情节。
等待的时候我顺便做着美梦,梦到我自己变成了那个球,那么多男人拼命地追逐我,想要得到我,真是过瘾。
没想到,这真是一个美梦,等我醒来时已是天光大亮,我在沙发上睡得欲仙欲死,而聂晟早就不知所终。
他居然不等我一起去学校,事实上,他从没等过我。
我讨厌他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与我理想的哥哥简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虽说已经是春天了,天气回暖,但大晚上的他也真不怕我冻着,连条薄毯都不给我盖上。
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既然昨天晚上错过了良机,我现在就得恶补一下。
我依稀记得姜念念买过的娱乐杂志上介绍过的足球明星是叫贝克汉姆吧?这家伙好像混得风生水起,都跑到娱乐界来了。
于是,我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贝克汉姆的资料,其中一篇文字虽然短小但感情很到位,于是我像做每一期广播节目前一样,废寝忘食地背下了其中最煽情的一段。这是关于小贝最经典的一段话。要知道要接近聂晟,让我俩相安无事,我觉得比让姜念念对他移情别恋还要难,我几乎黔驴技穷。
回到家,我酝酿了一下情绪,清了清嗓子,把家当成了广播室,手握空拳当成临时的麦克风,然后带着饱满的热情,操着一口播音腔,朗诵着进了门。
“最好的时光啊,最坏的时光啊,都曾在这里,他永远当成自己家一样的地方-老特拉福德!”
这一段是《天下足球》经典语录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我花费了整堂数学课背了下来,还特地声情并茂地反复练习了好几遍,通过了姜念念那一关,我才信心百倍地回了家,我想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将换下的鞋踢到一边,聂晟不在客厅,屋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老式的挂钟还在嘀嘀嗒嗒地响着。我果断提高了嗓音,闭上眼继续朗诵:
“在足球场上,他,不是天才,没有上帝的眷顾,他只是默默地奔跑,静静地等待。美丽的弧线,让他集万千宠爱,却也让他背负了太多的本不应该属于他的责任。”
我拿出自己在学校广播站金牌记者加播音员的本事,将所有的感情倾囊而出,坚持贯彻“成全别人,恶心自己”的服务宗旨,即使这样也快把自己憋死了,气换得不顺,难度太大,一连呛了好几口口水,屋里还是鸦雀无声。
我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小碎步挪到聂晟的房门口,感情已经所剩无几,只想快点儿背完,我几乎用吼的:“直到曾经的倔强变成今天的执着,直到背影渐行渐远,只留下一声叹息。我们可以说,他,没有老,因为青涩的微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说,他正在老去,因为岁月无情,唯有时间永恒。他是宠儿,也是弃儿,他被追逐,也被放逐。他在失重后赢回尊重,他在尊重中赢来更多的尊重,他在离开时已经没有离开,他叫大卫·贝克汉姆,一个总是牵动世界的人,这一次,他是一个动人的球员!”
回应我的仍旧是无边的寂静,嘲笑我的仍旧是那破旧的摆钟。恼羞成怒的我一个纵身扑向了聂晟的房门,门应声而开。
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一股淡淡的梅香扑鼻而来,我很少进聂晟的房间,原因是男女有别。但是现在我真后悔,我应该一进门就先扑开他的房门,也不至于落到唱独角戏的境地。
聂晟,不在家!
我只好收拾好自己就快爆发的情绪,一边埋怨一边给自己煮泡面。由于激愤的情绪过了头,煮面时少打了一个鸡蛋,最后将这个失误一并算到了聂晟头上。
就在我吃着面,看着最近上映的《男才女貌》时,聂晟回来了。他的手中拎着书包,他似乎从来都这样,不喜欢把书包背在背上,也许十七岁的他已经知道耍酷。
我想到自己刚才错付的一腔深情,气就不打一处来,愤愤地问他:“你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才回来?”
他看我一眼,脸上不动声色,但我分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疑惑,要不是有求于他,我根本不会关心他的去向。但他这模样无疑又戳中了我的痛处,在接触到我愤怒的眼神时,他只愣了片刻,然后不咸不淡地说了句:“刚放学。”
一向比我早的他今天居然这么迟,要不是看在我有求于他的分上,我早就把碗扣在他头上了。
我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心里的一团火犹如燎原之势,就快把我整个人烧死了。我只好把憋屈都发泄到面上,我咂巴着嘴,把面吃得很大声,汤汁溅了一桌,整个客厅都洋溢着香菇炖鸡的味道。
他在进房门前,我注意到他的表情很怪异,估计他是觉得我不是疯了,就是在疯了的路上。
一碗面吃得连汤都不剩,想起少打的那个鸡蛋怒火又往上蹿,我竭力控制情绪,思忖着花了那么大力气不能白费了,我一定要沉住气,我要淡定,不能被他的冷漠打败。
于是,我一个鲤鱼打挺,锅碗瓢盆都来不及收拾,再次向他的房门扑过去。
房门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他若无其事的背影,我心想,这人实在太能装了。
我开门见山:“聂晟,你昨晚看的是什么比赛?”
“你不是也看了吗?”他连头也没回。
真绝,一句话就差点儿把我堵得知难而退,好在我不是一般人,我锲而不舍:“我不知道是哪两个队。”
“主队跟客队。”他面瘫似的回答,但我已经快控制不住想要扑上去掐他。
不得不承认,十七岁的聂晟沉默得骇人,与我这热情四溢的姑娘一对比,他简直可以被称为万年冰山。
我咽了口唾沫,平复了一下心绪,几乎是咬牙切齿,一字一顿道:“我问的,是哪两个队,说名字。”
他终于回头看我一眼,神情淡漠,嘴巴张了张:“说了你也不知道。”
我的自视甚高又出来了,我很不服气他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大步流星跨到他的面前,把在网上看的关于昨晚比赛的新闻一股脑儿地喷薄而出,也顾不得是不是口水四溅。
“谁说我不知道?你就是什么眼看人低。昨晚直播的是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英超豪门曼彻斯特联队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意甲豪门AC米兰队。”我吸了一口气,补充道,“是小贝拖着一条伤腿第二次站在欧洲冠军联赛的赛场上,并且以队长身份打满了全部比赛。”
我一口气背着新闻,毫不注意语速语调,就是怕一停顿就给忘了。
背诵完毕,我用骄傲的眼神紧紧盯着他的后背,也许是他感到如芒在背,终于缓缓起身,也终于肯正眼看我一眼。我内心澎湃,如滔滔江水久久不能平复,我想他一定会热泪盈眶,会一把握住我的双手,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他有了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妹妹。
然而,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脱掉校服扔在床上,两手插在口袋里:“你知道还问我?”
我忽然有种想咬掉舌头的冲动,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给我设陷阱,睁着眼睛看我往里跳,连手都不伸一下。
我一时无措,就那么傻傻地站着。
他的嘴角终于抽了抽,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又做错了什么事?还是说你打算干什么坏事?”
我被他揭穿,一时窘迫难堪至极。却又不想就这么认输,于是我用了我的另一个撒手锏,装傻充愣死不认罪。
“什……什么坏事,你总是把我看扁,就会打小报告!等我有时间我一定给你扎个小人!”
说完,我看到聂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脸皮厚得让人发指。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贝克汉姆。”他轻轻地说,说完就去厨房煮泡面了。
我的面前飘下一片残叶,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如坠寒窖。
我的约会还是照常进行,虽然我没能拉拢聂晟。但是爸妈都不在家,只要他不变态地跟踪我,我想是出不了什么大事的。
我和“风流哥”的约会地点选在了离学校一公里外的某个小餐厅。纯粹是为了掩人耳目。
我想着出门前聂晟看我时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实际上,我对今天的打扮也不是很有信心,几天前,力挺这次约会并期望我能马到成功的死党姜念念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西屿,我姐姐的这位同班同学特别欣赏温柔有才的女孩子,你一定要把握机会。你看他现在就跟班成群,听说家里还挺有钱,好歹算个富二代,以后说不定会买下座山来自立为王,你成绩不好,将来能做个压寨夫人也是好的。”
话毕,她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条路边摊上十块一条的假白金项链,又给我抹了艳红的口红,我虽然觉得恶俗至极,但总不好拂了她的好意。但介于我以前的十五年从没戴过什么首饰,这突如其来的束缚感让我很不舒服。
当侍应生将一杯鲜榨的果汁放到我面前,玻璃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才回过神儿来,“风流哥”已经从汽车说到了游戏,从CS说到了魔兽。
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要怎么接话。后来觉得确实没话可接,还是埋头猛吃比较实在,就在我伸手去拿刀叉时,手肘不小心碰倒了面前的果汁杯,玻璃杯应声碎了一地,鲜艳的果汁打翻在我身上。
“风流哥”皱眉看了看我,打了个响指叫来服务生。他的动作利索潇洒,像极了有钱人家的少爷。
我本打算说点儿什么,但他又开始继续说魔兽,我接过服务员递来的纸巾认真地擦着,像做错事的小孩低垂着头,然后默默地闭上嘴巴。哦不,是更大地张开嘴巴,风卷残云般地将美食一扫而光。
“风流哥”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没风度,自己一个劲儿地说了那么多,而我只是“嗯啊”、“哦啊”地附和,说好听点儿是回应,说不好听的就是应付。
我想我不喜欢他,是肯定的,但是,我要不要现在就走?
就在我很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问道:“聂……小西屿你平时都爱做些什么?”
我只觉得浑身打了个寒战,这才第一次正式见面叫得比聂晟还亲切,我假装咳了一下,想起姜念念再三叮嘱说这位“风流哥”喜欢“有才”的女孩子,我思来想去,着实拿捏不好这个词,于是想了个保守的答案:“平时没事儿就看看电影,听听音乐。”
“哦?真是高雅的兴趣,都是什么电影和音乐?”他似乎来了兴趣,放下手中的刀叉,微笑着将身子往前倾了倾。
我看到他的三角眼里闪出期待的光芒,我抖了一下,把最后一口肉使劲咽下,抬眼牢牢地望着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金瓶梅》,听歌就听黄梅戏或者刘三姐。”
他的笑瞬间就僵在了脸上。
我在桌子底下做了一个剪刀手。
“风流哥”结账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我回头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杯盘狼藉,感觉吃得也不是太多,他不至于给我这么难看的脸色吧?
转念一想,又觉得他应该是和我一样,都不太喜欢对方,但是作为买单的一方,这投资真是有点儿白瞎了-姑娘没捞到,还赔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我想安慰他两句,但话到嘴边还是生生咽了下去。虽说今天我们是单独出来的,难保他不会秋后算账,让他的那帮弟兄在放学的路上给我套麻袋、上板儿砖。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下来,华灯初上。我对着餐厅的落地窗照了照,本想看看出门前仪容仪表有什么不妥的,这一照不要紧,居然把班主任给照了出来。
我怀疑自己是老眼昏花了,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怎么可能碰到班主任呢?于是抱着求证的心态回头瞅了瞅,那个端坐在餐桌旁、笑靥如花的女子不是班主任是谁?
许安之,高一(16)班的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