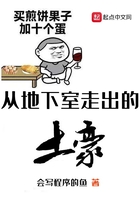我穿的的短袖精薄的不说还不是紧身短袖,而且下面还没有拽进裤子里,穿了和没穿没啥区别,丝毫起不到挡风保暖的作用,我先是感觉到皮肤像刀割一样疼,后来疼痛感渐渐降低,只是有些麻痒,最后就啥感觉都没有了。
我还以为是运动给自己取暖扛过寒冷了呢,其实是冻得麻木了,我的身子骨和那帮老毛子的身子骨没法比,他们壮实不说而且抗寒冷能力也不是我能比的,他们冬天冷习惯了我和他们不一样啊。
这场球一共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后来我们一个个累的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再也跑不动了,我们停下来吸烟,我没有烟,他们给了我一根。
俄罗斯的烟除了精神享受之外还能起到医疗作用,他们的烟刺激性特别强,味道特辣,比咱们国家老农民吸的旱烟味道还辣,我抽了一口就被呛得咳嗽,也不知道老毛子的肺是用啥材料做的,铁一般的肺呀。
身上的汗让风一吹就结冰了,我还是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除了穿衣服是的动作有些僵硬外没有其它的不适感,我对此也没太在意,以为就是累着了身体不受控制呢。
那五个老毛子也都纷纷穿上衣服,拿着篮球要回家了,临走前跟我挥手说拜拜,我也跟他们说“再见啦~”,看他们听不懂,我才又加了一句“拜拜~”
我离开了篮球场准备返回,四点钟之前赶回去,现在三点刚过,时间足够足够的,回家的这一路上我想起了我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我爸他们年轻的时候住在东北的林场子了,那时的冬天还下大雪,不像现在。一下大雪我爸和林场子里的几个好伙伴一起进山抓鹿吃。
他们都把猎刀或者是斧子别在腰间,脚踩滑雪板,划着雪进山。。
我爸说有一次他们一起进山的人中,有一小孩滑雪的时候把帽子甩掉了,帽子摔到了路边的雪窝子里头,虽然也就两三米的距离但却没有人敢过去捡。
因为这雪窝子表面看起来和正常的雪地没啥区别,但实际上这可能和流沙一样,下面的雪特别松软人一踩上去瞬间就陷进去没影了。
要不是上面的人发现的及时再加营救的及时,掉进去的人真的必死无疑。就是因为那个人是山东闯关东过来的,不了解老东北的地形,结果一脚踩了上去,没想到下面的雪竟然是空的,差点没命。)。
说的有点跑题了,之所以突然说这些是有原因的。
刚才说到我爸的伙伴把帽子甩掉了,没人敢捡,他们准备找一根长点的树枝给挑回来,就在他们找树枝的时候有一只落单的狼崽子跑了过来,见到前面有一大帮人聚在一起马上又吓得扭头就跑。
狼在落单的时候如果见到了人一般都是会逃跑的,更何况是一大帮人,而且刚才那只狼好像年龄不大,应该是一只小狼崽子,我爸他们一个个见到猎物马上把刀拔出来追了过去,暂时把帽子丢到一边了。
这只小狼崽子不知道为什么身边没有成年母狼跟着,不过没有母狼跟着最好,狼肉也能吃,狼皮也是好东西。
我爸一帮人蜂拥而上,追了几分钟之后把那只狼崽子捉住了,一个人抓着狼头,另一个人抓着狼的两条后腿把狼崽子的整个身体抻长,然后对准脖子一刀剁下去,狼就被放血了。
杀完狼之后为了防止血腥味把冬眠的熊瞎子给刺激醒了或者把东北虎之类的招来,我爸他们马上抓了一把雪把狼的伤口给冻住不让流血,再装进袋子里扎上口。
把猎物弄完了之后他们准备回去找帽子,但已经不可能找到了,因为刚才的奔波让他们已经离帽子好远了,而现在东北的山林子里风特别大,来时的印子被吹平了,找不着丢帽子的地方了。
一顶狗皮帽子挺贵的,丢了可惜,哥几个商量了一下子决定把狼皮归丢帽子那小子,让他妈用狼皮再给她做一个,也只能这样了。
后来一帮人在林子里滑雪,划了一段时间后找到了回去的路就回家了,往回返的一路上他们滑雪划了一个来小时,等回到村子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丢帽子那人在后面大哭:“我耳朵呢?”
我爸他们回头一看,王八个操!那人咋缺了一只耳朵呢?
那个丢了帽子的小子一只耳朵没了,脸的一侧光秃秃的,另一侧的耳朵打了两圈,不比猪耳朵薄到哪去,一帮大男孩都被吓坏了,手脚并用的跑进了自己家把留在家的打人都找出来了。
大人多半出去干活了,留在村里的大人不多,一个打人看到“一只耳……”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他妈是被风给冻掉的,赶紧去医院啊,另一只耳朵也要完犊子。”
用棉被把一只耳的脑袋给包住,大人开着拖拉机给送到镇里的医院了。
医生说那小子因为没戴帽子,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大风天里滑雪,耳朵里面脆骨多时间长了就冻僵了,掉下来了一点也感觉不到疼。
还好送医院送的及时,另一只耳朵倒是保住了,不过也不太瓷实了,也容易掉,日后得小心点,不能冻着,也不能娶个爱揪耳朵的老婆,要不然危险,揪着揪着一下掉了。
撤了这么多题外淡就是说人冻僵了就没感觉了,死了都不知道疼的,我那时没冻僵,因为我一直在高强度的运动,不过没被冻僵不代表没被冻出毛病来,貌似人一着凉了就容易发烧吧?
我后来也就是就是发烧了而已,不过我烧的度数有点高。
我走回到邱大爷家的时候姥爷和妹妹已经收拾好东西了,姥爷问我嘎哈去了咋才回来?给我打电话还不通,我说出去玩儿了一会,踩着点回来的。
我们是坐飞机回去,宁可提前到机场也不能完了,从来都是人等飞机,很少有飞机等人,除非你的背景牛逼到一个电话过去让飞机不准起飞飞机就不准起飞。
在准备飞机上我老是哆嗦,坐我旁边的妹妹问我咋的了?是不是恐高?我说不是,她又问我那你晕机?我说也不是,她最后说了一句相当气人的话:“第一次坐飞机不用激动成这样吧?”
我:“……”我想拍死她。
她又说:“那就是甩棍丢了心疼的?别呀,不就是根甩棍吗?姐下飞机了再给你买一根,乖啊~”
我的甩棍过不了安检,我把它仍机场里了,下飞机之后还得重新买一根。
我脑袋有点发涨,感觉自己是感冒了,也是,大冬天的我装什么逼呀?还跟着别人穿短袖在大风里打篮球,不感冒才怪了呢。脑袋涨得难受,一开始还能忍,到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飞机飞行了一段时间吧?我隐隐约约听到身边有人大声吵架,我用尽力气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妹妹和姥爷都坐在座位上,吵架的声音是身后传过来的,我想回头瞅一眼,但一点劲儿也试不出来,又睡了过去。
睡前的最后一丝意识就是:“谁这么缺心眼?在飞机上吵架?不知道有事儿下飞机解决么?”
听到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你们航空公司就是这个服务态度?啊!有你们这样的吗?当我好欺负呢?”
“先生,我再重复一遍,请你挺清楚:这是在飞机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请等飞机降落了再处理,我们会让你满意的。”在之后的就没印象了,可能是我睡着了。
朦胧中我被叫醒,我说:“到家了?”我脑子迷糊,当成坐火车了。
妹妹在一旁说:“睡的这么死呀?离到家还远着呢,因为飞机上有人闹事儿,飞机中途迫降了,咱们都得先下飞机等事情处理完了再上来继续。”
“靠,折腾人啊?出啥事了?别告诉我飞机上有炸弹?”我使劲揉眼睛,我病了,身体像不是自己的一样,我只是想不明白这病来的也太快了吧?下午冻着了现在还不到晚上咋就不行了呢?
“你摸摸你哥脑门,我是不是发烧了?现在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
我妹妹用手背抹了一下我的额头,摸完之后把她吓了一跳:“哥,你身上咋这么烫?你发烧了。”
“嗯,我知道,从上飞机就开始了,难受啊。”
“跟姥爷说下飞机买点药先吃吧,现在已经到中国了,找家药店不难。”
我问:“飞机上没有感冒药吗?”
“马上就要降落了,都不让随便走动,就算是有药谁给送来?”
飞机降落之后我强忍着头痛下了飞机,跟随者人流在候机大厅里等待,我也不知道到底出啥事儿了,搞得飞机都提前降落了。
我姥爷要给我买药去,我说我没事,不用了,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买个药挺费劲的,再说我们现在都在在候机大厅里等着呢,买药出去再回来还不够这麻烦劲儿的呢。
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想到我能烧到四十多度,也没想到我的烧发起来了愣是一星期都没退下来。
在等待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妹妹给我讲了飞机降落的原因,我也正好分散注意力让自己不是那么的难受。
我睡过去之后在我们的后座有一女乘客起身上厕所,可能是第一次坐飞机啥也不知道,上厕所没把门锁好。他进去之后紧接着又一个男的也上厕所,那男的可能是憋坏了,急急忙忙的推门就进,结果……
厕所里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我当时睡得太死了,那女的的尖叫声我都没听见。
那女的从厕所里跑出来,和她一起坐飞机的老公当时就急眼了,解开安全带站起来抡拳头就打那个上厕所的男的。
闯厕所的那男的想跟女的的老公好好解释解释,是女的上厕所不锁门在先,要说责任也不完全在自己,再说了,自己也不是故意的,纯属意外。
那女的的老公根本就不听,直接上去就拳打脚踢,空姐过来劝和没用,后来副机长也过来了,副机长只有一句话:“现在是在飞机上,有事情等飞机降落了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