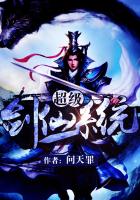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C·D·奥·威尔森
诺贝尔章程的第二段载明,“文学”应不仅只包括纯文学,“而也当包括在形式或内容上显示文学价值的其它著作”。这个定义使诺贝尔文学奖得以颁给哲学家、以宗教题材为中心的作家、科学家与史学家,只要他们著作的呈现形式有杰出的艺术性,其内容有高度的价值性。
瑞典学院今年必须在许多出众的名字之间做选择。最后的决定是赠予普鲁士皇家科学院18位院士联名推介的特奥多尔·蒙森。
蒙森70岁生日时,Zangemeister所收集的蒙森已出版文章目录共920篇。蒙森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是编辑《拉丁铭文集》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1867—1959年);虽然有许多渊博的学者相助,这仍是一项海格立斯式的重任,因为十五册之中不但册册有蒙森的文章,而且全集的组编乃是他特殊的成就。蒙森,这位在学术界屹立不倒的英雄,在罗马法、铭文、钱币学、罗马编年史与罗马通史方面都有原创性研究。即使对他抱有成见的评论家都承认他在伊比吉亚(Iapygia)的铭文上,在阿庇亚·凯卡斯(Appius Caecus)的片简上,在迦太基的农业上有同样的权威。有教养的读者之认识他则主要是透过他的《罗马史》(Romische Geschichte.18541855年,1885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而瑞典学院之所以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蒙森,主要是因为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于1854年开始出版,到目前为止,第四册尚未问世,但1885年则先出版了第五册,这是对罗马帝国治下的各行省的杰出描述,由于这段时期离现代不远,因之其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作为当代的借鉴,而可以跟诺贝尔章程中指陈的现象相比照,因而使各位对全书的评估可以有一个起点。蒙森这部业已译成许多外文的著作,既有彻底而广包性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蒙森结合了丰富的资料与精确的判断、严格的方法与年轻的活力,而又以艺术的形式将它呈现出来,这是惟一能使描述具有生命与具体感的方式。他懂得如何分别麦子与糠皮;而他渊博的知识与组织能力之可佩,正不亚于他的直觉想象力,不亚于他将细心研究过的资料以活生生的画面呈现的力量。他的直觉能力与创作能力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填平了。在《罗马史》第五册,蒙森曾说,想象力不仅是诗歌之母,也是史学之母,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其实已经感觉到其问的关系。真的,两者的相似非常大。兰克(Ranke)的客观态度相似于歌德的伟大沉静,而英格兰把马考雷(Macaulay)葬于西敏寺的诗人之隅乃是正确的。
蒙森用简略的几笔就勾勒出罗马人民的性格,显示出罗马人对国家的服从如何跟儿子对父亲的服从有关。他以杰出的技巧展开了罗马发展史的画布。从最初的蕞尔小族至君临世界的大帝国。他描述了随着帝国的成长,陈旧而顽固的体制已经如何不再能适于新的任务;“公民议事集会”的主权如何渐渐变成了一个虚有其名的东西,只偶尔被政治煽动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元老院早先如何尽心尽力注意公共事务,但这衰老的贵族寡头政治一旦履行了义务之后,又如何未能符合国家对它的新要求;而不爱国的资本主义又如何经常在政治的投机行为中滥用其力量:自由农民的消失又如何导致整个共和国的灾变。
蒙森也向我们论证执政官的经常更换如何阻碍了战事的一致性,因而使罗马人终于把军事指挥官的任期延长;而同时,将军们又如何日渐独立,凯撒主义如何变为必需,其原因甚多,但最重要者则为缺乏可以跟实际帝国相配合的制度;而绝对专制在许多情况下又如何比寡头统治造成的困难较少。在这位史学家不容情的眼前,虚假的光辉消失了,麦子与糠皮分了出来,而蒙森像他所赞扬的凯撒一样,具有清明的眼光,可以看出实际的需要,可以免于幻象的蒙蔽。
有不少的评论家对蒙森的《罗马史》提出批评,他们的批评或许并非完全不当。他们认为蒙森有时被他的天才牵着走,做下主观的、强烈的判断,尤其是对那些拥护垂死的自由的人士,反对凯撒的人士,以及在艰苦的时期于两派之间摇摆的人士。有些人批评蒙森,他在天才破坏法律的时候,仍对天才表示赞许,他曾说,在历史中并无所谓叛国罪,造反者可以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然而,我们却必须强调,蒙森从没有推崇过赤裸的暴力,而只推崇为国家崇高的目标效劳的力量;我们也必须记得他言之凿凿的信念,“推崇被邪恶的精神所败坏的事物,乃是对历史精神的罪恶”。也有人批评蒙森有时用跟古代状况并不十分相合的现代用语来指陈古代人物与现象,但这宁可说是蒙森博学的结果,而不是出自他的想象。若说它在陈述方面增加了太多的色彩,则它同样也增加了新鲜感。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蒙森并非历史唯物论者。他赞美波利比阿斯,但他也谴责他,因为他忽视了人的道德力量,因为他的“世界观”太机械化。在谈到具有使命感的革命分子C·葛拉丘时,他说,除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由共同的道德精神相缔结,否则任何国家都是建立在沙滩上。他认为健康的家庭乃是国家的核心。他严厉谴责罗马的奴隶制度。他看出,一个仍有活力的民族可以如何因灾难而振奋,他认为今日意大利的团结乃是高卢人在罗马烧起的一片火海所导致的结果,正如昔日雅典的自由生于波斯人对卫城的劫掠烧杀。
博学、活泼、善嘲讽的蒙森对罗马的内政与外交、宗教与文学、法律与金融以及风俗习惯,都做了动人的阐述。他的阐述是精彩的,凡读过他的《罗马史》的人,便不可能忘记他对特拉西曼湖之战、坎奈之战、阿勒利亚之战及法萨拉斯之战的记述。他对人物的描写也同样活泼。他用鲜明的线条勾画出“政治煽动者”C·葛拉丘:勾画出最后阶段的马利阿斯,那时,“心智的错乱已经变成了一种力量,人为了避免眩晕而投入深谷”;勾画出苏拉,给了我们无以伦比的生动画像;勾画出他心目中的罗马理想人物朱利阿斯·凯撒;勾画出汉尼拔,以及扎玛之战的胜利者西比奥·阿夫利坎纳斯,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次级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在巨匠的手中只略略几笔便已跃然纸上。
史学家Treitschke由于这些画像,认为《罗马史》是19世纪最佳的史学著作,而蒙森笔下的凯撒与汉尼拔则必会激起每个年轻人、每个军人的热情。
蒙森具有各种不同的才华。他是个渊博的学者,头脑清楚的资料分析家;然而,在做判断的时候他又可以是热情的。对于政府的内在运作与经济的复杂,他极为详尽的描述,而对战争场面于人物性格他又同样写得精彩生动。或许,最根本上他是个艺术家,而他的《罗马史》是一部庞大的艺术作品。“纯文学”,这文明的高贵花朵,在诺贝尔的遗嘱中得到肯定,而蒙森则是此种花朵的主要代表之一。当他把他第一册《罗马史》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他写道:“工作是艰巨的”,博士学位50周年纪念时,他则热烈的说到学海的无涯。但在他完成了的著作中,不论工作是多么艰辛,却已都不留痕迹,而这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之本质。读者走到安全的地面上,不被浪花濡湿。这伟大的著作屹立在我们面前,如同钢铁所铸。
艾克顿勋爵在剑桥发表就职演讲的时候曾说,蒙森乃是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因这个观点,蒙森理当获得一个“文学”大奖。《罗马史》的最新德文版刚问世不久,内容未做修改。这部著作仍保持着它新鲜的活力,它是一个纪念碑——尽管它拥有的不是大理石的柔美,而是青铜的永久性。书中处处可以见到学者之手,但亦同样可以见到诗人之手。事实上,蒙森年轻时就曾写诗。1843年的《三友之歌》(Liederbuch dreier Freunde)就证明了他本可成为缪斯之仆,只因环境才将他的一生做了转变,照他自己的话说,是“诗与文,并非每个蓓蕾都会变成花朵”。史学家蒙森是特奥多尔·斯笃姆(Theodor Storm)的朋友,是莫利克(Morike)的赞赏者,即使在他年事已高的时期,他仍把意大利诗人卡度齐(Carducci)与贾可撒(Giacosa)的诗译为德文。
艺术与科学的工作者常显示出精神的年轻。蒙森既是学者又是艺术家,85岁的高龄在工作上仍保持着年轻的活力。即使晚至1895年,他仍对普鲁士科学院会报提出重要的文献。
诺贝尔文学奖奖牌刻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在聆听缪斯神的灵感。蒙森是个老人了,但他具有青年之火,而当我们披读蒙森的《罗马史》时,最能了然克莱欧乃是缪斯之一。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历史的典型曾引起我们的热情;而现在,当我们年纪已长,再重读这些典范人物的史迹时,我们又重新感到他们的力量。史学的知识同伟大的艺术结合,便有这样的力量。
由上述的原因,我们今日从艾利克·葛斯塔夫·盖杰(Erik Gustaf Geijer)之国向特奥多尔·蒙森致敬。
注:蒙森未发表正式的致答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