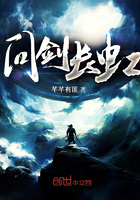她扑通一声,突然跪下了。看着君茹姐,我真的很想哭,恨不得冲过去,扶她起来。也恨严振宇,他是下水道,这会儿喝口水怎么就那么难?
严振宇不冷不热的说:“你起来,洋灰地,凉!”
“我知道我不配。”君茹姐,双手把茶捧到他唇边。
严振宇笑了一下,有点气苦说:“那里。不配的是我。”接过杯子说:“你起来,犯不着这样。”
君茹想扶着床站起来,蓦地又缩回手。严振宇朝她伸出了手,可她撑着自己的腿,慢慢站了起来。
严振宇举到嘴边,一口气灌下去,喝完,他呲牙咧嘴,艰难咽了口唾沫,瞥一眼杯子,佩服的说:“够狠!连暖壶都灌了碱水。”碱水是啥滋味?他没喝过,又怎么知道?君茹姐姐也是哭笑不得,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严振宇捂着胃,眉头紧皱,好象很难受,冲君茹摇手,示意别再理他。他躺下,头刚枕上枕头,砰的一声,顺着枕套,水哗的流出来。
严振宇跟诈尸一样,刺棱坐起来,警觉的跳下床,撩枕巾,翻开枕头套,没有枕芯儿,打里头拎出个破气球,水淋淋的。若不是我意志坚定,真要忍不住,会笑破肚皮的。
严振宇往凳子上一坐,笑了一声,突然呼吸急促,艰难的咽唾沫,喉咙一上一下的滚,终于一口气没吊住,咳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一声比一声来的深,背弓的象只虾米。最后已经没声儿了,他捂着嘴也堵不住咳出来的血。
君茹姐姐吓坏了,从盆架上,抽条毛巾,跪在他面前给他擦,他缓过气来,猛的推开君茹,吼了句:“滚!你滚!”
君茹姐姐坐在地上,只是哭。
严振宇站起来,不想他直着眼,就奔我这儿来,太快了,立柜门,猛地一下,给拽开,眼前骤然大亮,他一惊,好象整个屋子都跟着一震。
我望着他,先犯一阵晕,君茹也探头,吃惊的瞪着我。我紧紧抱着自己的腿,恨不得越缩越小,能象耗子一样,有个缝儿,就能溜之大吉。
很长很长时间,他们都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我熬不住了,呜呜的哭起来。
是严振宇把我抱出来的,我被放在地上时,还有点怕,膝盖都在打颤。他拎出油布包,我刚骑了半天的,从里面掏出个大望远镜,冲我晃了一下说:“给你的。”不待我接,就撂在桌上。
我急忙跑去,抓在手里,很宝贝的抱在胸前。
严振宇拎起包,义无返顾,大踏步走去开门。君茹眼睁睁,却不敢拦他。
振宇开门的一刹那,骤然僵住了,不知道黑灯影儿里,站的是谁?
还是君茹哀哀的喊了声:“哥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君苇大哥。
“君茹!起来!” 君苇大哥喝令道:“你给我站起来!”
“你小点声儿,想让咱妈听见?” 严振宇低声说。
君苇一头撞进来,严振宇来不及闪身让路,被他撞的后退了几个趔趄。
君苇拽起君茹,按耐着火气说:“振宇,我妹妹那里不对,我求你担待她……”
君茹姐姐,泪莹莹哀求:“哥……”
“你住嘴!你贱——呀你!” 君苇恶狠狠瞪着君茹。君茹姐吓向后一缩。
“严振宇。”君苇沉着脸,沉声喝问:“你怎么意思?”
“大哥。” 振宇转过身,对着君苇的后背说:“该担待的,我担待。不该担待的,我也担待了。你还想叫我怎么样?”
君苇冷不丁回身,狮子一样,扑去,揪住振宇的衣领,:“我问你?我妹妹,她干什么了?她有什么,让你不该担待的?”说到气头上,拼尽全力把他猛的一推,振宇连同手里油布包,都摔了出去,重重撞在楼梯的侧帮上。
君茹忙喊:“天雯,快去……”
我急忙跑到振宇跟前,还没怎么,后脖领子,就被君苇大哥一把薅住,稍一用力,我就摔个屁股墩儿。
君苇还饶振宇不过,横身将他逼住,指住他的脸,咬牙切齿的道:“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告诉你!咱没完!” 君苇的样子就象严刑逼供。
“你让我说什么?” 严振宇笑了一声,“绿帽子,扣脑袋上,我都忍了,你还让我说什么?”说到后来调门高的有点离谱。
君苇不及听完,一巴掌甩在振宇脸上,严振宇斜眼看着他,说:“你打吧,我不还手,我们有纪律。”那样子特别革命,跟电影里的底下党一样,斗争的有理有节。
君苇大哥眼都红了,在黑灯影下,熠熠放光。拳头已经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抬脚连踢带踹,逮哪是哪。严振宇也不出声,咬牙忍着,宁死不屈。
君茹踉跄着跑出来,几次扑到君苇身上,都被他搡开了。君茹姐没办法,不顾严振宇讨厌她,扑到他身上,护住他,哭道:“他有伤!他身上有伤呀!”她自己身上还挨了君苇好几脚踹。
君苇听见了,不在踢人,拽起君茹,裂开严振宇的衣服,露出里头的绷带,还渗着血。
君苇大哥,后退了两步,半晌突然说:“兄弟,我就这么一个妹妹,这么个老妹妹!交给了你……”听上去很可怜,好象什么好东西,死活舍不得给人。
“你还有妹妹。我呢……” 严振宇惨笑道。
“哥哥。”君茹还是哀求,“你放了他吧,他还得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还要赶到军区医院复查……”
“傻丫头!”君苇愤慨的指着严振宇,看着君茹,又恨又心疼:“他那么糟蹋你,你还护着他?”
君苇恨铁不成钢,气的直跺脚“你又没短儿在他手里?你干吗这么贱?”
“哥——!”君茹叫的,有点撕心裂肺:“我贱。我就是犯贱!”
君苇大哥非常艰难的,明白了什么似的,揪过他妹妹的头发,狠狠扇了她一记耳光,君茹惨叫一声,哭道:“哥哥!我是你亲妹妹!好歹你也给我留点脸!”
君苇不仅火大,反到加个“更”字。他扳过君茹的脸质问:“你犯的什么贱?让人家这么糟蹋你?说呀你!”
严振宇趁这个空档,扶着栏杆,站起来,他喊声:“大哥。”心平气和,说:“我该走了。我有话跟你说。”君苇扔了君茹,转身盯着他,好象振宇是仇人。
严振宇望着他说:“你记着,那孩子,不许他姓我的姓。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声音不高,可字字句句,咬的人生疼。说到“死”,他的嘴横着一扯,好象在笑。
严振宇提上的油布包,转身就走,下台阶时,有点打晃,自己站那儿稳了稳神儿。这回是真的,义无返顾的走了。
那一瞬,我有点心酸,紧紧抱着我的望远镜,几个箭步窜上楼梯。二楼的拐角,一直到我家阳台,密密匝匝,站满了人。我挤进人丛,跑到阳台上,白天,从这可以看见胡同口,用望远镜还能看的更远。可是,半夜了,没路灯,底下一片黢黑,没边儿没沿儿,深不见底。
注释:没边儿没沿儿是天津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无边无际。
苇遭劲风凋
我回头,看见君茹姐姐,被他哥哥揪着头发一路拖到楼上,扔进屋里,君家的门砰的关上。然后传出凄厉的叫声,君婶的哭声。
那些人,赶忙拢到他家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拿眼神互相交流,还有人偷偷的笑。我真的好恨!
突然,一声大吼:“耗子!耗子!下去了!”林天雨(大概是他,林天雷是不会干出这路事儿的)吓的连叫带跳,指着楼梯,“快逮耗子!”
楼下的人,一听就炸锅了,胆儿小的一路尖叫,打着滚就跑。胆儿大的就问:“哪了?哪了?”“跑了,院子里……”
一只耗子,把这帮看热闹的人冲散了。
楼里头,出奇的静,君茹姐姐的惨叫声,听来也格外的真。
转过天来,晚饭刚吃完,碗筷还没收拾呢。就听见,楼下又闹开了,打,砸,摔东西,哭的哭,喊的喊。
不一会儿,就听楼梯响,君姨哭着爬上来,嘴里喊:“他林师傅!出人命了……”
她到阳台上,一下子跌在地上,我爸爸愣了,赶紧扶她坐下,劝她别急,慢慢说。
君姨满脸是泪,哭着说:“我不活了!两个冤家呀!不叫我活呀!”
楼下就传来君茹姐姐的惨叫……
爸爸反身下楼,砸门那个节奏,跟打架子鼓似的,厉声喝道:“君苇!混蛋!开门!你想把你妈气死?”里边没回音。
爸爸急眼了,狠狠踹了一脚,骂道:“王八羔子!你妈那儿都犯病了!还不滚出来!”
这招儿,高!实在是高!象俺老爸这种大老粗,平时说话都不利落,没想到瞎话编还挺溜。
君苇大哥是孝子,门开了,他急皮怪脸的冲出来,一见我爸爸,就问:“我妈妈她……”我爸一脚给他踹回屋里。
君茹姐姐瘫在地板上脸都肿了,嘴角鼓着,眼眶都打裂了,我真的不明白,她犯了什么错,他干吗下这么黑的手。
爸爸一见跳起来,照着正要往起站的君苇,又踹了一脚,指着他,喝道:“那是你妹妹!你小子……也敢下的去手!说你嘛好呢。”
“林师傅!你问问她,她干的破事!老君家的脸让她给丢尽了!”君苇激动的嚷。
“她干嘛了?犯法吗?就是犯法,你也不能打死她。”爸爸转身,弯腰搀君茹,可她已经起不来了,爸爸只好,打横抱到她自己床上。
君茹轻轻的说:“您别搭理我。让他打死我算了。”
爸爸说:“傻话!年纪轻轻,有嘛过不去?你妈妈养你这么大,供你上大学,你倒好……”君茹突然捂着脸,闷声闷气的哭开了。
爸爸叹了口气,在不好说什么了。回头见我跟来了,说:“跟姐姐好好呆会儿。”我点点头。
爸爸去外屋了,对叉着腰,有气没地儿撒的君苇说:“别打你妹妹了,让人看笑话儿。”君苇苦笑道:“脸都丢大发了,还怕人笑话!你问她,还知道要脸吗她!”他指着君茹姐姐,气急败坏。
爸爸冲他连连摆手,语重心长的说“你呀,上去!把你妈叫下来,你们娘俩儿,合计合计。把事儿了了。说别的,现在都没用!”
君苇大哥,硬生生咽下这口气,上楼,不一会儿,扶着哭哭啼啼的君婶进来了。
君婶直奔君茹姐姐这屋来,哭着数落道:“死丫头呀!不省心的东西!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命苦呀!老头子呀!你走的怎么这么早呀!让我跟你去了……”
她倒了口气儿,接着哭道:“也不受这份罪了呀!可叫我怎么好呀——!”每一句都有个拖腔儿,象哭丧,夸张了点,可也催人泪下,于是我也跟着哭了。
君茹姐姐突然坐起来厉声道:“我死!我去死!”
君婶,愣住了。君苇跳进来,道:“你还有脸说!你死去!海河没盖盖儿,跳呀!你怎么不死呢?”爸爸揪着他的衣领子,急道:“你说的是人话吗!”
君婶回过身来,一头撞在儿子身上,道:“你个挨千刀的!她跳河去,你舒坦呀?”
君苇心软了,唤了声“妈……”
君婶不依不饶,在君苇身上一通乱捶,君苇比她高出一个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君婶晕了,跌到儿子怀里。君苇抱住君婶,把她平放到外屋炕上,急忙拧了把毛巾敷在君婶脑门上。她抓起毛巾扔了,挣扎着坐起来,君苇急忙跑到她身后,给她靠着。
君婶哭道:“他林师傅,这日子怎么过?我可怎么办好呀!”
爸爸叹了口气,点支烟卷,闷闷的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