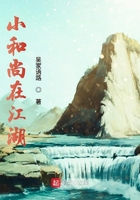小弦再被水柔清在“小鬼”后面加上“阴险”二字的评语,怒气上涌,差点就要出言应战。总算他修习《天命宝典》多年,还能保持冷静,心想若是万一输了以后听这小丫头的号令可真是要命的事情:“你别那么霸道,我,我下船之前必能赢你。”他听花想容说过船将沿长江东下,至岳阳进鄱阳湖转湘江,至株州才下船行陆路,至少还要再走十余天的水程,料想自己这十多天专心学棋,怎么也不会输给水柔清。
“好,一言为定,是男子汉就不要反悔!”水柔清再狠狠瞪了小弦一眼,转身回自家舱中去了。
段成看看散落一地的棋子,再看看小弦:“你真是第一次学棋吗?”
小弦木然点点头。脑中犹闪现着水柔清最后瞪自己那一眼中隐现的敌意,不知怎么心中就后悔起来,倒不是怕输给她,而是怕真与她做一辈子的对头。想到前日在船尾牵她的手说起彼此身世的情形,心中一软,恨不得马上找她认输,只要她不要再这样如当自己是什么生死仇人一般……段成倒没有想那么多,低声劝道:“她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平日都让着她,谁也不愿真惹急了她。”看小弦表情复杂似有所动,又道:“要么我帮你去说说,有道是好男不和女斗,为一盘棋弄成这样又是何苦?再说你不是还要找景大叔治伤么,景大叔可最疼她了……”
小弦本已意动,但听到段成说起治伤的事,顿时激起一股血性,大声道:“景大叔疼她就很了不起么?就算我伤重死了也决不求她……”
水柔清迥异平常的声音遥遥从门外传来:“少说废话,抓紧时间找段老三多学几招吧。”
段成一叹不语。
花想容知道此事后亦连忙来劝小弦与水柔清,但这两人均是极执拗的性子,一意要在枰上一决高下。虽只是赌气之举,但心目中都当作是头等大事,别人再如何劝都是丝毫不起作用。
当晚小弦就专心向段成学棋。小弦本以为棋道不过末学小技,以自己的聪明定然一学就会。试着与段成下了一局才知道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上手简单,下精却是极难,不但要审时度势,更要凭精深的算路料敌先机,往往一手棋要计算到数十步后……段成亦是左右为难,他只比小弦大五六岁,自是非常理解这种小孩子的好胜心理,既不忍让小弦如瞎头苍蝇般盲目研棋,又怕真要教小弦赢了水柔清她定会记恨自己。可转念一想,水柔清虽是败给自己,但棋力确是不弱,小弦只凭十几天的工夫要想赢她谈何容易?念及于此,教小弦时倒是尽心尽力,丝毫不藏私。
第二天水柔清也不找段成下棋,自个呆在房中生闷气。小弦正中下怀,便只缠着段成不分昼夜的学习棋术。只是苦了段成,一大早睁开眼睛便被小弦拉到棋盘边,路上途经的什么白帝城三峡等全顾不上看,还要时时对水柔清陪着小心,对此次鸣佩峰之行真是有些后悔莫及的感觉了。
小弦从小被许漠洋收养,许漠洋怜他身世,从不忍苛责于他,就是学武功亦只是凭着一时的兴趣,这一生来到是头一遭如此认真地学一样本事。他也没时间去记下各种开局与残局应对,唯有一步步凭算路摸索,几天来没日没夜地苦思棋局,便连睡梦中也是在棋局中竭精殆虑。
花想容本担心小弦如此劳累会引发伤势,但见小弦着了魔般沉溺于棋道中,纵是把他绑起来不接触棋盘,只怕心里也是在下着盲棋,只好由得他去钻研,暗中嘱咐段成细心照应好小弦。
第三日。小弦正在和段成下棋,水柔清寒着脸走过来,扬手将一物劈头甩向段成:“拿去,以后不许再乱嚼舌头说我耍赖。”
段成眼疾手快一把接住,赔笑道:“四大家族中人人都知道水姑娘是天底下第一重诺守信之人,我怎么敢乱说。”他倒真是再不敢以“清妹”相称了。
水柔清听段成说得如此夸张,面上再也绷不住:“扑哧”一笑,随即又板起脸:“你马屁也别拍得太过分,反正我不像有的人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哼着小调转身姗姗而去。
小弦知她在讽刺自己,心道这“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八个字用在她自己身上才是最适合不过,嘴上当然不敢说出来。却见段成细细观看手中之物,口中啧啧有声:“别看这丫头平日那么厉害,女红针线倒是门中一绝。”
小弦定睛一看,水柔清掷给段成的乃是一方手帕,上面龙飞凤舞地绣着三只鹤。那三只鹤形态各异,或引颈长歌、或展翅拍翼、或汲水而戏,看不出水柔清平日大大咧咧一付骄蛮的样子,原来还有这温婉细致的小巧功夫。
段成笑嘻嘻地道:“清妹的纹绣之功冠绝同门,本来我打定主意赢她一百只鹤,若不是你来搅局,日后我回万县城倒可给二位哥哥好好炫耀一番。”
小弦这才明白“一局一鹤”是什么意思。不由肚内暗笑,试想水柔清若真是和段成下满千局之数,怕不要绣几百只鹤,自己倒是救了她一回。他虽是心底惊奇水柔清尚有这本事,嘴上却犹自强硬:“我见过许多女孩子比她绣得好上百倍。”
“嘘!可别被她听到了,你倒不打紧,我可就惨了。”段成连忙掩住小弦的嘴,摇头晃脑地低声道:“温柔乡中索峰、气墙、剑关、刀垒四营中最厉害的武功便是索峰中的缠思索,清妹的父亲莫敛峰虽是主营剑关,她自己却是喜欢使软索。这缠思索的手法千变万化、繁复轻巧,要想练好便先要学女红针线。清妹的那一双巧手可是门中翘楚,就是普天之下怕也找不出几个比她绣得更好的人,你这话若是被她听到了岂不气歪了鼻子,倒时又会与你好一番争执。”
小弦倒是没想到练武功还要先学女红,听得津津有味:“那万一是你输了怎么办?”
段成嘿嘿一笑:“我当然不会学那些女孩子的玩意,若是我输了便捉只活鹤给她罢了。”
小弦曾听父亲说起过四大家族的一些传闻。那四大家族是武林中最神秘的门派,许漠洋也仅是当年听杜四偶尔说起过,对四大家族门中秘事自然也不太清楚,小弦更是一知半解,此刻见段成年纪大不了自己多少,随口说起抓鹤之事似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对这神秘的四大家族更是好奇,忍不住问他:“我听爹爹说起过四大家族是阁楼乡冢、景花水物四家,你明明姓段,为何也是四大家族的人?”
段成也不知道小弦的来历,见花想容对他如此看重,只道与蹁跹楼大有关联,也不隐瞒:“点睛阁中人丁兴旺是第一大家;温柔乡只许女子掌权,招赘了不少外姓,所以才分了索峰、气墙、剑关、刀垒四营,声势上仅次于点睛阁;蹁跹楼一脉单传,嗅香公子超然物外,素来不理俗事,但说话也算有些分量;而英雄冢武功却必是童子之身方可修习,所以广收弟子,每年只有武功最强的三个人才可以‘物’为姓,方算是英雄冢的真正传人。我们三兄弟的师父便是英雄冢主物天成。”
小弦听得瞠目结舌,倒看不出这个大不了自己多少浑象个大哥哥的段成这么大来头,竟然是英雄冢主的亲传弟子。他虽是嘴上说看不起那些世家子弟,但从父亲与林青虫大师那里耳闻目睹下,心中对四大家族这神秘至极的门派实是大有好感,心里颇羡慕段成,结结巴巴地道:“那你以后也要姓物么?岂不是连祖先都不要了?”
段成一笑:“我兄弟三人本就是孤儿,若不是师父收养,只怕连个名字都没有。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弦一呆,父亲本是姓许,自己莫不是也应该叫许惊弦才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得含混道:“我大名叫做惊弦……”
“这名字不错嘛。”段成倒没有注意到小弦的神情异样:“不过姓名只是一个记号,身外之物罢了。你可知道师父为何给我们兄弟三人起段秦、段渝、段成这三个名字么?”
小弦想了想:“秦、渝、成均是地名,你们定是在川陕一带被师父收养的。”
段成含笑摇摇头。小弦喃喃念着段氏兄弟的姓名,突想起自己上次给费源胡捏什么费心费神的名字之事,脑中灵光一闪:“我知道了!你师父是让你们斩断****尘念……”
“好机灵的小子!”段成大力一拍小弦的肩膀以示夸赞,又凑在他耳边悄声道:“以你的聪明好好学棋,说不定真能击败那小丫头。”
小弦不好意思地笑笑:“赢她也不算什么本事,我看她在你面前还不是输得昏天昏地……”
“你可别小看她。”段成正色道:“我师父可算是宇内第一国手,我学了十年棋算是得了他六七成的真传,赢她却也要大费一番工夫。若是你真在十几天的时间内赢了她,真可谓是百年难遇的天才,以后行走江湖上,在棋界中只怕也少逢敌手了。”言罢连连摇头,显是在这场争棋中根本不看好小弦。
小弦心里一跳,这才知道原来水柔清的棋力绝非想像中的三四流水平,而段成习了十年棋方有如今的棋力,要让自己才学十几天的棋就赢下水柔清何异于痴人说梦。但他心气极高,哪肯轻易服输,看段成摇头叹气的样子更是暗暗下定决心要争一口气,当下摆开棋盘:“来来,我们再下一局。”
段成纵然老成些,毕竟年纪也不大,虽对水柔清不无顾忌,深心内却是巴不得小弦能赢下这一场赌棋之争,好看看平日趾高气扬的水柔清一旦输了要如何收场。但想归想,对小弦实是不报胜望,只是与小弦说得投缘,唯有尽心尽力教他学棋。
几日下来,小弦进境神速。初时两人对弈时段成让小弦车马炮,如今却是让一只马也颇感吃力,不由对小弦的天资大加赞赏。
爱棋之人极重胜负,似苏东坡般“胜亦欣然败亦喜”的怕是几千年来也就那么一个,段成棋力在四大家族中也就仅次于师父英雄冢主物天成,自视极高,纵是让子也不愿轻易输棋,初时与小弦对局尚是权当陪太子攻书般心不在焉,不小心输了几局让子棋后终于拿出看家本领,直杀得小弦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小弦初窥弈道,兴趣大增。起先棋力不济,眼见总是差一、两步便可将死对方,却偏偏被段成抢得先机,心里尚极不服气,死缠烂打坚不认输,段成有意显示棋力,往往杀得小弦就剩孤零零一个老帅。小弦性格顽固,与段成较上了劲,半子也不肯弃,往往子力占着优势却莫名其妙地输了棋。段成又将舍车保帅、弃子抢攻等诸般道理一一教给他,小弦悟力奇高,棋力渐登堂奥,加上他每一局均是全力以赴,苦思冥想,算路越来越深,迫得段成亦得专心应付,一不小心便入了小弦设下的圈套。有些残局本是小弦输定的棋,他却偏偏不信邪,冷着迭出,迫得段成走出各种变化,这种细致的研究更是让小弦棋力飞涨,最后倒是段成主动不予让子,浑然将小弦当作了一个难逢的对手。
自古学棋者均是先看棋书,背下一脑子的开局与残局谱等,似小弦这种直接由实战中入手长棋的几乎绝无仅有,结果练就了一身野战棋风,全然不同一般象棋高手的按部就班稳扎稳打。此种棋风虽是独辟蹊径,但小弦心内没有固定成法,加上他修习《天命宝典》,感觉敏锐而不失冷静,每一种局面都是将各种变化逐一算尽,竟然不存在所谓高手的盲点, 往往从不可能中走出突发的妙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