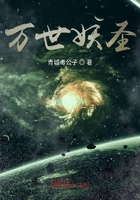果然,他在建国之初到院系调整之前的二三年里,就已在清华讲授过“辩证唯物论”、“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课;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过“辩论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新哲学概论”等课。他“是将辩证唯物论引入清华大学课堂的开拓者”。这些都是解放初期最稀缺的课程。因此,合并后北大新哲学系于1953年就特地聘请了苏联专家萨波什里柯夫来主讲“马列主义基础”一课,而系里则只遴选出他这位教授和助教黄楠森先生(而今早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名教授)两人担任辅导,他并讲授“马、恩、列、斯著作选读”课。系主任郑昕说:“张先生虽然搞中国哲学,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很深的研究和体会,50年代苏联专家在哲学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如张先生讲得好。”可见,张先生也应是新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的先驱之一。
同时,张先生又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授中国哲学史一课的建设中去。1954年成立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并试开“中国哲学史”一课,他主讲其中的宋元明清的哲学。他讲授提纲的主要部分,随后连载在《新建设》上,“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此后,他常常专讲这一部分的课。当然,他也开设过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其他课程。
同年,他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一文,详细分析了王船山的唯物论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船山哲学的专论”,获得好评。贺麟先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客观唯心论,看了这篇文章,我同意船山是唯物论。”系主任金岳霖先生将该文的主要部分以《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为题,发表在他兼做主编的《光明日报·哲学》上。1955年,他撰写并发表于《哲学研究》上的《张横渠的哲学》一文,引起了争论。他又写了两篇答辩文章。1956年,他还撰写了《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小册子出版。1957年,又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出版。同年春,他又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和《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等文章。这些都充分表明他是坚持以实际行动来大力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的一贯的主张。他为了参加北大哲学系于1957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围绕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撰写了论文。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4年成立之初,就明文规定每人每学期须撰写一篇论文。
可见,作为中哲史教研室的骨干教师兼室副主任的张先生,无论是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科研工作中,他都以超额达标和高质量的实际行动,带了个好头。
二
张先生在建国与院系调整的初期,无论在政治和业务上的表现都很突出,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决非是出自于一时,而是和他在这两方面自觉早、成熟早、智慧早密切不可分。历史是割不断的,现在与过去和未来都是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所以,必须追溯到他的早慧。诸如:
他上初二时,通过读《老子》和《新解老》以及《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对于哲学有所领会。于是,他就开始“常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并且,从此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日晚上经常沉思一二小时,养成致思之习”。作为一个小小的初中生,竟然就对高深莫测的形而上学的玄之又玄的问题,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又能培养出“好学深思”的习惯,以至于受用一生,诚然不可不谓之早慧!
念高一的他,在上语文课时,他写了一篇《评韩》的“作文”。大出所料地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赞赏说:“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学三年级的论文也不过如此。”大三比高一要高六个年级,张先生的智力真是大大超前了!
读高二时,他在1928年3月《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有生以来的处女作——《关于列子》,“得稿费银元8元”。这稿费可不低啊!差不多相当于那时北大图书馆馆员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的薪水呢!难怪他“当时甚为欣喜!”
他是1927年春才上高中,1928年暑假就考上了清华哲学系。高中三年,他一年半就念完了,大大提前毕业!
他开始以“张季同”的笔名于1931年6、7月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连载所撰写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个假定》一文。他的这篇论文竟然吸引到了大家冯友兰先生的眼球,而且还给予冯先生一个蛮有趣的假象。冯先生居然“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但是,“后知其为一大学生”。于是,他“则大异之!”此文也获得了另一位大家罗根泽先生的赏识,遂将其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正在开展大辩论,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胡适先生为一方主张老先于孔,以梁启超先生为一方则主张孔先于老。张先生竟然敢于以一名大学生身份参与之,可见其既具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又具有得到大家好评的智慧!
张先生广泛阅读,深入钻研,既有中国哲学,又有西方哲学,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他将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等,认真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了最后的与众不同的极其重要的结论:我“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我完全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于是,他一方面就撰写并发表了《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的一贯》、《关于新唯物论》、《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又一方面就在清华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课时,主动增加了原来教材中所没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并予以高度评价:“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显然,这是张先生的最大的早慧!
张先生早慧的又一大亮点是对中国哲学的前途这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当时,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他“也不甘落后”。于是,他就写出了他的哲学上纲领性的文章,既为他日后创造自己新的哲学体系,又为引导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新的趋势,明确指出了一个新的路向,即《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他在文中“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所谓“唯物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所谓“理想”,就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人生理想,也包括了辩证法和唯物论;所谓“解析”,就是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关于三者的关系,他进一步认为应以“唯物论”为“基础”,以“解析”为“方法”,以“理想”为“内容”。他明确说:我主张“以唯物论为基础”,去“吸收理想与解析”;对中国哲学最注重的生活理想,“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对有大发展的解析派的哲学,“应容纳”他们的“新贡献”。随后,他就用这个理念,沿着这条道路,创建出新的哲学体系。
张先生坚守独自所开辟的新方向,发奋著书立说,予以论证,建构体系。他于1937年,写成正题为《中国哲学大纲》,副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一书。
全书约50多万字,是一部巨著。该书有三大特色:其一,正如副题所明示,是以问题和范畴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以清理并重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这就和当时以对代表人物和学派的分类和分期的叙述性研究为主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大异其趣了;其二,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以逻辑分析法为方法,运用中国哲学所固有的概念和范畴及其源流和发展,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个层面着重揭示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人生论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其三,以上述为基础,进一步对宋元明清理学划分为以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论和以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的两派说,增加了以张载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唯物论新的一派,发展为三派说。这是张先生自创的,我称之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理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次成功的运用,这是他对哲学史方面的新贡献。所以,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代表作,时年仅仅28岁。
张先生为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哲学上关于宇宙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他说:“民国三十一年春,余始撰哲学新论,将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至三十三年夏,关于方法,仅成《哲学思维论》六章;关于宇宙,仅成《事理论》八章,关于认识,仅成《知实论》四章;关于人生,仅成《品德论》四章。所成不及原初设想之半;若干重要问题俱未及论列。”他为什么突然停下笔来不继续写下去呢?先因日寇投降前夕,他滞留于沦陷区北平的生活每况愈下,“厥后生活日益窘迫,运思维艰,竟尔辍笔”。后因抗战胜利,清华迁回北平,他又回到清华重新忙于教学。耽搁到了1948年,“他念‘新论’之作难于续成,因将已成之稿略加修订,各自单独成书,另撰《天人简论》一篇,简叙‘新论’之要指,而随时间之推移,余思想亦复有所进,亦并及之。今夏草草写成,共凡十节,以著历年致思所得之大要云尔。”他又说:“此篇是1948年夏季撰写的,内容略述我对于若干哲学问题的基本观点……篇中肯定物质是心知的本原,提出以‘兼和’代‘中庸’的观点,自审尚非过时。”张先生非常重视“兼和”,强调这是他哲学的核心理念。他在这合称为《天人五论》中,在在自觉运用其自创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理念去研究天和人的问题,以“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要领”,这是他对哲学方面的新贡献。“当时年近四十,可以说‘四十而不惑’。”由上述可见,张先生构建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其名称我们认为应命名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其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其创作时间绝大多数都在“三十而立”之年的前后,诚可谓之早慧呀!那时在北大哲学系的教授群中,尚难以再找出一个像他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新哲学体系的年轻的教授呢!
张先生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正关乎到我们哲学界近年来所讨论的中、西、马哲学三结合的热点问题。所以,“他的新哲学乃是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对当时的北大以及今后中国的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
张先生调到北大哲学系后,决不像有的教授,特别是有的老教授,有历史问题,有政治问题,有观点问题,有信仰问题,等等,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难以适应。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些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前进,甚至他的内心还一定会暗喜,从此以往他就有了占天时(解放了的天),得地利(北大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传统),享人和(全国各哲学系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幸福际遇。他诚心诚意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北大,决心要大展雄图大志,不断做出新贡献。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突然大祸临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罪行”就是他于1957年5月17日在小组整风鸣放会上所说的话:“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召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当时,平安无事。
但是,过了暑假,到了9月初新学年开始后不久,他的这两点意见,突然被上纲上线为“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的三条反动言论。
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张先生并未听进去。因为,他平素待人接物的本性就是“直道而行”,并具有“以德抗位”的德性。他的学生和系党总支负责人孔繁在《忆张师岱年先生》一文中说:“张先生在1957年党的‘整风’会议上,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批评党内不正之风时,曾形容他敢于提批评意见是‘以德抗位’。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其他人说,张先生在说他是‘以德抗位’时情绪有些激动,而激动使他口吃更重,而语气亦显得更重了。这样张先生便因‘鸣放’招来祸端,他的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愿望被曲解,从而蒙受‘向党夺权’之冤。”张先生又满以为自己既“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就决“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响应党的号召,讲事实摆道理。所以,张先生对于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事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事后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俗话说得好哇:“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批判会中,一些人深文周纳(指不根据事实而牵强附会地妄加罪名——引者注),给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张先生“完全陷入迷惘之中!”他痛感“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他痛定思痛,甚至想到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一个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哲学家竟然被迫想起了“宿命论”呢!但同时,他仍很有理性地反思到:“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其实,乃是十七年极左路线使然,加之个别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小人乘机落井下石而成!1983年,我曾当面听汪子嵩先生十分歉意地回忆说:“北大哲学系当年划‘右派’时,本来没有张先生,后来因为已划‘右派’的数字还不够,尚未达标,需要补划一些凑足数,这才把张先生补上了!”我一听说,就想到:“汪先生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的负责人,是知情人,了解内幕真相,其言必可信无疑。听到这里,‘往事不堪回首’的慨叹,则令人油然而生了!”
张先生一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教学和科研的权利,立即被“剥夺”了,被“中断”了,只能做些“资料选注工作”。古人所云“怀才不遇”之落魄感,张先生亦恐难免不油然而生吧!其实,他很可能更加感慨系之于“道虽同而竟不相谋”啊!
他的几百块钱的教授工资,降为几十块钱的生活费。他虽没有说明,但我们可参照冯友兰先生于“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即被“扣发工资,每月只给先生夫妇二人生活费24元。”张先生从1933—1952年的20年中,除去1949—1952年的解放后的三年多,剩下解放前的17年左右,他并非一直工作在清华,其实只工作了短短的四五年而已,另外于1943—1946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三年书,其余的头10年的时间则长期失业;他家历来又只有他一个人工作。所以,他本是个穷教授,没有积蓄,现在只发点生活费,并且他直到1979年1月才得到彻底平反,才完全恢复了名誉和待遇,20多年贫苦的日子,一定有难言之隐,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