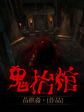当叶子转过身来,发现她要找的男孩在栅栏旁,于是摞着清秀的衣袖,向他走过去。
你怎么在这儿,我找了你好久。叶子依然带着灿烂而无暇的笑,一身CD的香水,让雅奇感觉她像是飘忽的灵魂。
恩!找我有什么事?雅奇看着她,第一次这么看着一个女孩。
我说过要请你客的。她从书包里摸了一块口香糖,洁白的细手指反衬着雅奇粗黑的手指,使雅奇感到不敢去接。
于是说:我不要,谢谢你。
叶子坐在他身边。那股浓浓的香总使他产生联想。
他们成了好朋友,好象世间的特定安置和规律。
雅奇在送叶子的那天,穿着一条牛仔裤和T恤衬衣。蓝色的,雅奇喜欢蓝色。这是大海和天空特有的颜色,是博大和精深的象征。叶子将地址写给了雅奇,人潮一群群涌向了车里,很安静,并不像以前那么吵闹。
在车窗边,叶子说:高考见。
然后车轨开始滑动,感觉车震动着铁轨,很凶猛,很强烈。他和叶子挥挥手,一直等到车消失在模糊的远方,沉没在遥遥无期的山水间。第一次想到了这条地铁通向何方,两条坚实的平行线突然显得那么恍惚地在心里震颤。
他习惯地用手把乌黑的短发向后抹了一把,然后唏嘘地离开,离开这个分离的场所。
离高考一天天逼近,每天十几个小时像晃过的箭,还没会过神来,箭已落地,时间已收场。
雅奇不久后收到了叶子的信封,白色的信封像悬在玻璃瓶里的牛奶。柔软却冰冷,让人觉得这是毒汁的装饰,是在无声地引诱他靠近的物品。
信有两张,都是淡蓝色的海底世界为背景。
我发现你和城里的男孩一样那么喜欢潇洒,但你比城里人心胸更宽富,我喜欢北京上空缠绕荫蔽的云朵。那些急促的阴影,像人性中最软弱的部位,只要用力一捅,就会流泪,就会像撕开的伤口那么疼痛。
我问妈妈可不可以和一个只见过三天面的人做朋友,妈妈说只要我自认为是幸福快乐的事,就可以,于是在背负这个高三的日子里为远方一个一无所知的男孩写信。
雅奇发现自己越来越分心,是不是应该和叶子分手,他一次次地彷徨在校园,操场。曾经在学业面前从不低头的雅奇,此刻似乎变得象易碎的玻璃开始出现裂痕。落拓不羁的心总会引起肉体的疲惫和精神的委靡,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他开始喜欢一个女孩,他总想起叶子那深红而饱满毒液的嘴唇。总是感觉到每封信中都有她特意喷洒的CD香水。总是梦到他们一起在亲吻中时被老师发现……,总是盼望着她快点回来向她说,我爱你,把自己准备的那些语言全部说出来。
信毕竟是死的,它是一个无生命的介质。
在第一次模拟考试中,他的成绩一下到了20名以外。这个一向成绩稳定的学生成为了学校的焦点。老师、校长、家庭不断地为他做思想工作,他都以沉默回避,他第一次看到他在学校的地位的举足轻重。
他的灵魂在被寂寞所吞噬,天空中铅灰色的忧愁的云在变淡、漂流,到一直消失为此。
在星期一到来的时候,雅奇的母亲送来了《红桃K》补品,他知道这是父亲用200ml血换来的,他多次劝父亲不要那样做,可父亲每次都说自己强壮得很,自己平常刻一个雕塑扎手流下的血也会留下100ml血,下次刻雕塑少扎破手,少流点血,这样200ml血也就节省下来了。
他望着母亲微微笑容,感觉好久没有被母亲拥抱的感觉,母亲干苍泛黄的面孔虽枯瘦,布满褶皱,但充满了天下母亲共有的慈爱。他的眼泪不断地在眼眶里荡漾,他知道在没有完成母亲寄托的任务之前,他的眼泪是无力的。
校园里的夜很漆黑,很多的树木常常把天空遮得严实的,夏天常有一群群人在树的旮旯下侈谈,会感觉到风触摸时那种滑滑的感觉。
可现在是冬天。
一切都是萧瑟匿静的,那些有历史记录的树身上残留的铜绿也开始变黑,那意味着死亡。他们是寄生的。今年秋天有棵树将永远枯萎下去。直到化为烟尘。
雅奇曾经在某棵树上用洋刀刻下过一个名字,他把那棵树就叫做雅奇。像父亲刻石头雕塑那样,工工整整的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也刻上了树的名字。在他刻的时候,他看到了树在不断地掉汁液。粘稠的,冰冻的,悲凉的,直到最后一笔,他的手酸酸的,然后悄悄地跑了,不曾记得。
他没有目的地在做一件事,或许就是无聊做作。
当他走进枯树边时,他赫然发现那颗树就是雅奇。雅奇死了,连那些名字也模糊得几乎变了形体。只能从削平的皮块上认出些笔画,那些眼泪凝固而突显的痕迹是苍老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刀,再次将他理得更清楚时,却发现那棵树再不会有汁液了。汁液从这儿都流干了。
就像自己捅家里的那只狗,血流干了,生命也就干涸了。
没有眼泪的东西是脱不起记忆的。
雅奇感觉身体好冷好冷,全身都在抖动。
在某个夜间,突然下起了大雪,无声地飘落。
像花瓣纷飞在四月的季节里,随着风向落定尘埃。
雅奇给叶子写信:总喜欢说南方的雪比北方更温柔体贴。那一层薄薄的积雪给南方人带来喜悦和丰收,就像你的信带给我安慰和关怀。
我经常到送你的那个空旷的地铁边看陌生人从眼前匆匆走过。然后看到在肮脏角落里的青年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扔在墙角,用脚狠狠地磨碎,再欣然地向地铁里走去。
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个女孩,熟悉的面孔全身通体明亮,丝绸的连衣裙上印着大朵大朵的******。还有横跨一个书包。脸上是青春的。
可每次我都很失望,我不知道这条地铁延伸到多远,总之,这里即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只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驿站。有人从这里开始是到起点或是终点。它只能走过一段路程,不会是永远。
雅奇从不谈学习。他知道这已是第五封信了,叶子一直没有回信。
他每次都是自己亲自投进邮箱,寄往的地址一直没变。他开怀疑是不是叶子搬迁而忘记了告诉自己。或者是不是自己的邮票没贴稳投进去时弄丢了邮票。或是叶子生气了,更或许是叶子把这当作一场游戏,她先退出了,而自己却使终坚持。
可他又推掉了猜想,在最后一封信里他根本没有分别的意思。
虽然第五封信又是一个无知的谜,可他依然把它投进了信箱。
当新芽从枝条间透露出来时,燕子还没有来。
新芽才是春的使者,那些融化后的雪水在簇草丛中缓缓浸淌。枯槁的草用坚硬的一叶触动着软弱而富肥的沃土时,那一刻就是死亡气息里的复苏。
死亡和新生是矛盾,就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句话一样,这已经没有太多讨论的意义。
雅奇一直等下去,但不写信。因为叶子要来这里高考的,有很多不眠之夜都在聆听窗外那些不安的声音,像振动的音符。虽杂乱无章得几乎不能分辨吟声的出处,雅奇喜欢听,听得头脑失去知觉迷失方位遗忘思念为止。然后用冷水洗澡,感觉那种从模糊到清晰的瞬间快感,像从水里跳到岸上的鱼明知道死亡就在眼前却还要折疼挣扎。
高考考完了,他还没见着叶子,叶子依然舀无音训。
尽管被感情玩弄得差点遗恨终生,但雅奇在前两年的基础很牢固,最终以全校第一名考取了清华。这不仅是学校的荣誉,还是老师们的全心瞩望。
在毕业晚会上,他似乎已快忘了叶子。对一个人来说事业比女人重要。面对一路走过的三年。雅奇在与叶子会面认识的栅栏旁踟躇了一下。又坐在那块两人一起坐过的椭圆石上,这种感觉又给了他她身上CD的香水味。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掉下了眼泪。晃荡的液体模糊了眼睛,朦胧了心体。原来他才感到他忘记的只是她的面容。而不是思念。
猎人一般是不流眼泪的,流眼泪的人一般不是猎人。因为猎人必须要无情才能捕到动物。
班主任把雅奇叫到办公室里,这是常事。因为雅奇是班主任的助手。办公室里有外面的光透过窗帘映射出淡黄的光芒,显得格外的宽畅空阔。
班主任说:雅奇,这次你能不负众望完成学校的任务。这是我们都很高兴,活着就应让身边的人为此而得到启示和骄傲。
然后从抽屉里抽出一沓泛着CD香水的信纸。然后说,看吧!不管怎样恨我,你应明白。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团团迷离的碎影,好象这些虚幻的烟能增强他自身的承受能力。
雅奇用手指夹起那叠纸就向外跑去,泪水滴在手上,淌在信纸间,浸糊了那些工整而零散的字迹。
那些萦绕在雅奇心头的种种疑问都解开了。老师毁掉了他少年时所注入的纯洁的爱,他的心是空的,很多时候那些空瓶子虽然能装很多东西却没有装东西,这才叫空瓶子。否则这就不叫空瓶子。
他把那些写满快乐时光的信捧在手心,坐在栅栏旁寂静地读,总想寻找某种东西,她每七天就来一封信,而叶子只收到雅奇五封信,不是叶子退出了游戏规则。而是自己在游戏一开始就退出了。昨天是叶子的最后一封信,昨天也是叶子的最后的快乐。
叶子患了白血病,没有参加高考,她一直在为远方的一个男孩做不起作用的鼓励,寂寞的守望。叶子的父母为她写下了最后的遗嘱:如果我死了,你一定在清华了,我一直相信你在倾听我的生活历迹。当我离开时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如果给我一条命,我会为你而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来生缘,但我相信来生缘。
雅奇双手抱着膝盖,只是觉得这个梦太累太累,让他欠了很多债。
狼行成双
她让他先一边歇息着,她来接着干。她在井坎附近,刨开冰雪,把冰雪下面的冻土刨松,再把那些刨松的冻土推下井去。她这么刨上一阵,再换了他来,把那些刨下井去的冻土收集起来垫好,重新踩实。他们这样又干了一阵,他发现她在井台上的速度慢下来。他有点急不可耐了。他不知道她是饿着的,也很累,她还有伤。天亮时分,他们停了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会在下一次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最终逃离那口可恶的枯井,双双朝着森林里奔去。但是村子里的两个少年发现了他们,跑回村子里拿猎枪来,朝井里的他放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后脊梁射进去,从他的左肋穿出。血像一条暗泉似的往外蹿,他一下子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来。开枪的少年在推上第二发子弹的时被他的同伴阻止住了。阻止的少年指给他的伙伴看雪地里的几串脚印,它们像一些灰色的玲珑剔透的梅花,从井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中。她,是在太阳落山之后回到这里的。她带回了一头黄羊,但是她没有走近井台就闻到了人的味道和火药的味道。然后,她就在晴朗的夜空下听见了他的嗥
他的嗥叫是那种报警的,他在警告她别靠近井台。要她返回森林,远远离开他。他的脊梁被打断了,他无法再站起来。但是他却顽强地从血泊中挣起头颅,朝着头顶上斗大的一方天空久久地嗥叫着。她听到了他的嗥叫,她立刻变得不安起来。她昂起头颅,朝着井台这边嗥叫。她的嗥叫是在询问出了什么事。他没有正面回答她,他叫她别管,他叫她赶快离开,离开井台,离开他,到森林深处去。她不,她知道他出了事儿。她从他的声音中嗅出了血腥味儿。她坚持要他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她决不离开。两个少年弄不明白,那两只狼嗥叫着,呼吸毗连,一唱一和,只有声音,怎么就见不到影子?但是他们的疑惑没有延续多久,她就出现了。
两个少年是被她的美丽惊呆的。她体态娇小,身材匀称,仪态万方,她鼻头黑黑的,眼睛始终潮润着,弥漫着小南风一般朦胧的雾气,在一潭秋水之上悬浮着似的。她的皮毛是一种冷凝气质的银灰色,安静的,不动声色的,能与一切融合且使被融合者升华为高贵的。她站在那里,然后慢慢朝他们走来。两个少年,他们先是楞着的,后来其中一个醒悟过来。他把手中猎枪举了起来。枪声很沉闷,子弹钻进了雪地里,溅起一片细碎的雪粉。她像一阵干净的轻风,消失在森林之中。枪响的时候他在枯井里发出长长的一声嗥叫,这是愤怒的嗥叫,撕心裂肺的嗥叫。他的嗥叫差不多把井台都给震垮了。在整个夜晚,她始终待在那片最近的森林里,不断地发出悠长的嗥叫声。他在井底,也在嗥叫。他听见了她的嗥叫,知道她还活着,他的高兴是显而易见的。他一直在警告她,要她回到森林的深处去,永远不要再走出来。她仰天长啸着,她的长啸从那片森林里传出来,一直传出了很远。天亮的时侯,两个少年熬不住,打了一个盹。与此同时,她接近了并台,把那头黄羊用力推下了枯井。他躺在那里不能动弹。那头黄羊就滚落到他的身边。他大声地叫骂她,要她滚开,别再来扰烦他。他头朝一边歪着,看也不看她,好像对她有着多么大的气似的。
她爬在井台上,尖声地呜咽着,眼泪汪汪,哽咽着乞求他,要他坚持住,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她就会把他从枯井里救出去。两个少年后来醒了。在接下去的两天时间里,她一直在与他们周旋着。两个少年一共朝她射击了七次,都没能射中她。在那两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井里嗥叫着。他没有一刻停止过这样的嗥叫。他的嗓子肯定已经撕裂了,以至与他嗥叫断断续续,无法延续成声。但是第三天的早上,他们的嗥叫声突然消失了。
两个少年,探头朝井下看。那头受了伤的公狼已经死在那里了。他是撞死的,头歪在井壁上,头颅粉碎,脑浆四溅。那只冻硬的黄羊,完好无损地躺在他的身边。那两只狼,他们一直试图重返森林,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但他们后来陷进了一场灾难,先是他,然后是她,其实他们一直是共同的。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死去了。他死去了,另一个就不会再出现了。两个少年回村子拿绳子。但是他们没有走出多远就站住了。她站在那里,全身披着银灰色的皮毛,皮毛伤痕累累,满是血痂。她是筋疲力竭的样子,身心俱毁的样予,因为皮毛被风儿吹动了,就给人一种飘动着的感觉,仿佛是森林里最具古典性的幽灵。
她微微地仰着她的下颌,似乎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她朝井台这边轻快地奔来。两个少年几乎看果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中的一个才匆忙地举起了枪。枪响的时候,停歇了两天两夜的雪又开始飘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