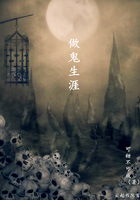《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革命叙事缺陷
高华(1954-2011),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当代中国史研究。著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革命年代》等。
我们很熟悉这种“革命叙事”,其“宏大叙述”影响甚深,就连日常生活语言都烙下痕迹。
高华教授去世后,很多人缅怀他。他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很重要,唯一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文集《革命年代》我先后买了三本,皆不知被谁拿走,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是在香港出版的论文集,部分文章跟《革命年代》重合。其中一篇题为《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很能体现高华教授毕生治学之关怀所在。
高华教授发现,当代中国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主要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现代化叙事”则主要论证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这两种叙事方式均存在缺陷。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因素经常被不经意地忽略了,而“革命叙事”对中国历史学的负面影响更大。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革命叙事”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过分追求“宏大叙述”。基本特点是:第一,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解释,遮蔽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第二,在叙述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第三,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的训导式风格。
我们很熟悉这种“革命叙事”,其“宏大叙述”影响甚深,就连日常生活语言都烙下痕迹。高华教授认为这相当不妙,我们应持一种客观中性的“灰色历史观”,不要故意忽略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对重大现象的研究不要故意回避事实,不要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
假如摆脱革命史观来看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有点敏感。过去常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甚至连“当代史”的说法都未必成立。高华教授认为,1840年以后该传统已被打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当代史。
1949年后,修当代史长期提不上议事日程,主要是因为社会已有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提供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所谓历史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
“革命叙事”强调1949年就是一个分水岭,过去是个晦暗无光的世界,现在迎来无限光明。这个间隔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高华教授认为,应跨越这种人为的间隔。他特别注重1949年前后的延续性,认为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未因1949年新政权的统治而中断。很多原以为建国后诞生的现象,其实根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埋下。
这本书收录了另一篇重要文章,题为《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主要谈“阶级出身论”。这套理论在1949年后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它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对“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未多论及,长期以来,它只是依存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之下。在争取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旨在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它被用来清算敌对阶级,改造和重建社会。
“阶级出身论”不是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却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尽管它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使得党内和民间社会曾经一度保持长期的紧张情绪,却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
身为优秀的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敏感地注意到一些易被忽略的史料,然后发挥小说家般的想象力进行解读。他在《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一文中引述的资料就非常有意思。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1]在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到南京,为抓“右派”找部分高干谈话。毛泽东质问道:“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回答:“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泽东大发雷霆,拍着沙发旁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毛泽东乃“一国之尊”,为何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高华教授分析道: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尚未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实职高干中展开。毛泽东可能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
江渭清圆熟地避开毛泽东的攻势,表态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毛泽东挺信任江渭清,这时怒气消了,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然后,毛泽东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
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渭清回答:“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高华教授分析道:上述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毛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但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泽东对他一向有好感,知道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
(主讲梁文道)
《士人风骨》
“颂圣”折弯士人道统
资中筠(1930-),祖籍湖南耒阳,生于上海。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著有《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
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资中筠先生风度翩翩,见者无不倾倒。很多女性说,但愿自己红颜老去时,也能这么好看。资先生是当今学术界最受尊敬的老前辈之一,晚年推出五册《资中筠自选集》[2],广受赞誉。
资先生有一篇文章很有趣,题为《关于我的履历》。公共场合常有人提及她“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她不以为意,后来愈感不是滋味。为澄清自己并非此类靠曾担任高层翻译而“吸引眼球”之人,她说自己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
资先生有点不解:工作半个多世纪,仅短短五六年有过帮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她自谦后半生虽碌碌无大成就,但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为坚守独立人格,资先生不厌其烦以正视听,风骨卓然。然而像她这样坚守知识分子道统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分析透彻,令人震撼。
资先生追溯先秦诸子百家,看看当时的大思想家是如何与政治人物打交道的。她发现孟子“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
战国后期,知识分子的气度已变。《战国策》里那帮人不再是“帝王师”,只是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是“谋士”,总是准备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他们的目标是助王称霸,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他们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此后,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在尊崇孔孟之道的时代,“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特点:第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家国情怀。第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三,“颂圣文化”,将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见用则“皇恩浩荡”,获罪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士人这三大精神特质,在五四时期有了一个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告别“颂圣文化”,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当时虽是专制政府,高压统治,甚至搞暗杀,但知识分子总体上保持着气节和价值共识。比如张奚若[3]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后拂袖而去,从此拒绝参加。知识分子敢跟政权作对,不怕官员的脸色。
1949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结果被上级严厉批评,学校党支部深刻检讨。借此事件,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开展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
过去经常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几乎都写过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资先生说“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你“清高”就要挨骂,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问你。你有骨气也要挨批,对人民必须折腰。“旧道德”也要反对,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当时甚至鼓励投机,过去士大夫视之为丑恶,如今“投革命之机”越快越好。
资先生认为,士人道统的衰落与知识分子自身也有关系。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日留学生则主要为自己谋前程,即使选择回国发展,大多也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社会改造。她慨叹:“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资先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是得利者,便以各种“理论”
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辩护。还有一部分所谓的“文人”因夸张地、超越起码人道底线地“颂圣”而名利双收。
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如今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排外、仇外,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这些论调大多殊途同归。资先生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这种言论具有一定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将一切不满转向洋人。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
中国知识分子难道要继续这样丢人现眼吗?或许是时候重拾失落已久的士人道统了。
(主讲梁文道)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盛世言论最不自由
王汎森(1958-),台湾云林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著有《章太炎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
这些禁忌在大清律例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裹挟着一切,连皇子都要自我压抑。
今天常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却忘记了这一时期也是文字狱最盛之时。文字狱历朝皆有,尤以清代最多。现在很多人把《四库全书》当宝,殊不知这套书恰恰是禁书运动的成果,里面收录的都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书,那些不正确、不健康、不道德的内容早被剔除得干干净净。
清代的文字狱是如何开展的?文字狱如何影响了社会风气?论文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里最有趣的一篇文章就谈了这个问题。作者王汎森是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台湾史学界数一数二的重量级人物。我曾有幸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他,他的朋友张大春[4]告诉我,王汎森这辈子没用过圆珠笔。这怎么可能?
怎么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人?后来我发现王汎森果然随身携带毛笔,连写个联系方式也用毛笔!论及文字狱的文章题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看到这个题目,对理论敏感的人会联想到福柯[5],因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来自他。在清朝皇权专制下,政治、道德、权力等各种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样,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在老百姓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里发挥着作用。在那个文字狱盛行的年代,议论时政是很容易玩火自焚的,题献颂诗也可能马失前蹄。换句话说,你骂政府会死,拍错马屁也会死,最后只好缄默——这就是权力追求的压制效果。
乾隆皇帝对皇权的自我想象是非常有趣的。他想做一位千古帝王,自以为文化水准高人一等,喜欢为文化定标准,很多前朝流传下来的书画珍品上都留有他的题字,斗大一个印盖下去,特别破坏品位。他还有一种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本朝人应忠于本朝——你活在什么政权底下,就该好好听它的话,跟你是什么种族无关。
乾隆当年搞《四库全书》,最初想搞成类似《大藏经》那样的全书,后来决定趁此机会广泛搜罗民间的禁书。什么是禁书?那年头有很多敏感词,比如皇帝御用的“赦”字,老百姓不能用;“汉”“明”“清”“夷”等字也不能随便用;称呼清军不能叫“清师”,而应叫“大兵”“王师”。我们翻遍《明史》找不到“千钧一发”这个词,因为清朝施行“剃发令”,你说一根头发可以系千钧重量,是不是你对剃发很不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