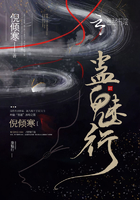顺江南下有一座野庙,天色渐暗,又似有大雨将至,几人行至庙前。
洛韶麟道:“公子,你们先进去吧,我去四周探查下,看有没有被人跟踪。”
高衡,道:“快去,快回。”
“喂,到了,下来吧!”洛韶麒用力地拍着林月城的后背如是叫道,但只见林月城直挺挺的一动不如,于是乎大声骂道,“喂,你装死呢?!”
低下头一看的时候,林月城口吐白沫着,脸色发青,果真个半死不活的模样。
“笨蛋,你没事吧!?”蒹葭心一慌从高衡的骏马上一跃而下,小跑着来到了林月城的身下,掐了掐林月城的人中,却毫不见成效,不禁怒有心起地道,“你这混蛋家伙,对我的笨蛋林月城做了什么?!”
一时间数道目光都集中在了洛韶麒的身上,就连公子高衡也投来了训诫的眼神,洛韶麒慌乱的摆手,结巴道:“你们,干嘛都这样看着我?我,我,可什么都没做,是,是,这小子自己晕过去的!”
一开始的时候,林月城还在洛韶麒的马背上大喊大叫着,但等再跑出去一段路程的时候,就已经听不到林月城发出的任何声音了,洛韶麒还想着这小子是不是又在琢磨着什么鬼伎俩想要算计自己也就没去搭理他。
“狡辩,除了你还有谁!?”
“我——”洛韶麒无端的竟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错觉。
白露也下了马,看了看林月城的脸色又给林月城把了把脉后,轻声地道:“好了,蒹葭,月城不过是舟马劳顿暂时晕厥过去罢了,并不关这位洛公子的事情,我们还是先将月城抬进庙里再说吧。”
“嗯嗯,对对,还是这位白露姑娘说的有理!”洛韶麒擦了擦额头的虚汗,连连点头,还主动的上前打起了下手。
这一举动,竟连高衡都颇有几分意外,但高衡却并没有随同他们一起走进破庙,而是沿着泥泞的小道往河岸的方向走去,其他几人的心思此刻都在林月城的身上也就没有人注意到高衡脸上的异样。
“哼!我警告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我就会原谅你了!”蒹葭还是不依不饶地道,“你不过是在将功折罪罢了,要是林月城那笨蛋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蒹葭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呃,是是。”洛韶麒说着,似乎想到了其他的什么事情,转身跑出了庙外。
白露从随身的药囊中取出一些晒干了的药草,如是吩咐蒹葭,道:“蒹葭,你先将这些草药熬成汤喂给月城,记得多熬一会。”
“嗯。”蒹葭应了声,便忙活开了,见白露起身,随口问了句,“姐姐,你也要出去?”
“带来的药草都落在了那辆马车上了,我想去外面走走看能不能采些替补的草药回来。”
“好的,放心去吧,我会照看好这笨蛋的。”
破庙之外,高衡独自瞭望着江面若有所思,肃寒的远山周国传来了阵阵清笃的暮鼓之声,日落之后的岚烟江上,弥漫着的雾气更加的凝重了,层层又叠叠的迷雾,望之不尽。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高衡一时心有所感,轻颂着《诗经》中的名篇《国风·邶风·击鼓》,吟罢,高衡垂下了眼眸,沉沦于脑海中的记忆。
月落乌啼霜满天,风平浪静的江面上骤起狂风,颠簸着一艘孤影的帆船在风浪中肆意摇摆,一如高衡此刻的心境。
某刻,洛韶麟走了过去,解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高衡的身上,柔声道:“殿下,江边风大,小心着凉了。”
“这岚烟江的风浪再大,又岂有晋国的人心险恶?威王高瞻就是那一江汹涌的波涛,本宫就如同那江中的帆船,摇摇摆摆,稍不留神就有倾覆之危。”
“殿下!!——”
高衡苦笑一声,道:“抱歉,本宫实在不应该说这些丧气的话,只是我等离开晋国也算有些时日了,事情却一筹莫展。而我,却只能望江兴叹——”
“但,您现在不也平安无事的站在这里吗?事情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我——”洛韶麟吞吐了片刻后,似下了什么决心,咬了咬殷红的嘴唇,敛容道,“殿下,韶麟倒有一计,望殿下斟酌。”
“什么计策?!——”
“——之前,在树林中追着林月城的那伙人,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周国国府北宸府,钦天监统御下的二十八舍琅琊霄羽卫,虽然我不知道林月城他们是怎么惹上那么厉害的人物的,但若是我们将林月城等人交给周国国主的话,说不定殿下您就能够得到周国国主的襄助,再与他们借兵——”洛韶麟的话戛然而止,接下来的是谜一般的寂静,就好像是两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相同的沉默。
许久,高衡闭眼道:“韶麟,你先回去吧,容本宫再考虑考虑。”
“诺。”洛韶麒完全的以一位下属的身份回应道,“韶麟,告退。”
江畔边上的温度一时下降了好几分,卷起的巨浪拍打着岸边,飞溅而起的浪花夹杂着一股刺骨的寒意,打湿了他的脸庞,温润如玉的外表下不断得痛苦着,挣扎着,再度睁开的时候,他眉宇间的神采与之前已是判如两人,澄明的双目中,胧上了一层杀意。
蓦地,高衡似察觉了什么,大喊了一声:“什么人!?”
“嗄?!——”那人一慌,沿着江岸跑去,很快的就消失在了重重迷雾之中。
高衡一怔,没有再追上去,而他也大致能猜到刚才站在那里的是谁,转身往破庙的方向而去。
*************
鄢陵城,镇北大将军府邸。
昏暗的厢房内,沈策负手而立,静静的注视着这空无一物的墙壁。
墙壁上有面青铜镜,铜镜上的花纹古朴怪异看似有些年头了,沈策长袖一甩,手掌缓缓略过镜面,一阵蓝色光芒之下,光滑的镜面犹如湖水般荡漾着涟漪,数人模糊的身影出现于镜像之内。
沈策开口道:“老夫嘱咐你们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属下无能,暂时还没有擒住林月城几人。”回话的是景霂,恭敬的语气,丝毫没有了白日里追逐林月城丝毫的气焰。
“林月城几人不过只是一群凡人,以你们的实力还擒获不住?!”沈策脸上的表情一变,紫色的瞳孔内更是闪过一丝厉芒,显然是动了真怒。
景霂见势,连忙躬身跪倒在地,请罪道:“太仆大人息怒,实则是因为——”
从自己居住的南苑厢房处走了出来,沈策一脸凝重的往东苑的方向而去,途径下马亭的时候,一名身着甲胄的军官拦在了沈策的面前,恭声道:“相爷与将军大人正在书房会客,还望神策子先生稍后片刻,容小的前去通秉一声。”
原本以沈策周国六卿太仆的身份纵使在郑国京畿的皇宫首府之内亦来去自如,更不用说他还与郑国丞相宁致远这一分亦师亦友的匪浅情谊,但,此刻居然有这么一个不知死活的小人物胆敢拦在他的面前,沈策的口中不说,脸上已是有了不分不悦。
“失敬了,小人也是奉命行事,还望大人海涵。”那军官也知沈策不好惹,始终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
“奉命,吗?——”沈策的嘴角竟是莫名的流露着一丝微笑,意义不明地道,“那老夫就在此稍后片刻,你进去通报吧。”
“小,小人告退。”那军官长嘘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虚汗,转身快步的向偏厅的方向而去。
没过多久,就有两人从偏厅的书房内走了出来,一人是之前的那名军官,另一人沈策也认得乃是郑国太医院的首席,梁承嗣,但,现在的他却是将军府的御用大夫。
那名军官,道:“神策子大人,丞相大人请您进去。”
沈策应了一声,却并没有马上地往书房的方向走去,而是向前一步拦在梁承嗣的身前,拱手道:“梁太医,别来无恙。”
“噢,沈太仆有礼。”梁承嗣行了一礼后,疑惑道,“沈太仆,不是有事求见丞相大人的吗?怎又为何不进去了?”
“实不相瞒,老夫是有一事,想要叨扰下梁太医。”
“何事?如是老朽知晓的定,言无不尽。”
“倒也并非什么要紧的大事,只是关于瑟儿的病情,老夫想要询问下太医罢了。”
“二公子,外热内冷,盗梦虚汗乃是风邪入体所生的症状。但他却又一直昏迷未醒又药石无灵,可见二公子的病因该是心魔所至——”
沈策一怔,凝声道:“连,梁太医,您也毫无办法?——”
梁承嗣摇着头,无奈地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老朽也只能尽力而为。”
将军府书房,沈策推门而入,室内只有两人,似在商议着什么,一见沈策走了进来,那名年纪稍大的长者从座位上起身走了过来,反观那名精壮的男子一动不动的呆在远处,眼神中似乎还透着敌意。
“宁相,瑟儿的病情,沈某适才已从梁太医处知晓了一二。”沈策沉吟了一声,接着说道,“瑟儿的病只因一人而起,若是能寻得那人瑟儿自担药到病除。”
一直以沉稳示人的宁致远脸上也显出了焦急的神色,道:“即使如此,还不快将那人请回府中?!”
“不急,除了此事,沈某另有一要事与相爷您商议。”沈策顿了顿,目光随意的上下扫视着这间不大的书房,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宁致远会意,头也不回地昊声道:“荣儿,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父,——”
“下去。”宁致远脸上的表情不怒自威,语气中更是没有丝毫转寰的余地,即使贵为镇北大将军的宁荣在父亲的威压下也只能悻然而去。
“现在这书房中就只剩下了我和先生两个人,先生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沈策将自己派人追踪林月城等人的事情简单的复述了一遍。
宁致远摸了摸脸上的胡子,忖思道:“本相先前就曾听闻晋国皇室不和,藩王高瞻欲弑兄夺位,晋国太子下落不明,想不到这一切居然都是真的。”
沈策,接着说道,“现如今林月城等人在栖息于我周国境内的临江府的一座破庙之中,而那名疑似晋国太子高衡的人物也一并和他们呆在一起,相爷若是有心,倒不如今晚就去与他们见上一面,再伺机找个借口将高衡几人安置于府中。”
“安置府中?先生的意思,本相有些糊涂啊。”
“高衡流落至此,一定昼思夜想妄图复辟,相爷又有何不明的?——”
闻言,宁致远的脸色陡然大变,面有薄怒地道:“先生,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吗?!私自会见他国要人本已是禁忌,你竟还要我助高衡复国,岂不与通敌叛国无异,这叫本相如何回朝面君,先生难不成是想陷本相与不忠不义之境地吗?!”
沈策,神色自若地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更何况相爷您还是两朝元老,位极人臣,功高震主。荣公子又是恩威显赫的镇北大将军,右丞杨肇更是行思坐想要除掉您,而您此番没有禀明陛下就私自前来边陲重镇鄢陵,本就已落人口实,您这一回去必是凶多吉少,还不如早作打算!”
沈策说的这一切,宁致远又怎会不知,但当今国主的父亲毕竟与自己曾有过同胞之谊,自己也曾发誓永远效忠于郑国,自己这一步如果真的踏出的话,就将是再也回不了头了。
宁致远沉默了许久,正色道,“先生,此事事关重大,若是不甚泄露出去被杨肇等人知晓不但你我二人人头难保,我宁氏一族更会因此满门抄斩,还请先生容本相三思。”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沈策冷笑一声,又再说道,“相爷不会连兔死狗烹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知道吧。”
宁致远脸上的表情更是阴晴不定,终于还是无奈的喟叹了一声:“一切,就照先生的意思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