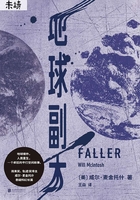柯凡踌躇一下,开始拨打莞尔的手机,他突然发现自己已有一段时日没有和她联系了。母亲走了,犹如一阵风,轻轻关上了他的一道心门,这道心门将他和莞尔隔离开来。这些天,他终于想明白了,他并不怨怪莞尔,他是在惩罚自己,以一种决裂的方式去抵御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修复的缺憾就像胸腹上的那道疤痕,已经植入他的记忆深处,他并不愿意被提醒,尤其被另一位“肇事者”提醒。莞尔关机了。柯凡再打给苏雯,后者没有接听,放下电话,他突然有些恍惚。刚才的电话是不是梦中的某个情节。现实是不是梦的延续呢?如果是,他希望自己出入自如,不沾染任何悲喜的尘埃。他终于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需要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中,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除了工作,他的时间都留给了父亲。这天上午,萧云又打来电话,约他见面,到时她会带上自己的儿子,他突然觉得荒唐。如果这个孩子真是他的骨肉,他将如何面对父亲?该不该拉着孩子的手去祭拜自己的母亲,以告慰她老在天之灵。
莞尔知道又会有什么反应,是声嘶力竭指责他还是冷嘲热讽奚落她,彼时,他们终于可以一拍两散了。走到半路上,手机铃声响了:手里握着格桑花呀,美得让我忘了摘下。这个音乐铃声已经有一阵时日没有响起,以至于柯凡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刚分居时,莞尔曾经买了一大推水果和营养品放到家门口,按了门铃就迅速离开。也曾在他上班时间打电话到他家,问候柯父。近段时间,她却在他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他没想到她会在冷秋季节和苏雯去了五台山。“你好吗?”莞尔在电话里问道,她的口吻带着浓重的鼻音,好像感冒了。“还好吧,今天早上你到哪里去了?没事吧?”柯凡问道,一听到她的声音,他的心顿然安稳了许多。原来自己的内心还牵挂着这个和自己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苏雯大惊小怪啊,我只是昏倒在公共厕所里了。”莞尔带着轻描淡写的口吻。“你小心点。”柯凡一边开车一边说道,车子快到十字路口,一交警正在指挥交通。“在开车吗?要去哪里?”莞尔在电话那头问道。
那时,柯凡已将手机远离耳朵,握在手里,过了红绿灯随即又放到耳边。“你刚说什么吗?五台山之行还愉快吧?”柯凡赶紧问道,电话那头却没有声音,柯凡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电话并没有挂断。“没什么,这里虽然没有蓝天,我的心却很清澄,我已经能放下一些事了,但是还放得不够彻底,要不也不会这个时候打电话。”莞尔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好像要蓄积某种力量,随即又道:“你多保重吧,早点回家,多陪陪爸爸。”莞尔的电话总共只说了五句话,却在柯凡心底起了波澜。她说她已经能放下了,什么意思?她是在牵挂他,还是只想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来向他告别。烟雨朦胧的中午,莞尔三人去了一个离五台镇有十来公里路程的一个偏僻寺庙,寺庙不大,前来上香的游人不多。三人在一个小师父的引领下,去了旁侧的一间略显破旧的僧堂,拜见法名为信慧的住持。在中国佛教寺庙的建筑中,殿堂是寺院建筑的主体。殿是供奉安置佛像以供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供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起居的地方。
信慧师父约莫四十多岁,已经瘦到不能再瘦,为人平和朴实,目光流露几分淡定温和。据苏雯说他年轻时曾是一名教中文的中学老师,学识见解非同一般。信慧师父面对三位年轻的女施主,话并不多,总是简单一句,却形象深刻,予人回味。临告别时,莞尔问了信慧师父两个问题。大抵是看出莞尔的神色有别于其他两位施主,信慧师父不再惜字如金:“师父,您没有经历爱情,如何告解我们情感上的困惑?如何让我们放下呢?”“你看,外面的落叶,它的存在,是不是已经在告解你:喧哗的尽头是萧索。而我,不过是在提醒施主,当生老病死迫近时,父母、子女、爱人都无法代替你,在烦恼和生死面前,我们只有独自面对,独自承担。”“这些道理我都懂,您能给我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吗,针对我目前的烦恼?”“施主,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尝试在宽恕自己中宽恕他人吧。洒在地上的牛奶不能收回,我们不妨先接受这个事实,再来清理,然后慢慢放下。阿弥陀佛。”说着,信慧起身,双手合十,莞尔的心有些触动,连忙双手合十,态度恭敬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