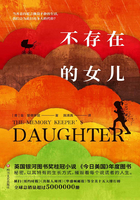“都不敢玩大的啊?那我们先来点容易的。水果市场一直有一群小贼在那里发财,天天都能够搞几百上千,咱们去敲他们一笔如何?”唐松促狭地故作苦笑。他吃人嘴短,所以不得不陪着阴四爷玩。这些事他张口就来,证明了他就算不是一个江城黑道百事通,至少也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算了,扒手不沾。好像他们是跟何庆丰的吧?再说,那是段炼的地盘,何庆丰跟段炼一直有仇,段炼都没有动,我们不要去捅这种马蜂窝。”阴四爷故作老练地分析。
接下来,他们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主要是由唐松提议,阴四爷否决,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件适合他们做的事,不是太困难,就是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办到,或者是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一鸣惊人,在黑道扬名立万。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什么地方进行突破,把这群黑道新秀们难住了。
最后顾军的传呼结束了他们这种可能永远没有结果的讨论。
顾军在一个朋友开的酒吧捧场,他请苏树东过去,“有朋友也一起叫上吧。”
四个人打了一个车过去,顾军在门口等他们。如果是苏树东一个人,他不用这么麻烦,但是苏树东预先告知是四个人,这个新警察有非同寻常的干练和严密,苏树东的朋友很可能是他们打击的对象,贸然坐到一张桌子上,就算不发生什么,影响也不好。“我那桌朋友都喝多了。”他解释,“我们另外开张台。”他亲自把他们引进去安顿好,然后客气地跟四人一一碰杯。介绍到唐松时,顾军特别留意了一下,表情古怪。而当苏树东要介绍他时,他悄悄地碰了苏树东一下,苏树东默契地把顾军简介为“我的朋友”。
场面酒喝完,顾军说:“我先过去,等会儿再过来。”
“条子?”等顾军离开,唐松首先问。他没有辜负这十多年的混混经历。
苏树东没有回答,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他似乎没有听见唐松的问话,在认真观察酒吧中的另外几桌客人。这些人一律喝酒豪放,说话声大,不仅有普通人喝酒后的张扬,还有另外一种满不在乎的跋扈,看起来,很有可能都是顾军的同事,这个酒吧,也可能是某个警察的产业。他感觉怪异起来。但是他的伙伴明显与他不同。
阴四爷显示了他强大的适应能力,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他都能够寻找到别致独到的乐趣,他叮嘱一个眼睛大大的服务生,只要他的酒杯没有满,就一定要给他添酒。结果,他每次都喝一小杯,那个服务生只好一趟一趟地走过来为他服务,这个时候,他不是盯着她的一双手死看,就是对着她的大眼睛放电,自得其乐。坦克表情木然,不知道他脑中在想什么,阴四爷举杯的时候,他就举杯,大家不理他的时候,他就发呆。唐松还没有坐下,就在四处搜寻,结果他如愿以偿,有两桌酒客中有他的熟人,顾军离去,他立刻自由活动,一手端酒杯,一手提酒瓶开始了他的巡回演出。这种场合,哪怕仅仅是彼此脸熟,也会上升为兄弟友情,再加上大家都喝得差不多,倍感亲热,拉手扶肩。唐松回来时,已经耗费了整整一刻钟加六支小瓶的啤酒。
顾军带了一个中年人过来介绍,“顾老板。这是我的几位朋友。”
这个人身上烙着比顾军还要深刻的标志,连坦克都看得出他是一位警察。老警察虽然喝了很多酒,但是依然很清醒,鹰一样的眼一下子就看清他们所有人的底细,除了苏树东。他的客套也掩饰不了那种强烈的傲慢和敌意,仅仅因为他们是客人而稍稍收敛,他跟他们一起喝了一杯就离开了。
又过了十分钟,顾军那一桌人走了。这个时候,已经十一点多,苏树东小声问顾军:“现在做哪?”
“城北。”顾军伸手去拿酒瓶倒酒,身子不引人注意地挨近苏树东,小声回答。苏树东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分在城北派出所,也懂了顾军的暗示:他现在不希望谈他的工作。
这让苏树东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决定了接下来他们整个气氛的尴尬。顾军跟他们分别再碰了几杯,显示了他的超级海量,然后,苏树东决定结束。
他示意阴四爷结账,同时,坚决拦住了想起身的顾军。他认为酒钱应该由阴四爷结。他不能让顾军结,不想在顾军面前失了气势,这是他的奇怪想法。但他也不愿意自己来结。他身上有钱,白云湖几个月的工资再加上聂山鹰补给他在上海的薪水,所有的家当他全带在身上,这是一个穷人通常的做法。对于金钱,他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这点钱能够不用的时候一定不用,他绝不会冒充豪爽。现在阴四爷有这个能力,何况,阴三爷特意拿了一千元,这一千元,他也有份,就是用来招待他的。甚至,他可以追究阴四爷私自赌博输掉那两百元的责任。
酒钱二百一十二。这个数字让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既然朋友捧场,没有连零头也要收的道理。阴四爷掏出一大把钱,有整有零,数了两张一百和一张十元一张一元,“妹子,能不能优惠一下?只有这么多了。”善于在细节上发挥的阴四爷再次显示了他的独特,明明手中还有一大把零钞,但故意要在一元钱上计较,一部分是对这个数字不满,也有一部分是想跟这个大眼睛的服务生磨叽。
“蟑螂,在顾哥的堂子扫皮?越混越转回去啊!”旁边一桌一人嚷道。之前他背对着他们一桌,这时侧着身,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满嘴酒气。他刚刚进来坐下不久,也是刚刚结束酒局,觉得还有战斗力,乘兴来酒吧发挥余勇。他们是两个人,说话的是一个胖子,他也跟蟑螂一样,进来就在寻找熟人,但是这时候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苏树东他们这一桌,他发现了蟑螂,其他人都是生面孔,一看就是刚出来混的样子,他认为蟑螂是他们的头,同时认为他镇得住蟑螂,为了显示自己,出言讥笑,但这一句戏谑的话有些伤人,变成挑衅。阴四爷把钱放在桌上,转头狠狠地瞪着他。
“小子,不高兴啊?刚才看人家的手还没有看够吗?”胖子不怀好意地笑起来,他注意到了阴四爷的过分,心生不满。这也是他出言讥笑的原因之一。
阴四爷没有说话,他在做着判断。他看起来大而化之,玩世不恭,真正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不是莽撞的人。同时,他也在偷看苏树东,似乎在等着看他的表现。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看着一桌沉默的人,胖子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愉快地继续调侃:“蟑螂,你不是局二的兄弟吗?是不是以为你的局二哥要出来了,就可以在江城横着走了?喝酒也可以不给钱啊!”
这是一个典故。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蟑螂有幸与江城黑道大佬局二在一个堂子吃饭,虽然不是一张桌子。蟑螂这桌的人过去敬酒,不愿失了礼数的局二过来回敬,并且客气地称呼他们所有的人为“兄弟”,这不过是酒场的客套,但是后面发生的故事,成为一个所有江城道上兄弟都知道的笑话。
这天蟑螂喝多了,散场后一个人去恩恩的翻牌机赌场向幸运挑战,但是上帝抛弃了他,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输得精光。因为喝得特别多,或者是因为局二那一杯酒,他要求赌场免费给他上一千分。赌场经常会这样做,是一种笼络安抚客人的手段,但对象基本上是那些输得很多的豪客,唐松不在其列。他打的是两角机,每次押分一般不会超过十分,除了特殊的情况。赌场的工作人员对这位装模作样的穷鬼早就心怀不满,他们私下里认为他是来混免费盒饭吃的,于是发生争执,并且逐渐升级,最后被赌场工作人员挟到小屋里,准备给他醒醒酒。但是用不着,这个时候他自己被吓醒了,情急之下,他宣称自己是局二的兄弟,而且赌咒发誓刚刚他们才在一起喝酒。
这个时候威胜公司一统江城黑道,如日中天,苏雪峰锋芒峥嵘,威势凌人,如果这个穷鬼真是局二的兄弟,那是万万动不得的。赌场的工作人员立刻给他的大哥打电话,然后他的大哥又给谢淳恩打电话,最后谢淳恩把电话打到局二那里求证。局二愕然。他只有一位姐姐,已经过世多年,从来没有一位兄弟,同时这个人也不是威胜公司的兄弟。经过一些曲折的解释和求证,最后局二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他叹了口气,算了吧,这个人毕竟还真是跟他喝了一杯酒,也算个缘分,他让谢淳恩包涵这一次。谢淳恩答应,这是一个顺水人情,只是几句口角之争,这个人并没有给他们赌场造成什么损失。
但是全身而退的唐松觉得很有面子,毕竟局二亲自打过电话过问了他,而且也真的替他求了情,志得意满。他认为应该再奖励自己一些酒,于是他很容易在热闹的大排档上找到了几个熟识的混混做了不速之客,又是几瓶下肚,他再次开始膨胀。最后,因为夜深公用电话收摊,一个混混去旁边的宾馆回传呼,认为一元钱的话费收得太贵,跟保安口角了几句,唐松奋然起身,要替这个混混出头,于是一群醉鬼涌进宾馆的大厅。两个值夜班的保安见势不妙,立刻拨打110,其他酒鬼作鸟兽散,只有唐松坦然躺在沙发上等待着警察到来。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或者,这个时候他的大脑已经不受自己控制,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他被带到警局,再次条件反射地祭出老法宝:宣称自己是局二的兄弟。
警察立刻给局二打电话,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局二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隐隐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不是叫唐松?”局二问。
打电话的警察大喜过望:“对。看来真是二哥的兄弟了。幸好我们还没有怎么样。”谁都知道苏雪峰不好打交道,但局二向来出手大方,有情必还。
局二哭笑不得,怔了一会儿,才说:“先把他泼醒,用尿最好。醒了也不要放他,吊他一晚松松他的骨头。”
他不想跟这种无赖纠缠,必须惩罚这种行为。但是因为这天晚上的电话通过了很多人,所以第二天无论是混混还是大哥,都把这件事当成一件笑谈广为传播,唐松一夜之间名声臭遍江城。他混了这么久,总算混出名了。
胖子的话击中了唐松的软肋,他尴尬地笑笑,苏树东转头去看顾军,顾军沉稳地坐着,脸带微笑,但有些不满和轻蔑,这让他心里有了底,然后,他做了决定。
一桌人中,他距胖子最近,他伸手抓起一支没有开过的啤酒,直接就砸在胖子的头上。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才站起来,冷冷地看着胖子。虽然胖子头上的肉很多,但苏树东用力实在太猛,啤酒瓶完全破碎,只剩下几厘米长的一截留在他手上,酒和碎玻璃洒了胖子一身,暗红的液体迅速冒出,那是鲜血。
胖子的同伴站起来,坦克一个飞腿踢了过去。或者是因为学武之人特别的反应,苏树东啤酒瓶砸在胖子头上的时候,坦克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显示了与他平时完全迥异的敏捷。他起腿快,动作突然,力量大,胖子的同伴甚至连闪挡的意识都没有,直接连人带椅被打倒在地。然后有两三秒的停顿,阴四爷也扑了过去,他拿的是烟缸,砸在胖子头上,这是打落水狗,但是他如此用力,烟缸砸到头上的声音如此大,以至于大家都以为胖子的头可能碎了。唐松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不仅是苏树东,坦克和阴四爷的表现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本来从心里看不起这三个人,但是这一瞬间,他们表现出来的气势和残忍,完全像那些真正的黑道凶徒。他想劝阻一下,但被吓住了,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很可能激怒这三个煞神,甚至自己也可能被放倒在这里。他见过太多的斗殴场面,这种时候很多混混都处于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癫狂状态,任何拂了他们意的人,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个细节,都可能立刻被视为敌人,予以打击,哪怕一分钟前彼此还在称兄道弟。
苏树东握着半截啤酒瓶严阵以待,等阴四爷加上烟缸,胖子溜到了地上,他确信胖子和他的同伴都已失去了还击能力,把手中的半截啤酒瓶丢开,一片寂静,他开口说话:“我叫东哥。”
他往酒吧外走去,阴四爷和坦克紧随其后,唐松怔了一下,也急步跟上。
他们走过两条街,没有人说话,每个人脑子里都在想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又或者是一片空白,他们隐隐意识到今晚可能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阴四爷感到兴奋,他终于确定苏树东不是随口说说。坦克无所谓,但开始有些佩服苏树东。唐松心中忐忑着,他见过太多的混混,但苏树东非常特别,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吸引着他,也让他害怕。苏树东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他发现自己整个过程一点也不紧张,他在监视胖子的时候,也在冷眼观察他这三个可能的伙伴,他们的表现让他感到满意。尤其坦克,证明了自身的打斗能力,还有头脑简单,这是一块璞玉,值得打磨与笼络。还有阴四爷的残忍让他感到惊奇,他没有想到阴三爷的儿子会是这样一个怪物,嬉皮笑脸、玩世不恭的另一面是惊人的暴戾和胆量。或者,每个人都有不被了解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松也值得继续观察。
苏树东拦了辆出租车,“去火车站。”
其他三人心中充满疑惑,但没有发问。几分钟后,他们在江城火车站的售票厅外下车。
“我有事,等会儿坐火车走。下周五我回江城。”苏树东简短地说。阴四爷没有向坦克和唐松介绍他的真实身份,他特别叮咛过。他们只知道他是阴四爷的家乡人。
“苏兄弟……”唐松上前一步嗫嚅着,表情紧张。
“你以为我是丢下你们独自逃跑?”苏树东清楚这位老混混的心思,问。
这一刻他的语气中透出瘆人的寒气,脸上的表情有些狰狞。唐松感到害怕,刚才的出手已经完全颠覆了自己对苏树东的印象,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了杀气。
“我不是胆小鬼。”苏树东语气柔和下来,“相信我,阴四爷可以替我保证。我下周五一定会重新出现在江城。我明天就会传呼你,如果真有什么事,我也可以马上赶回来。”
“肯定会有事的。今晚你们打的那个人是……”唐松苦笑。
“我打人之前,从不问他是谁。”苏树东缓慢地说。
刚刚进入黑道打拼的年轻人用这一句做作的话来显示自己的傲慢,标榜自己,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鼓励。但是后来,这句话被苏树东团伙每个混混挂在嘴边,并且渐渐变成某种凶悍和血腥的招牌。实际上,苏树东谨慎精明,在做一件事之前,喜欢做周密的考虑,跟老头子和聂山鹰一样,但诡异的是,在他刚刚进入黑道打拼的那一段时间,他做事的风格却是那样截然相反:鲁莽,狂妄,不计后果,肆无忌惮,甚至比当年以疯狂号称的蒋疯子还要疯狂。
“还有,你应该说‘今晚我们打的那个人’,你以为今晚跟你无关?你认为你跟我们三人无关?”苏树东冷冷地盯着唐松。
“苏兄弟,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怎么可能脱得了干系?他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唐松哭丧着脸。
这个时候,他的传呼响了,唐松的脸色更加难看,一副“看吧,这不找来了”的表情,他看了号码,松了口气:“苏兄弟,你朋友。”
苏树东找了公用电话回过去。
“我已经跟老顾联系过了,他答应不管这件事。剩下的事你们自己解决。”顾军淡淡地说。
“谢谢。改天我请你喝酒。”苏树东用同样平淡的语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