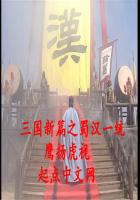狗儿先进屋,用灯笼照着亮儿,发现道衍正躺在床上,头枕瓷枕,左手支颐,眼睛却是亮灼灼的。此时燕王也悄然进来了,便笑道:“这和尚好无理!见本王来了,还在挺尸啊?”
道衍仍躺着不动。却说:“勿骚扰。老僧正坐禅呢!”燕王哧地笑道:“有你这样躺着坐禅的吗?”
道衍说:“这你就不懂了。昔临济在僧堂里睡觉,黄檗禅师过来,用柱杖敲了一下床板头。临济抬起头来,见是黄檗禅师,他理也未理,躺下又睡。黄檗禅师又敲了一下床板头,便往上间房去了。来到上间房,黄檗禅师看见首座在坐禅。黄檗就说:‘唉,下间的临济在坐禅,而你在这里妄想什么?’……你看,坐着的倒是‘妄想’,那躺着的,却是真正地坐禅呢!”说着,道衍也就坐起来。随即请燕王到外间房落座。
燕王落座后又与道衍调侃:“如此说,我倒成了黄檗禅师了吗?”
道衍也笑了。说:“你也不是黄檗,我也不是临济。但你我有缘。我知道你此时会来的。”
燕王便敛笑说:“你下午找我,有何事?”道衍说:“你先说,你心里有何事吧?”
燕王说:“我是想请教先生,永平那边,我要不要去解围?”
道衍摇摇头笑道:“大王不是为这事来的吧?”燕王想了想,也笑了。他也就不想绕圈子了,在和尚面前直吐胸臆说:“说实话,我是挂记着宁王……”道衍点点头说:“这就是了。你还挂记着宁王那边的朵颜三卫呢!”
燕王两眼一亮说:“啊呀,你真看到我心里去了!”道衍说:“我再给大王讲一个黄檗禅师与临济禅师的‘禅趣’。有一回黄檗来到厨房,问饭头说,‘僧人们一顿能吃多少米’?饭头说,‘二石五’。饭头又说,‘这还怕不够呢!’黄檗遂将饭头打了一棒。饭头觉得委屈,转告了临济。临济来到方丈见到黄檗。临济说:‘饭头不会说话,请和尚代替饭头下一转语。’黄檗说:‘你只管举说。’临济说:‘不是太多了吗?’黄檗说:‘来日再吃一顿。’临济说:‘说什么来日?’只今日便吃……”
燕王将这故事捉摸了一下,恍然大悟道:“你是说,宁王的朵颜三卫,我不要等待来日,今日便去吃它?”
道衍微笑道:“善哉,善哉!”燕王明白了道衍的意思。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他们都认识到,辽东那边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否则遗患无穷。
随即议定:待将士们休整数日后,燕王即亲带大军,赴永平解围。
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看起来只是对付包围永平的吴高、杨文,而觊觎着的却是宁王及其朵颜三卫。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道衍“如此这般”为燕王献上一条妙计。这条妙计的核心环节是对待宁王朱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极敏感,极复杂,所以现在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如果暴露了,极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甚或使燕王坠入深渊,永劫不复。三
正当燕军将士秣马厉兵,做着东征准备的时候,却从南方传来消息:李景隆已替换耿炳文充任“平燕大将军”,现已抵达德州,正收集耿炳文所部并檄调各路军马,估计有五十万,不日即会集河间。
带来这条消息的是一位自称“白发书生”的人,名叫高巍。这回李景隆北伐,他在军中谋了个“参赞军务”的差使。他先行一步,极潇洒地来到王府,叩响了端礼门,对守门将校说,“白发书生”高巍求见燕王殿下,有要事请教。
那时候燕王和道衍正在存心殿里商议对付官军北伐的事儿(他们已从谍报那里得知李景隆挂“大将军”印,准备北伐,具体情况却是不甚清楚),听说京师里来了人,自是非常重视。燕王先看了高巍通过门官递上来的手本儿,一时竟想不起这位高先生何人。问了问道衍,道衍拍拍脑门说,想起来了!却不就是高皇帝旌表过的那位大孝子吗?
原来,高巍在洪武十七年时,因其对亡母“蔬食并庐墓三年”,被洪武帝旌其孝行,并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最近他上书皇帝,毛遂自荐,甘冒杀身之祸,亲赴北平充当说客,劝燕王罢兵,向朝廷请罪。他想凭三寸不烂之舌,创造苏秦、张仪之类人物的奇迹。建文帝见其精神可嘉,遂批准北行。高巍当然不可能受到如李景隆那样的“饯于江浒”的礼遇,但他只身飘然过江时,心中倒油然生出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呢!
燕王听说高巍叩门求见,自然要弄明白来意。而一旦弄清了来意,便又犯了踌躇:对这位说客,见,还是不见?理,抑或不理?
燕王征求道衍的意见。道衍说,我看还是不见为妙。可否请他给殿下写一信,在信上把他的意思说一说。大王看了,再作理会如何?
燕王说甚好。便叫门官告诉高巍,说实在抱歉,王爷近日偶有小恙,未便于接待,且请先生于馆驿中住下。如先生有何事要谈,亦请先生写一便笺,卑职可以代呈殿下的。
高巍虽有些怏怏,也只好下榻于馆驿。当夜即写就一信,其情辞确乎慷慨激昂。
国朝处士高巍再拜上书燕王殿下: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见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诸臣,文者智辏,武者勇奋,执言仗义,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皆云大王借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隙奋击,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兵兴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地。且大王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生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洒泣流涕也。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迳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不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入?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以无愧矣。
燕王读了此信,虽怫然不悦,却不想杀高巍。他笑对道衍说,这个“白发书生”,他是想效郦食其,让我做齐王田广呢!我却不傻。我杀了他,岂不叫他一举成名,而令我遭万世唾骂乎?道衍也说,且不理他!我们还是商议自己的事吧!
于是高巍吃了闭名羹。弄得不尴不尬,无滋无味。住了数日,见燕王一直不肯会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高巍此番北平之行虽未取得成功,但他致燕王的书信却留于青史,成为当年燕王袭取大宁和保卫北平这两个大事件中的一段有趣的插曲儿。
高巍还在北平的时候,燕王已经召集众将,商议对付李景隆北伐军的策略。将领们听说李景隆有五十万人马,心头不免沉甸甸的。然而燕王听到这消息,不但不惊慌,倒是极高兴的模样。那一天在会上,他竟当着众将的面儿哈哈大笑说:
“李景隆?不就是乳名九江的那小子吗?哈哈哈,他来得好啊,我还真盼着是他来呢!”
将领们对他的这番话莫名其妙。连一向足智多谋的老将张玉也摸不着头脑。他便问燕王:
“大王何故为李景隆发笑呢?”燕王不忙于回答。倒是再问大家一句:“李九江此人,诸公熟悉否?”见无人应声,他才正色说道:“李九江乃我亲戚。其父岐阳王李文忠呼我皇考为舅父,论起来九江应尊我为表叔。我对这小子可谓知根知底。这小子乃膏粱竖子,纨绔少年,华而不实,徒有一副好相貌儿。我评论此人有四句话二十字,即:‘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成,忌刻而自负。’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说罢,燕王摸过茶碗呷了一口,抹抹唇髭,等待着大家发话。
道衍听得津津有味。他一面习惯性地捻着胸前的念珠,一面不住地点头。可以说,在这所有的人里,惟有他和燕王的神情是轻松的。刚才燕王对李景隆的评价,本是他和燕王一起捉摸的,但此时却故作不解地问:“据大王看来,朝廷选李景隆为将,是选错人了!”
“确是如此”。燕王说,“李九江这小子未尝习兵,不曾大战,只不过胡乱诌得几句‘兵法’。不想我侄儿允炆竟敢以五十万兵马托付于他。唉,允炆这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呢!”
道衍又帮腔儿说:“听说今上对李景隆宠敬有加。不惟赐了节钺、通天犀带、尚方宝剑,还为其行了推毂礼,礼数儿胜过汉高祖拜韩信呢。”
燕王嘁地一笑说:“此正是我侄儿可悲处也。昔汉高祖宽宏大度,知人善任,使天下英雄为其所用,他亦不过统兵十万。惟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而九江这小子何等才?竟付给他五十万兵马,实可笑可悲至极!”
说到这里燕王讲述了战国时赵括的故事。赵括为名将赵奢之子。他只知侈谈其父兵书,却不能通变。可惜赵孝成王以他代替廉颇为将,结果在长平一战中大败。他本人被射死,麾下四十万赵国将士全被秦将白起坑杀。赵国自此一蹶不振。燕王将李景隆与赵括相提并论,说道:“李九江连赵括都不如。他来打我,必败无疑!”
燕王接下来分析“李景隆必败”的原因。他认为,除了“死读兵书,不知通变”而外,还有:“政令不修,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其败一也;贪而不止,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勿扰,其败二也;好谀喜佞,专任小人,嫉贤妒能,气量褊狭,贪色嗜痂,其败三也……”他一口气说了诸多弱点,而这皆是为将者的致命弱点。所以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战争还没开始,胜负已成定局。
将领们听了燕王对李景隆淋漓尽致的分析,心里有些豁然,忧心忡忡的神情渐渐消失。其中有个人对燕王这番话尤其佩服。他就是顾成。顾成乃军界老人儿,又与李景隆共过事,他对李景隆也有所了解。故而慨而慷之道:“殿下真把此人的五脏六腑都看得透彻分明啊!”道衍便停止了捻佛珠。兴趣盎然地问顾成:“听这话,顾老将军对李九江亦是知根底的了?”
“唉!一言难尽。”顾成说,“别的姑且不论,单是殿下方才批他的‘贪而不止’,我提一件事,诸位听了或许都不敢相信呢!”
顾成说的是去年夏天,李景隆奉了建文密诏,带兵去开封逮捕周王。进得王府,未曾见得周王面,先已被这儿那儿的奇珍异宝馋得心跳,垂涎三尺。唐朝吴道子的一幅中堂人物和宋徽宗的一幅斗方花鸟,硬是被他从墙上摘下,塞入私囊。他还想跟周王索要武则天用过的什么砚台,曹植佩过的什么玉璧、玉圭之类,但周王没有答应。转到后花园时,看到宋徽宗办“花石纲”时遗留下来的两块太湖石,又是赞叹不绝,可惜难以搬运,只好作罢,总之,此人之贪婪,说起来令人齿冷呢。
燕王听顾成这么一说,不禁又惊又怒。说真的,这种“趁火打劫”打到亲王身上的事,他还是头一回听到。心里话,也惟有李九江这竖子能做得出来呢!周王是他亲弟,提及周王受屈辱的事儿,他心里就隐隐发疼,就窜无名火儿。此时他气得又吹胡子又瞪眼,问顾成:“九江如此大胆妄为,就无人告发吗?”
顾成叹道:“唉!今上对景隆眷宠甚重,又顾及岐阳王的名誉,就把这事儿给压下了。”燕王鼻子里哼一声:“这便是允炆的不对了。”道衍说:“故此才可说南军‘必败无疑’呢!”接着顾成的话题,人们议论纷纷,对李景隆的人品皆嗤之以鼻。但也有人对燕王方才评论其“贪色嗜痂”不能理喻。“嗜痂”即嗜好吃疮痂,莫非李景隆真有刘邕那样的怪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