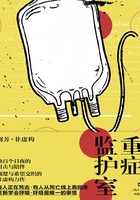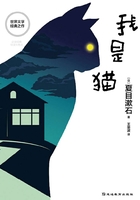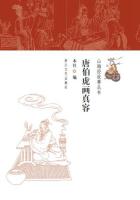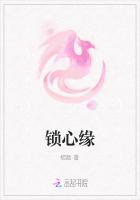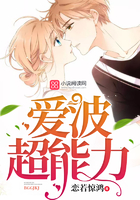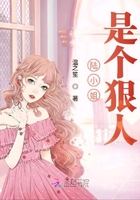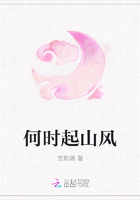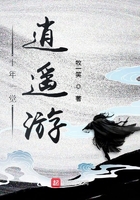/王充闾/
传统戏曲里有一出“访白袍”的戏,表演的是唐朝大将尉迟恭寻访“白袍小将”薛仁贵的故事。我这里却讲寻访“大红袍”。“大红袍”,原是武夷山岩茶中之佼佼者,素有“茶王”之誉。我们所要寻访的就是这种茶树。
几位文友此刻正行进在武夷山风景区的“九龙窠”里。溪涧潺潺,流淌在错错落落的鹅卵石上,一路上弹出淙淙的琴响。面对这种山川丽景,友人竟情不自禁地高声朗吟起来:“云麓烟峦知几层,一湾溪转一湾清。行人只在清溪里,尽日松声夹水声。”原来这是宋代“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的诗,他写的正是武夷山一带的景观——峰峦重叠,清溪曲折,水声松籁,不绝于耳。闽北风光宛然如画。
走着走着,看到一小片茶园,枝株茂密,叶片微呈红晕。几个人同时喊出:“看,这就是了。”谁知,错了:它是“大红袍”的老弟——“小红袍”。
又拐了一个弯,前面略显开阔,却不见了茶园,小石丘上独有茶亭翼然。在高山悬崖之间,由石块垒起的台座上,果然长着几株茂密的茶树,旁边还隐约可见镌刻在岩石上的“大红袍”三个字。由于山势高耸,距离较远,茶树的具体形态看不太清楚。东道主介绍说,这几棵“茶王”生长时间很长了,枝干弯弯曲曲,长满了苔藓,又浓又绿的叶片间夹杂着一簇簇的嫩芽,边缘上都呈紫红色。传说从前是靠训练猴子攀崖采摘,后来从旁边石罅里凿出一条缝隙,架上悬梯,茶工可以勉强上去,采摘之后,悬梯立即撤除,因为这是“国宝”啊。
相传古时候一个读书士子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了,下山化缘的老方丈发现后,叫来两个小和尚把他抬到庙里。方丈见他面色苍白,体瘦腹胀,便泡上一壶好茶,服侍他饮下。士人见茶叶绿地红边,泡出的茶水黄中带红,如琥珀一样光亮,遂呷了几口,顿觉口角生津,芳香四溢。连续喝了几次,鼓胀全部消退,身体健康如常。谢过老方丈,他便赴京投考,竟得状元。不忘救命之恩,状元郎重返武夷山,在老方丈导引下,寻访这半山腰的神奇茶树。这天,他正跪在山下虔诚地焚香礼拜,忽然一阵风来,把猩红状元袍卷上了半空,不偏不倚,恰巧罩在“茶王”的枝头,宛如红云一片。“大红袍”遂由此得名。
说着,一行人已上到茶亭坐下。女老板提着水壶汲来了山泉,用硬炭升起了炉火,顷刻间壶中便冒起了热气。她左手端过一个古香古色的茶盘,上面摆放着比拳头稍大的紫砂壶和几个酒盅般大小的茶杯;右手托着一个贮存茶叶的锡罐。茶叶放进壶中,注入滚沸的水,并用开水将茶壶淋过。两分钟过后,便提壶在各个杯中先斟少许,然后再均匀地巡回斟遍,最后将剩下的少许茶水向各杯点斟。据说这里头有个名堂,头一次叫“关公巡城”,第二回为“韩信点兵”。
天色向晚,同伴们向女老板致谢,说有幸在这里品尝到了“大红袍”这种人间至味。女老板却歉疚地摇摇头,说,准备不周,十分抱歉,今天我这里只有“小红袍”。当然,这也不是凡品。
不晓得这种“小红袍”与“大红袍”有没有亲缘关系,颇悔当时没有询问清楚。
喝茶
/金受申/
品茶与饮茶
茶道在中国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向来以“品茶”和“饮茶”分为不同的“茶道”。陆羽《茶经》, 即谈的是品茶。换句话说,即是欣赏茶的味道、水的佳劣、茶具的好坏(日本人最重此点),以为消遣时光的风雅之举。善于品茶,要讲究五个方面:第一须备有许多茶壶茶杯。壶如酒壶,杯如酒杯,只求尝试其味,借以观赏环境物事的,如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并不在求解渴,所以茶具宜小。第二须讲蓄水。什么是惠山泉水,哪个是扬子江心水,还有初次雪水,梅花上雪水,三伏雨水……何种须现汲现饮,何种须蓄之隔年,何种须埋藏地下,何种必须摇动,何种切忌摇动,都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须讲茶叶。
何谓“旗”,何谓“枪”,何种须“明前”,何种须“雨前”,何地产名茶,都蓄之在心,藏之在箧,遇有哪种环境,应以哪种水烹哪种茶,都是一毫不爽的。至于所谓“红绿花茶”,“西湖龙井”之类,只是平庸的俗品,尤以“茉莉双窨”,是被品茶者嗤之以鼻的。第四须讲烹茶煮水的功夫。何种火候一丝不许稍差。大致是:“一煮如蟹眼”,指其水面生泡而言,“二煮如松涛”,指其水沸之声而言。水不及沸不能饮,太沸失其水味、败其茶香,亦不能饮。至于哪种水用哪种柴来烧,也是有相当研究的。第五须讲品茶的功夫。茶初品尝,即知其为某种茶叶,再则闭目仔细品尝,即知其水质高下,且以名茶赏名景,然后茶道尚矣!
至于饮茶者流,乃吾辈忙人解渴之谓也。尤以北方君子,茶具不厌其大,壶盛十斗,碗可盛饭,煮水必令大沸,提壶浇地听其声有“噗”音,方认为是开水。茶叶则求其有色、味苦,稍进焉者,不过求其有鲜茉莉花而已。如在夏日能饮龙井,已为大佳,谓之“能败火”。更有以龙井茶加茉莉花者,以“龙睛鱼”之名加之,谓之“花红龙井”,是真天下之大噱头也。至于沏茶功夫,以极沸之水烹茶犹恐不及,必高举水壶直注茶叶,谓不如是则茶叶不开。既而斟入碗中,视其色淡如也,又必倾入壶中,谓之“砸一砸”。更有专饮“高碎”、“高末”者流,即喝不起茶叶,喝生碎茶叶和茶叶末。有的人还有一种论调,吃不必适口而必充肠之食,必须要酽茶,将“高碎”置于壶,蔗糖置于碗,循序饮之,谓之“能消食”。
还有一种介于品茶与饮茶之间的,若说是品茶,又蠢然无高雅思想,黯然无欣赏情绪。若说是饮茶,而其大前提并不为解渴,而且对于茶叶的佳劣,辨别得非常清楚,认识得非常明确,尤其是价钱更了如指掌,这就是茶叶铺的掌柜或大伙计。
每逢茶庄有新的茶样到来,必于柜台上罗列许多饭碗,碗中放茶叶货样少许,每碗旁并放与碗中相同的茶样于纸上,以资对照与识别。然后向碗中注沸水,俟茶叶泡开,茶色泡透,凡本柜自认为能辨别佳劣的人物,都负手踱至柜前,俯身就碗,仔细品尝。舌吸唇击,啧啧有声。其谱儿大者又多吸而唾于地上,谓之“尝货样”。大铺尝货样多在后柜,小铺多在前柜,实在是有意在顾主面前炫耀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