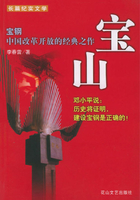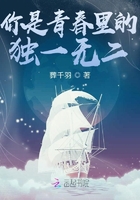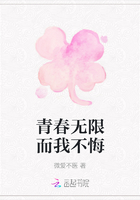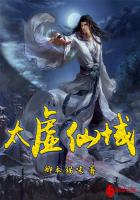/郑启五/
貌似平常的汉语“茶园”一词,却因为中华地域的不同而导致内涵多义,又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引发外延的新义。
北京的“茶园”是过去北京人听戏之处,即在茶座中加筑一个小戏台,观众可一边品茶,一边赏戏,同时店家还供应点心、小吃。最有名的是创建于1933年,现经翻修面貌一新,并由戏剧大师曹禺题名的“天桥乐茶园”。该茶园仿老北京的茶园戏楼构筑,经营上分戏部、茶部、食部三部,早、午、晚三场轮番演出各具特色的节目,如再现老北京市井百姓的众生相、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品尝百样吃食。笔者几度进京,却无缘光顾,幸好作家陈建功在《北京滋味之“天桥乐”的红灯笼》里绘声绘色的描写,得以聊补:“茶园子分两层,楼上是包厢,楼下是散座,南端是一个小舞台。进得店来,店家发给每一位客人五枚旧式的铜毫。到包厢里或散座中坐定,身着长袍马褂的主事立刻吩咐茶房给您上茶。
您如果进的是包厢,只听一声吆喝,一个白生生的物件就从楼下飞将上来,原来是扔上来了手巾把儿。一楼散座的四周.是卖酱牛肉、艾窝窝、驴打滚、杏仁茶、豌豆黄……各类小吃的摊位,胸前挎着笸箩的小姑娘,游走于茶座间,卖糖葫芦,卖瓜子香烟,您可以凭那几个铜毫,随意选用。就在这和旧京茶园几无二致的氛围里,小舞台上的表演开始了。节目,意在重现旧天桥的‘绝活儿’:串场的是‘小金牙’,一边拉着洋片儿,一边把一个个节目给报了出来,其间插科打诨,滑稽风趣自不可少。唱八角鼓的、数莲花落的、变戏法的、耍把式的、摔跤的……一个一个出来亮相。”陈建功真见“功夫”,文字推拉出的镜头活灵活现,而以往在电视里电影里也时有所见,可见北京的“茶园”热热闹闹,听京戏赏曲艺看杂耍,吆喝声声,早就喧宾夺主了,喝茶越发显得次要。
“茶园”移转到了西南,就是喝茶当头,茶博士与茶客为了一个共同的“茶”字走到茶园来。1993年我首次飞抵成都,留下《文殊院品茶》的文字,“文殊院茶园布下的竹椅阵阵容雄威,‘露天八卦阵’置于庭院,‘室内方阵’安于斋堂,另有‘长蛇阵’见缝插针地罗列在走廊上。任它风雨和阴晴,管它秋夏与春冬,闲适的茶园横陈于不败之中。千张竹椅千位客,茶园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茶客偶尔变换着坐姿,竹椅四下吱扭有声一如绿野秋虫的吟唱。椅间游走的脚是添水的茶园伙计——茶博士。
他一停步一抬手,沸水一注便从天而降,瞬息之间一汪翠色的茶汤含烟泛珠,正好齐了杯沿,且滴水不溢!茶园的中枢是茶房,位于庭院和斋堂的结合部,那老旧的茶房里木橱、铜壶、灶台以及橱内那一溜一溜的白瓷盖碗,联手营造着陈古的香色。茶房墙壁上悬着张黑板,告示着茶的等级与售价。茶园中以茶会友的大有人在;自带点心,以茶代餐的,更不乏其人。点心大至包子油条,小至花生米怪味豆,不一而足。老人们双目半闭,瘫坐在大靠背的竹榻上,慢斟细嚼,好一派低消费高享受的早茶乐!我入园随俗,仰靠在竹椅上,潇潇洒洒当一回成都人。虽与‘左邻右舍’脉脉不得语,却共享着这溢满茶香的晨光。”顺着旧文,笔者似乎又过了一次茶馆瘾,成都的“茶园”是茶的一统天下,尽管也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好吃的名堂,但用我们闽南话来说,这些大大小小油油酥酥的吃食都可一概称为“茶配”——茶之配角也。
在我们福建,茶园既非看戏的,也非饮茶的,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种茶的田园或山地,茶园茶园,茶树安居的家园嘛,所以贵客光临八闽想喝茶想看戏千万别说什么“茶园”,否则就南辕北辙了!不过南辕北辙就南辕北辙,没准歪打正着呢,因为有些种茶的茶园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例如安溪县大坪乡的高山茶园。冬日去大坪的感觉很奇特,车一直在呼呼地爬山,当抵达群山之巅的时候,眼前却突然出现一片平原——一片翠绿色的高山平原。平原的中心有一个相当繁华的村镇,四周的山包则全是茶园,梯田式的茶园层层叠叠,像排天的绿色波浪,全世界最好的‘毛蟹’乌龙茶就出产在这里。人们把大坪誉为“茶海明珠”,不但诗意和抒情,而且极为贴当和形象。我还进一步爬上一个叫“迎仙埔”的生态观光茶园,山高风寒,气温至少比山下要低5到6度,游客套上了风衣还缩头缩脑的,而“迎仙埔”所有的山包都披着和暖的绿色盛装,昂首挺胸地迎接着来访的“仙人”!进入茶园之中,这下在远处所见到的绿浪全变成了绿龙,一畦畦的茶灌木就像一条条肥壮的绿色长龙,蜿蜒而去,难见首尾……
但八闽大地种茶的“茶园”也非一成不变,至少目前就有两个闪烁的亮点:一为“乐园化”,你瞧瞧闽西的“云顶茶园”,在苍翠养眼的茶园中兴建游客服务中心,让游人在郁郁葱葱中把玩与吃喝,神迷与心醉。二为“田园化”,你看看闽南的生态茶园,那茶园的四周种上酸枣和香椿等树木,形成保护林带;在茶树间套种杨梅、余甘、橄榄和黄豆,以增加茶园行间的绿色覆盖,还在茶园梯壁上种植百喜草与爬地兰,以提高茶园的保植能力,可谓班驳苍翠,好看又实惠。茶叶是植物万叶中最敏感的精灵,在田园的轻风细雾中茶香悄然与果香、草香、叶香、豆香形成互补与融合。我想灵巧的采茶姑娘正在用她们勤快的双手谱写着新的《采茶扑蝶》,“左手一把茶,右手一枝梅,满头都是绿橄榄呀绿呀绿橄榄……”
同为“茶园”各不同,或听戏找乐,或喝茶会友,或植绿发家,或静心养生,但总归离不开一个“茶”字,一个人与草木自然和谐亲密相处的“茶”字,品饮品味,有意思更有滋味,我想在新生活明媚灿烂的阳光里,“茶园”还会跟随着闲适的生活衍生出更多健康与快乐的元素,但万变不离其宗,终归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精神家园。
门前的茶馆
/陆文夫/
早在四十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两三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爿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图,十分有趣。
每至曙色朦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
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作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
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担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歇,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间或还有卖唱的,一个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那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见到的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
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孵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就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各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