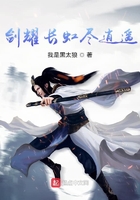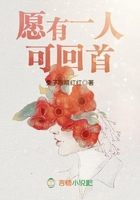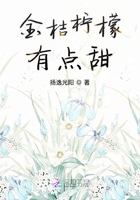自然,物品味道的本身,是很有关系的;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日常应用的太普通了吧,喝茶的情趣,无论如何,总来不及喝酒风雅。这当然不是说自来被传着关于它的逸事、隽语,是连鳞片都找不出的。譬如“两腋生风”、“诗卷茶灶”,这都是值得提出的不可淹没的佳话。但我们仍然不能不说酒精是比它有力地大占着俊雅的风头的。举例是无须乎的,我们只要看诗人们的支籍中,关于“酒”字的题目是怎样多,那就可以明白茶是比较不很常齿于高雅之口的东西。话虽如此说,但烹茗、啜茗,仍然为文人、僧侣的清事之一。不过没有酒那样得力罢了。
吟咏到茶的诗句,合拢起来,自然是有着相当的数量的;可是此刻我脑子里遗忘得几等于零。翻书吧,不但疏懒,而且何必?我们所习诵的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虽然是说到茶的烟气的,但我却很爱这个诗句,并因之常常想起喝茶的滋味。“从来佳茗似佳人”,这是东坡的一句绮语。我虽然觉得它比拟得颇有些不类之诮,但于茶总算是一个光荣的赞语吧。不知是哪位风雅之士,把此语与东坡另一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作起对来,悬挂在西湖上的游艇中。这也是件有趣味的事吧。
岭表与江之南北,都是有名产茶的地方。因为从事于探撷的工作者,大都是妇女之流的缘故吧,所以采茶这种风俗,虽没有采莲、采菱等,那样饶于风韵,但在爱美的诗人和民间的歌者,不免把它做了有味的题材而歌咏着。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中,录有采茶歌数首,情致的缠绵,几于使人不敢轻视其为民间粗野的产品。记得幼时翻过的《岭南即事》里面,也载着很逗人爱的十二月采茶歌。某氏的《松萝采茶词》30首,是诗坛中吟咏此种土俗的洋洋大著吧。就诗歌本身的情味来说,前两者像较胜于后者(这也许是我个人偏颇的直观吧?),但后者全有英文的译词(见曼殊大师所编著的《汉英文学因缘》Chinese—EnglishPoetry),于声闻上,总算来得更为人所知了。
双双相伴采茶枝,
细语叮咛莫要迟。
既恐梢头芽欲老,
更防来日雨丝丝。
今日西山山色青,
携篮候伴坐村亭。
小姑更觉娇痴惯,
睡倚栏干唤不醒。
随便录出两首在这里,我们读了,可以晓得一点采茶女的苦心和憨态吧。
如果咖啡店可以代表近代西方人生活的情调,那么,代表东方人的,不能不算到那具有古气味的“茶馆”吧。的确,再没有比茶馆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东方人那种悠闲、舒适的精神了。在那古老的或稍有装潢的茶厅里,一壶绿茶,两三朋侣,身体歪斜着,谈的是海阔天空的天,一任日影在外面慢慢地移过。此刻似乎只有闲裕才是他们的。有人曾说,东方人那种构一茅屋于山水深处悠居着的隐者心理,在西方人是未易了解的。我想这种悠逸的茶馆生涯,恐于他们也一样是要茫然其所以的吧。近年来生活的东方化西方化的是非问题。闹得非常地响亮;我没有这样大的勇气与学识,来作一度参战或妄图决判的工作。但东方人——狭一点说,中国人这种地方,所表现的生活的内外的姿态,与西方人的显然有着不同,是再也无可怀疑的。
说到这里,我对于茶颇有点不很高兴的意态;倘不急转语锋,似乎要写成咒茶文来也未可知。还是让我以闲散的谈话始终这篇小品吧。有机会时,再来认真说一下所谓东西文化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似乎只有“荼”字没有“茶”字,——据徐铉说,荼字就是后来的茶字。这大约因为那时我们汉族所居住的黄河流域,不是盛产茶的区域吧。又英语里的茶字作tea,据说是译自汉语的。我们乡下的方言,读茶作“de”,声音很相近;也许当时是从我们闽、广的福佬语里翻过去的也说不定呢。
高濂的《四时幽赏录》,是西湖风物知己的评价者。他在冬季的景物里,写着这样一段关于茗花的话:“两山种茶颇蕃,仲冬花发,若月笼万树。每每入山寻茶胜处,对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种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云绡,心黄俨抱檀屑。归折数枝,插觚为供。枝梢苞萼,颗颗俱开,足可一月清玩。更喜香沁枯肠,色怜青眼,素艳寒芳,自与春风姿态迥隔。悠闲佳客,孰过于君?”(《山头玩赏茗花》)碎踏韬光的积雪,灵峰的梅香,也在高寒中嗅遍,去年的冬天,总不算辜负这湖上风光了吧。但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文人笔下极力描写着而为一般世人所不愿注意的茶花。今年风雪来时,或容我有补过的机会吧。否则,两山茶树,或将以庸俗笑人了。谁能辩解,我们每天饮喝着它叶片的香气,于比较精华的花朵,反不能一度致赏!
我和茶
/叶君健/
茶和我的生活,甚至工作发生关系,是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就是在抗战期间。1940年我从香港绕道越南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教书。学校在沙坝坪。那里有条小街,街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店铺,只有一个茶馆,颇为热闹,它总是宾朋满课。原来那个地方“哥老会”的朋友们很多,他们相会的地方就是这个茶馆。战时的住房紧,我住在学校宿舍,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把房间塞满了。我要会朋友或与朋友聊天,就只有去那个茶馆。茶馆所提供的茶是有名的四川沱茶。茶很浓,味带苦涩,非常提神,是聊天的最好兴奋剂。不知不觉之间我喝这种茶上瘾。不去那个茶馆的时候,我就在我那个小房里喝起来——独酌,配合我的“读书”。我发现浓茶会提高读书的理解力,因为茶可以活跃脑子的想象力。
1944年我去了英国。那时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英国被德国的潜艇封锁,生活物资运不进来,沱茶当然没有了。好在我天天得到英国各地去巡回演讲有关中国人民抗战的事迹。英国人民也被动员了起来,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努力。刺激头脑的事情时时刻刻都有,没有沱茶也不觉得有所失。我真正想喝点什么的时候,就拧开自来水管——在去重庆以前我就是这样解决“渴”的问题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茶。但在英国,茶还是要饮的,不过茶的性质及饮它的目的不同——实际上它是饭食之一种。
茶这种植物原是中国人发现的,饮茶这种习惯也是首先在中国人中间传开——据传说,神农在位期间,纪元前2737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饮茶。但是中国最古的辞书《尔雅》里记载的茶作为人民生活中的饮料,实在纪元后350年才开始。倒了18世纪末,饮茶的习惯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唐代文人陆羽(733—804)还专门写了一部《茶经》,论述茶的形状、品质、产地、产制方法及应用等问题。唐朝政府甚至还征收茶税。日本从唐朝引进了饮茶的习惯,竟然在13世纪末也出版一本有关《茶道》的著作。欧洲文献中最初出现于威尼斯的著名哲学家建姆巴蒂斯塔.。胡歌.万.林一叔丹写的《旅游记》才得知“茶”这种饮料。到了17世纪中叶,茶已经开始在英国普及了。1657年伦敦的加尔威咖啡馆开始公开卖茶。1658年伦敦《政治信使报》第一次登了这样一则关于茶的广告:
那种美妙的、被医务界所认可的中国饮料,中国人名之谓“茶”。别的国家叫做“泰”,又名“德”,现在在斯魏丁.伦兹街的“苏丹总咖啡馆”,由伦敦的皇家交易所出售。
饮茶的习惯就这样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英国成了西方的主要饮茶国。但英国人所饮的茶却和我们的不同。当茶叶最初在英国出售的时候,它每磅的价格大概相当于现在至少六十到一百英镑,相当于现价五百到一千人民币。这样价钱的茶当然只有贵族才能品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茶园,大量生产茶叶。因为气候的关系,这种茶叶既粗又黑又涩,即英国所谓的“黑茶”,我们把它叫做“红茶”。英国人喝它的时候在里面加进牛奶和糖。这样的茶就不是“品”的饮料了,而是食物的一种。英国人吃早饭的时候有它,上午十点多钟打尖的时候有它,下午四点来钟“小吃”的时候也有它。有些英国人甚至把它配以三明治、沙拉和电信当做晚饭,即所谓“高茶”。每天人们就这样伴着饭食“吃”几次茶,此外就从不“泡茶”作“品”的享受。但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办公桌上随时随地都放着泡好的一杯茶,当然也随时随地地“品茶”。甚至公共汽车司机在行车的时候,也要在他的座位旁边放一大杯泡好的茶。
我在英国住了近六年,虽然天天要“吃”几次茶,但真正渴的时候还得开自来水管,用漱口杯或用嘴对着它饮几口。我在重庆习惯了的沱茶,当然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再与它重逢的时候,是在1949年冬,我回国以后。从此“黑茶”们成为记忆了,因为中国的饭食和它配不上套。沱茶又成了我在家接待朋友或读书的陪伴。我对茶的经验也只限于这个范围。有关沱茶(除四川以外还有云南产品)的学问,据说很广,但除了上述范围外,我就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了,因为我对它的体验不深。我喝茶大部分在晚间。我的办公桌的抽斗里从没有茶叶,桌上自然也没有茶杯。一晃三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倒是现在当了“顾问”以后,也就是过了花甲之年以后,我不需坐班,得有机会到国内许多地方(有不少还是名胜地)去跑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承他们的厚谊,每年我总要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本地新茶,我“品”起来倒还带味。我当然谈不上是什么茶的鉴赏家,但近十多年来我“品”过的茶种确实不少。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很简单:中国的美好东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种。但它并不像其他珍贵的东西,它既高雅,又大众化,没有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不完整——柴、米、油、盐、酱、醋之外,还必须有茶。可惜这个真理,我只有在生活中兜了好大一个大圈子以后才悟出来,未免觉得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