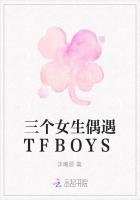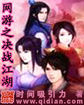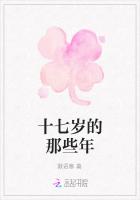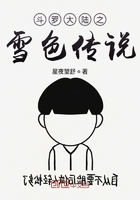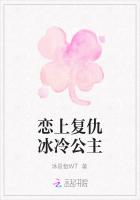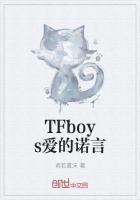兔毫盏失传七百多年了,现有新闻报道福建建阳县池中瓷厂,把这仿古瓷品制作成功,放出光华。这种瓷杯有着乌金般的黑釉,釉面浮现着斑点和状如兔毫的花纹。又传闻四川省的广元窑也仿制兔毫盏,造型、瓷质、釉色与建窑的兔毫纹相同,很难区别。这真是值得高兴的事。
吃茶文学论
/阿英/
吃茶是一件“雅事”,但这“雅事”的持权者,是属于“山人”“名士”者流。所以往古以来,谈论这件事最起劲,而又可考的,多居此辈。若夫乡曲小子,贩夫走卒,即使在疲乏之余,也要跑进小茶馆去喝点茶,那只是休息与解渴,说不上“品”,也说不上“雅”的。至于采茶人,根本上就谈不上有什么好茶可喝,能以留下一些“茶末”“茶梗”,来供自己和亲邻们享受,已经不是茶区里的“凡人”了。
然而山人名士,不仅要吃好茶,还要写吃茶的诗,很精致的刻“吃茶文学”的集子,陆羽《茶经》以后,我们有的是讲吃茶的书。曾经看到一部明刻的《茶集》收了唐以后的吃茶的文与诗,书前还刻了唐伯虎的两页《煮泉图》,以及当时许多文坛名人的题词。吃茶还需要好的泉水,从这《煮泉图》的题名上,也就可以想到。因此,当时讲究吃茶的名士,遥远地雇了专船去惠山运泉,是时见于典籍,虽然丘长孺为这件事,使“品茶”的人曾经狼狈过一回,闹了一点把江水当名泉的笑话。
钟伯敬写过一首《采雨诗》,有小序云:“雨连日夕,忽忽无春,采之瀹洺,色香可夺惠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系其四角,而石压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瓮中庭受之。避雷者,恶其不洁也。终夕缌缌焉,虑水之不至,则亦不复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厌,亦居心转境之一道也。”在无可奈何之中,居然给他想出这样的方法,采雨以代名泉,为吃茶,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概见了;张宗子坐在闵老子家,不吃到他的名茶不去,而只耗去一天,又算得什么呢?
还有,所以然爱吃茶,是好有一比的。爱茶的理由,是和“爱佳人”一样。享乐自己,也是装点自己。记得西门庆爱上了桂姐,第一次在她家请客的时候,应伯爵看西门那样的色情狂,在上茶的时候,曾经用首《朝天子》调儿的《茶调》开他玩笑。那词道:“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揪不采叶儿渣,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口儿里常时呷,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他。原来一篓儿千金价。”拿茶比佳人。正说明了他们对于两者认识的一致性,虽说其间也相当的有不同的地方。
话虽如此,吃茶究竟也有先决的条件,就是生活安定。张大复是一个最爱吃茶的人了,在他的《全集》里笔谈里,若果把讲吃茶的文章独立起来,也可以印成一本书。比他研究吃茶更深刻的,也许是没有吧。可是,当他正在研究吃茶的时候,妻子也竟要来麻烦他,说厨已无米,使他不得不放下吃茶的大事,去找买米煮饭的钱,而发一顿感叹。
从城隍庙冷摊上买回的一册日本的残本《近世丛语》,里面写得是更有趣了。说是:“山僧嗜茶,有樵夫日过焉,僧辄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师嗜之甚也?’僧曰:‘饮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欲三也。’樵夫曰:‘师所谓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苏以给食,豆粥藜羹,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饥也。明而动,晦而休,晏眠熟寐,彻明不觉,虽南面王之乐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劳苦也。小人有妻,能与小人共贫窭者,以有同寝之乐也,若嗜寡欲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贫也。夫如则,则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辞。’”可见,吃茶也并不是人人能享到的“清福”,除掉那些高官大爵,山人名士的一类。
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那一方面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八九年前,芥川龙之介游上海,他曾经那样的讽刺着九曲桥上的“茶客”;李鸿章时代,外国人也有“看中国人的‘吃茶’,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无救”的预言。然而现在,即使就知识阶层言,不仅有“寄沉痛于苦茶者”,也有厌腻了中国茶,而提倡吃外国茶的呢。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叹了:“呜呼!吾欲无言!”
茶之梦
/忆明珠/
说茶是我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大概不为过,我之于茶,已是“不可一日无此君”,更甚而至于“不可一夜无此君”。许多人睡前不吃茶,因为茶能提神,兴奋大脑,影响睡眠。我则相反,临上床时必重沏一杯浓茶,放在床头柜子上,喝上几口,才能睡得安适。半夜醒转还要喝,否则口干舌燥,断难重新入睡的。民间说法:茶,可以明目,可以清心。我的经验除了这些功效,茶还可以滤清梦境。我善于做梦,年轻时夜夜有梦如花。老来仍多梦而不衰,只是梦境渐趋清幽旷远,所谓“归绚烂于平淡”也。偶尔有噩梦惊扰,细细排查,大都是睡前疏忽了喝上几口茶的缘故。有位医生对我的茶可滤梦之说,报以轻蔑的微笑,说:“你肝火太旺了吧?”痴儿不解,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我不喜欢红茶,无论怎样名贵的红茶,“玉碗盛来琥珀光”——我嫌它太像酽酽的酒了。我不怕睡过去,但怕醉过去,我宁要梦乡而不愿坠入醉乡。还拒绝花茶,因它的香是外加,是别的花的香。就像一个被脂粉擦香了的女人,香是香的,香得刺鼻,却无一点女人自身的气息了。奇怪的是,女人们不但喜欢涂脂抹粉,且又往往喜欢吃花茶,难道还嫌她们外加的香不够多的吗?
我只饮用绿茶,一因它的绿,绿是茶的本色;二因它的苦,苦是茶的真味。闻一多诗云:“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我断定他这壶苦茶必是绿茶。是绿茶沏出的一壶苦;同时又是苦茶沏出的一壶绿。这茶却又是清淡的,是清淡的绿与清淡的苦的混合。一壶春茗在手,目中有绿,心中有苦,这才能进入境界,成为角色,否则,终不能算作茶的知音。
这里顺便说说,我极叹赏闻一多的这句诗,可题上画幅,可镌入印章。郭小川诗有“杯中美酒,盘中水饺”八字,亦佳,但只宜题画而不宜入印。新诗以句胜者凤毛麟角,远不如古典诗词的警策。这或许由于古典诗词以句为造境单位,而新诗造境动辄以段、以节,空大其壳,经不起单摘。此中利弊,似颇需诗人们善自斟酌。
现在再回到茶上来。吃茶正式成为我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至今已积有三十余年。换句话说,我的下半生是被茶的绿和苦浸透了的。十年“文革”浩劫,也不曾间断这绿和苦的浸透,真是个奇迹。当然,这该归功于我的妻子,她像数算着一颗颗珍珠似的,谨慎地数算着当时勉强维持一家最低生活水准的那点点费用,尽最大努力保证供应了我那“一壶苦茶”的“粮食”。记得深更半夜里,突然停电了。她从哪里摸出半截红烛,点上,又为我重沏上一杯茶,这情景,很容易调动诗兴。但,她这是为了让我不误时限,赶写出明天就要交上去的“认罪书”啊!我是在写着“认罪书”的时候,在半截红烛的光照之下,凝视着手边的那杯茶,才感悟到茶的绿,不但是茶的本色也是生命的本色;而茶的苦,不但是茶的真味也是生命的真味啊!“认罪书”一遍遍地写着,我却仍有着一夜夜的安睡。这么说,茶可以滤清梦境,安人魂魄,又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