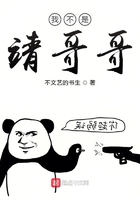“他向你要过或从你那儿拿过钱吗?”“没有,从来没有!”“你知道他可能有什么目的吗?”“没看出,除了他说的那件事。”“你告诉他我们的电话约会了吗?”“我说了。”福尔摩斯沉默了,我看得出他有些疑惑不解。“你的收藏里有珍贵的东西吗?”
“没有,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我没钱,虽有许多收藏品,但也不值多少钱。”
“你不怕别人偷吗?”“一点不怕。”
“你住这屋子有多少年了?”“差不多五年了。”这时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主人刚一拉开门闩,那位美国人就兴奋地闯进来了。
“找到了!”他摇着一张报纸大声叫道,“我想我该马上告诉你。内森·加里德布先生,祝贺你!你发财了。咱们的事情圆满结束,万事大吉。至于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只能说,让你白跑一趟了,真不好意思。”他把报纸递给主人,主人站在那里仔细看报上的大字广告。福尔摩斯和我也伸长脖子从他身后看去,上面登的是:
农机制造商霍华德·加里德布经营捆扎机、收割机、蒸气犁及手犁、播种机、松土机、农用大车、四轮弹簧座马车及各种设备承包自流并工程地址:阿斯顿,格罗斯温纳建筑区“太好了!”主人兴奋地说,“这回凑够三个人了。”“我曾在伯明翰做过调查,”美国人说,“我的代理人把这个刊登在地方报纸上的广告寄给了我。咱们必须抓紧行动把事情办完。我已经给此人写过信,告诉他明天下午四点钟你将到他办公室洽谈。”“你让我去见他?”主人说。
“你看如何,福尔摩斯先生?你不认为这样安排更为妥当一些吗?我是一个身在异乡的美国人,我的故事过于离奇,人家无缘无故怎么会相信我呢?而你是一个交际广泛的英国人,他一定会看重你的。我是十分愿意和你一同前往的,但我明日非常繁忙。你若是在那边遇到什么难题,我会随时听从你的召唤的。”
“可是,我已多年没做如此之远的旅行了。”“放心吧,加里德布先生,我已经为你筹划好了。你十二点动身,下午两点到,当天晚上就可以回来。你不过是和这个人见一面,说明情况,搞一张法律文件以证明存在他这样—个人。”他十分激动地说,“我是不远千里从美国中部来这里的,你只走这么一点路去把事办完还有什么不妥的吗?”
“不错,”福尔摩斯说,“我也有同感。”内森·加里德布先生有点无可奈何,最后他耸耸肩说:“好吧,我只好照做。你给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希望,我自然难以拒绝你的要求。”“那就这么说定了,”福尔摩斯说,“然后尽快把情况告诉我。”
“我一定会,”美国人说,“哎呀,我得走了。内森先生,我明天上午来给你送行。福尔摩斯先生,你和我一同走吗?您还要再待会儿?那么,再见吧,请明天晚上静候佳音。”之后,我注意到福尔摩斯脸上的不解已逝,神色明了了。
“加里德布先生,我想看看你的收藏品,”他说,“我的职业需要各种生僻知识,它们总有一天都会派上用场的。这间屋子真是这类知识的宝库。”我们的主人听后颇为得意,一副大眼镜后面闪着光亮。
“我经常听别人说你很有才智,”他说,“如果你有空,我现在就带你观看一遍。”“太不凑巧了,我现在没空。不过我看这些标本都有标签,也分了类,不用你讲解我也能看明白。如果我明天有时间,我想把它们看上一遍,可以吗?”“当然可以,欢迎光临。明天我虽然不在,但是四点以前桑德尔太太在地下室,她可以放你进来。”“也好,我明天下午刚好有时间,如果你能告诉桑德尔太太那就好办了。对了,你的房产经纪人是谁?”主人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颇感奇怪。
“霍洛韦·斯蒂尔经纪商,在艾奇沃路。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我对房屋建筑也有些考古学的知识,”福尔摩斯笑道,“你这座建筑是安妮女王时期的还是乔治时期的?”“肯定是乔治时期的。”
“是吗?但我觉得还要古老些,不过没关系,这容易搞清楚。好吧,再见,加里德布先生,祝你此行成功。”房产经纪商的工作地点倒是不远,但已下班。我们又回到了贝克街的住处。吃过晚饭福尔摩斯才提起这个话题来。
“这个小问题已经结束了,”他说,“你大概也在头脑中形成答案了吧?”“我还是很糊涂。”
“原因是很清楚了,结局还得等明天再看。你注意到广告的特别吗?”“我看到‘犁’这个字拼错了。”“华生,你也注意到了?你有进步了。那个拼法在英国是错的,但在美国是适用的。排字工人是照排的。还有‘四轮弹簧马车’,那也是美国的东西。与英国相比,美国的自流井更加普遍。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广告,却自称是英国公司。你看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广告是那个美国人自己登的,但目的是什么我却猜不透。”“解释可以是不同的。他是想把这位足不出户的老古董弄到伯明翰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本打算告诉老头儿不要空跑一趟了,但仔细一考虑还是让他去吧,腾出地方比较好。华生,明天一切都会清楚了。”福尔摩斯一大早就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但他脸色阴沉。
“案子比我先前设想的更要严重,华生,”他说道,“我该告诉你实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定是要随我去冒险了。多年相处,我当然了解你的秉性。但是我仍然必须告诉你,此行危险甚大。”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与你共患难了,福尔摩斯。我希望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告诉我,这次到底有什么危险?”“这是个相当棘手的案子。我已经查实了约翰·加里德布律师先生的真实身份。他原来就是‘杀人能手’伊万斯,阴险狡诈,颇有名声。”“我还是不明白。”
“当然,你的专业不须整天去背诵监狱的大事记。我去拜访了警察厅的雷斯德老伙计。那里在技术的严格方面还是堪称一流的,尽管有时缺乏丰富的想像力。我想或许能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找到这位美国朋友的线索。果然,我在罪犯照片馆里找到了他那张幼稚的胖笑脸。‘詹姆斯·温特,又名莫尔克罗夫特,绰号杀人能手伊万斯’,照片上就是这么写的。”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又说,“我从他的档案里摘了一些关键的情况:年龄四十四岁,原籍芝加哥,据悉在美国枪杀过三个人,受某实权人物帮助而逃出监狱。一八九三年抵达伦敦。一八九五年一月在滑铁卢路的一家夜总会内因赌牌枪杀一人,使之致死。事实证明伊万斯在这次争吵中最先动手。死者是罗杰·普莱斯考特,原为芝加哥著名的伪币制造者。伊万斯于一九〇一年获释并一直受警方监视,但无犯罪行为。他系危险人物,常携带武器并易于使用武力。你看,华生,这就是咱们的对手,毫无疑问,他是个危险分子。”
“但他想搞什么鬼把戏?”“会越来越明朗的,我方才见到了房产经纪人,他们说咱们的主顾在那里住了五年,此前房子曾有一年空着。再往前房客是一个无职业者,名字叫沃尔德伦,后来突然消失了,再无消息。房产商清晰记得他的长相,高身材,留着胡须,脸挺黑。而被伊万斯枪杀而死的普莱斯考特据警察局讲也是这个样,可以设想,普莱斯考特原先就住在现在博物馆似的屋子里。你瞧,总算有了一点线索。”
“下一步怎么做?”“马上就会清楚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我。“我带着我那把常用的旧枪。如果这位西部朋友真如他的绰号所言,咱们就必须小心防着他。我给你一小时休息时间,然后咱们就去赖德街。”我们四点整到达内森·加里德布的古怪住处。看屋人桑德尔太太刚要回家,但她十分爽快地就让我们进去了。门上装的是弹簧锁,福尔摩斯答应她走时把门锁好。等桑德尔太太戴着帽子走出去后,这楼下就剩下我们俩人了。福尔摩斯迅速检查了屋子。屋角有一个柜橱与墙之间有一点空隙。我们就躲在空隙里,福尔摩斯小声道出了他的打算。
“他的目的无非是把这位绝顶老实的朋友骗出屋去,只是这个老古董一向深居简出,所以颇不容易。编造的这一整套加里德布谎言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得承认,他编造的谎言相当狡猾,里面有一点鬼把戏,尽管房客的古怪姓氏的确带给他一个出乎意料的开端。”“但他的最终目的何在呢?”“这就是咱们要等待的答案。据我观察与咱们的主顾完全无关。这事和他枪杀的那个人有关系,那人可能曾是他的同谋。我可以肯定的是,这间屋子一定藏有什么罪恶至极的秘密,开始我以为咱们主顾的收藏中可能有他未知的价值连城的东西。但是既然罪犯普莱斯考特曾住过这间房,事情就不能如此简单了。好吧,华生,咱们只有耐心等候静观其变。”
时间飞逝。传来大门,被打开的声响,我们在柜后躲藏得更加小心谨慎。接着有金属钥匙声,那个美国人进来了。他关上门,警觉地四处查看,然后脱掉大衣,胸有成竹地直奔屋子中间的桌子。他迅速把桌子推到一边,掀开地上的一个方地毯,然后拿出一个撬棍,开始狠撬地板。木板滑开了,出现了一个方形的洞。伊万斯这个号称“杀人能手”的美国人点燃一根蜡烛,进了那个地洞。
时机已到。福尔摩斯轻触我的手腕,我们俩人一同蹑手蹑脚溜到洞口。尽管我们动作很轻,但我们脚下的老地板不合作,发出了响声,因为美国人的脑袋突然冒出洞口四处张望。他的恼怒的脸转向我们时,渐渐转为一种自嘲的笑,因为他发现两支手枪指着他的脑袋。
“好,好,”他一面冷静地爬上来一面说,“你们是二比一啊,福尔摩斯先生。我猜最开始你就看穿了我的把戏,把我当猴耍儿。好,我服了,你赢了……”突然,他抽出一支手枪连放了两枪。我感到大腿上一热,仿佛烧红的烙铁贴在肉上一样。接着只听“砰”的一声,福尔摩斯已经用手枪砸中他的脑袋,他倒在了地上,血从脸上流出来,福尔摩斯从他身上搜走手枪,然后伸出结实的胳臂搂住我,扶我坐到椅子上。
“受伤了吗,华生?我的上帝,你可千万别受伤。”我要是得知在这表面冷如冰霜的面孔后面蕴藏着多么深厚的忠诚和友爱,我觉得受一次伤,甚至是多次也是值得的。他那明亮坚强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那坚定的嘴唇有点颤抖。这是惟一的一次,我看见他不仅有伟大的头脑,也有伟大的心灵。我多年不受人关注而忠心如初的服务也就因此而感到满足了。
“没事儿,福尔摩斯。只擦了一点皮。”他用小刀小心谨慎地割开我的裤子。“不错,”他放心地喊了一声,“是表皮受伤。”他把冷峻的脸转向俘虏,那犯人正努力地坐起来。“算你走运。要是你伤害了华生,你休想活着走出这间屋子。你还要说什么?”他没说什么,只是愤怒地瞪着眼睛。福尔摩斯搀扶着我,探头去看那已经揭去了暗盖的小地窖。伊万斯点燃的蜡烛还在洞内燃烧。我们看见一堆生锈的机器,大捆的纸张,一排瓶子,许多小包整齐地码放在里面的一张小方桌上。
“印刷机——造假钞的全套设备。”福尔摩斯说道。“不错。”伊万斯挣扎着坐到椅子上,“这是普莱斯考特的印刷机,他是伦敦最大的伪钞制造者,那些小包是伪钞,一百镑的足有两千张,各地都可使用,毫无破绽,先生们,你们拿走用吧。咱们公平交易,我可以走了吧?”福尔摩斯大笑起来。
“伊万斯先生,这不符合我们办事的原则。你在这个国家无处藏身。是你杀死普莱斯考特的,对不对?”“是的,先生,本来是他先抽枪,但我还是被判了五年徒刑。而我应该得到的不是刑期,而是盘子大小的奖章。普莱斯考特的伪钞与英国银行的钞票几乎完全相同,常人无法辨别,如果我不除掉他,他能使伪钞充斥市场。我是惟一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造伪钞的人。我到这儿来不是更加合情合理吗?我发现这个破烂儿收藏家,这个姓氏古怪的人死也不肯离开此地一步时,我只能设计叫他离去。这也不奇怪吧?我或许应该干掉他,这样倒是明智,容易许多。但我心肠软,除非对方有枪,否则我决不开枪打人。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错儿,我没动这个机器,我也没伤这个老古董。我犯了什么错?”“但你蓄意杀人,”福尔摩斯说,“可是这不是我们的业务,马上会有人接手办理。我们要的主要是你这个善辩的人。华生,挂警察局。他们早已做好准备了。”
这就是有关杀人能手伊万斯以及他编造的三个同姓故事的事实梗概。我们听说那个老古董无法承受梦想幻灭的刺激而精神失常了,后来进了布利斯克顿的疗养院。普莱斯考特印钞设备被查出,这对警察局来说是值得庆贺欢呼的事情,他们虽然知道这套设备的存在,却始终没有发现它。伊万斯确实立了大功,使那些情报人员可以安稳睡觉了,因为这个伪钞机一直困扰着他们。他们几位倒是颇愿替伊万斯申请那个盘子大的奖章的,无奈法庭不同意,于是,这位杀人能手就又回到了他刚被放出来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