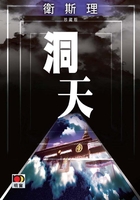1
在文人的笔下,“病”,是一种风情的象征。你可以在书里欣赏楚楚可怜一步三摇弱不禁风我见犹怜,但是你真要生病了,你会后悔得吐血。
首先你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要是你这病生得逢时,比如毛主席那个年代,没说的,单位劳保,全包了。现在?你没钱挂号就得在那儿躺着。
其次你没有精力应付你的爱侣合理的生理要求。“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老古话流传了那么多年,肯定是有道理的。自己造出来的种都会给你看脸色,你就别奢望和你曾经陌路的他或她守你一辈子了。
“要是我被查出来患了绝症,你会怎么做?”
原本躺在床上抽烟的西渡,一下子坐了起来,“不是真的吧?”
“不是,我只是假设。”
西渡又躺了下去,“你不要吓我!这种问题是可以假设的吗?”
“我就是想知道你会怎么做?你告诉我啊!”灵子坚持。
“怎么做?这有什么办法?只好过一天算一天了。”
“那你会不会离开我?”
“不会,我怎么舍得?”西渡摸一摸灵子头发。
“那要是我被救活了,但是永远都不能做爱了,你还会不会在我身边?”
“为什么问那么奇怪的问题?”
“我想知道人和人的想法是不是很不同。”
“会啊。我在你身边是因为我们有感情。你不可以做爱,我就不会往那方面去想。要是我有需要,我会在外面找。可是,你知道如果我快死了,我会怎么做吗?”
“会怎么做?”
“首先,如果我要死了,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自杀,百分之二十是因为贫穷。我不会生绝症。所以如果我快死了,我希望能一个人呆着,我需要安安静静地去死。
所以,人和人的想法是很不同的。现在假设和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又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傻问题。”
蓝色的烟雾在房间里升腾着。
“要是我被查出来患了绝症,你会怎么做?”
灵子问常德。
“我会想尽方法捞钱,一定要把你治好。就算是诈骗也无所谓。”
“坐牢也无所谓吗?”
“我要是坐牢了,谁来照顾你?所以我会很小心的。”
常德信誓旦旦。灵子没有再问下去。
不过自己要是一辈子都不可以和喜欢的人做爱,他能理解,当然好。要是他觉得痛苦,灵子是宁愿牺牲了自己的。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即使只有一天的快乐都是值得的。
反正总会失去他。
可是事情不发生,谁知道当时当地会是什么反应?
记得母亲曾一遍遍细细回忆,说是在医院住得久了,看多了生离死别,也看到了太多人情冷暖。
有推入手术室前1小时,生身母还在床前缠着要交出存折的;
有大病初愈刚出院就拗不过丈夫苦苦哀求,勉强同了房过夫妻生活,没几个月就下身血流不止送进来急救的……
那个女子结婚才1年,说起丈夫来脸上总有止不住的笑。再送进来已是面无人色,输多少血进去就流多少血出来,医生长叹,说是作孽啊,一条人命。
女子死前一晚紧紧抓住丈夫的手不放,流连久久。
3个月后就有消息传来,说她男人已然结婚。
母亲住院整整3年。3年里照光照得头发掉光,往静脉里吊大蒜汁,问相熟医生讨了新生儿胎盘熬着吃。胎盘这东西腥人,少有病友能坚持服用。母亲煮的时候却不放盐不放任何调味品,好几次做不到一口口细咽,只得囫囵吞下……什么法子都试过,什么苦处都吃过,终于死里逃生,熬出生天。
病终于治好。母亲出院那天主治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说是一条命拣回来不容易,何必葬送在一个男人手里?切记切记,不可同房。母亲牢记在心。
对灵子,加了倍关心。身体要从小抓起嘛。
腌的咸鱼咸肉、腊香肠,是从来不进家门的,据说容易生癌。
流行什么健康法子,就带着灵子一块儿操练。醋蛋不是能治百病?一天一个。甩手功可以防癌?每天练习2次,一次15分钟。
母亲独独没重视眼睛。她一家人都是好眼睛,哥哥的视力尤其好,当年差点选去当空军,自己两个眼睛,视力都是1.5。
结果灵子小学3年级就有250度的近视。
冬天渔夫划船,划着划着热了,自己脱一件上衣,跑进船舱就给儿子脱一件。再热,再脱,儿子后来冻死了。这当然只是个笑话,可也看得出来,设身处地四个字,是多么的难。
这样的精心照护,灵子还是一身的病。
一到阴雨天,浑身的关节都不得劲,又酸又软,胳臂,提都提不起来。还会转移,从右肘转到右肩转到左肘再左肩,接下来是右大腿,再痛到左大腿,也就雨过天晴了。
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来偏方,黑蚂蚁可以治关节炎。天气好的时候,就坐在树下抓蚂蚁,用纱布裹了,泡酒给灵子喝。
痛依旧,发展到后来,吸一口气都会痛。
初中的不知哪一天起又开始了头疼。疼起来什么事都做不好,只能睡觉。
开始是一个月发作一次,再后来,发作的间隔时间就越来越短了。
高三最后冲刺时,灵子舍不得休息,头疼倒成了一个可以说服自己休息的理由。
后来知道了“克感敏”。
再疼起来就习惯性拉抽屉数药片。不到三分钟,脑袋轰隆隆倒得比柏林墙还快。疼痛,被更大的药力一下砸晕了。
每次买“克感敏”总是光光的一板一板,大概是因为普通,而且便宜,所以也没有什么说明书可以看。是在什么样的药理作用下呢,竟然会产生幻觉?
吃了药,轻轻的在房间里晃。
午后的阳光把她照得非常苍白。点一支烟,烟很轻盈。头却昏得连自己的脚也感觉不到。挥挥手,烟蓝蓝的在光里走S,扑朔迷离的舞动。
头重脚轻,老是想倒下,就靠了墙站着。
墙有没有耳朵?地有没有耳朵?树木、花朵,有没有耳朵?
2
关于幻觉的自言自语……
“我只看到影子,自己的影子,影子在动,我看不到人了,我的眼中只有这移动的影子,影子不会说话,影子没有嗅觉,所以影子没有了感觉。我喜欢和自己的影子打交道,在黑夜里,在光的后面。”
“我看到无数白色的鸟飞过我的眼前,我的眼睛变得无限的大。所有的白色的鸟全部从一个方向往另一个方向飞去。没有起飞也没有降落。这种无休无止的持续让我痛不欲生,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每个细胞都被这些鸟带去了,带到未知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身体里最后一个细胞会在什么时候被鸟群带走。
青春、鲜血、爱、悲伤,诗意,矫情,在乎与不在乎,统统都去了。
泪水不停地流出来,我能感觉到自己是努力地迫着这些泪水出来,我想我是在解放他们。他们从我的体内来到了表面,并且散发在空气里,就可以不会被鸟群带走。我就留住了这些。
在我的肉体,一个细胞一个细胞被消失后,我的脑子就从高处、很高很高的高处,鸟群带上去的高处,看着床上的,地下的,椅子上的,窗边的,那些泪水。
我看到了我的故事。泪水柔软地裹着它们。我可以放心的去了。”
“是不是下雨了?谁叫我收衣服?反正是湿了,就让它去吧。湿了再干,干了再湿,总有一个状态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只需要等着好了,何必去打断呢?”
“我已经很不自由了,我想让我的灵魂一直在空气里飘荡。它被医院吸收了,就有了来苏水的气味。它被拉面馆吸收了,就有了牛肉汤的浓香。它被摩天大楼吸收了,就有了冰冷冷的玻璃的气味。它们不断飘着荡着,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存在,带着各自的气味。
这样,即使它们有一天再碰上了,它们也分辨不出对方了,我就不是我了,而我又都是我了。我要侵袭这世上所有角角落落,那样所有有味觉的地方都是我,又都不是我,同样,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形状里居住着,只要我高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要选择慢慢衰老或者慢慢死去。
比如病死,浑身插满氧气管子。我的灵魂受不了了会自动溜出去,弃我不顾的溜出去。没关系,它去好了,它不会知道的,是我让它去的。
比如割腕,灵魂随着血珠一滴滴渗出去,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它可以不必受我这个恶魔统治了。我给它自由!
可是我不能接受突然死亡,严重的,如车祸,卧轨自杀,都是很愚蠢的行为。就象一架突然失控摔下的电梯,人被封在里面,出不去。灵魂也一样,它出不去了,左冲右突还是被锁在了这个突然断电的身体里,不久以后,它就和这具毫无意义的肉体一起沉默下来,固定下来,一起死亡。
这是一种浪费,你知道吗?是我不能容忍的浪费。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它自由啊。
可是我贪恋自己的肉体,我贪恋舌头品尝到的美味,所以我还是禁锢着它。
所以我活着,自私的活着。”
“我的头,是不是轻轻搁在你的肩上?只有你才有那么瘦、那么凸起的肩岬骨。
那天夜里,你睡得死沉,烂在那里。
已经不会说梦话的你咬牙切齿抢我的呼吸,想多一口气说话吧,给我听吗?可是我不想把百页窗卷起来,我就在这样的床上和蚊子一起跳舞,我想带它们一起改变蚊香,那样就算你不会动了,风不会动了,别人还是以为我们在动。
人不都这样吗?抢了别人的气流偷偷地在梦里吸,好象很忙的样子。没了气流的人怎么办?好不容易拼死拼活屏足的一口气,没得换,生生把自己憋成一具肿涨的浮尸。
所以我,自得其乐。
本来,具体的人,抽象的气,怎么合二为一?”
“我把这堆积木搭得好漂亮,你有没有看到?可是它怎么会塌下去了呢?分崩离析得瘫塌,一块一块,再精心的对待,又有什么用?”
“白天是关闭的,夜晚也是关闭的,而时间,不再显示。
我看见我脑子的灰质层已经被细细展开了,斑斑驳驳显示出事件的层层叠叠,在细碎的表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我知道他是男人是因为他没有头发,也没有戴着妩媚的宽边帽,他的头下是一根笔直的支柱,没有我熟悉的肌肉,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一滴泪滴在了支柱上,在斑斑驳驳曲里拐弯的纹路里蜿蜒进展,我熟悉的曲线渐渐化了出来。是你。”
“不对不对,我好象听见滴水的声音,是从我身上听到的?快帮我拧紧啊,我不想这样漏水,漏出一盆水一桶水一缸水一河水,你觉得我这样看起来不是在消耗?因为水表盘让我看起来静止?然后呢?你用它干什么?刷煤球?于是我在不为人知己知天知地知的一微米一微米的流在一个煤球上?有多少只煤球就这样给洗没了?你知道就快点告诉我,你快说啊!”
3
吃下一板药片的那一次是西渡走的那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习惯一个人。
只是不能习惯。
一个人,很冷。
睡觉,就可以钻到暖和的被窝里了。
可是,她睡不着。
因为脑子不停的活动着。
吃下十二粒“克感敏”后,身子忍不住晃了晃,一屁股跌在床上。不久眼皮就沉重落下,关闭了想象。
脑子失去活动,于是肉身也动弹不得。
没有“克感敏”,这日子怎么熬?吃完一把药后就可以静静躺在床上等睡着了。多么好。
脑袋关上后,至少可以有片刻安宁了。
除了吃药,没别的方法。
从一粒到2粒再到后来的半板一板,从缓解她脑袋里的疼痛到麻木她的心灵,“克感敏”,成了她的需要。
脸上,漠无表情。眼睛,只能呆呆盯着一点。脑子,在千里之外唱着独角戏。
不用去想该用怎样的笑,怎样的声音,怎样的表情去配合别人。
一个人的时候,不觉得痛。
只是那时的自己,是真实的吗?
很多很多年了,一只无人关注的空瓶子,被众多众多孩子的手接住,抛过来又抛过去。(只有在吃完药后灵子才特别随波逐流,非常飘泊地经过,不去在乎,在乎快乐或是伤害)可是没有一个孩子敢向瓶子里张望,他们的邪恶用无邪的年龄掩盖。但他们自己知道,瓶子里有属于他们的迷离故事,不敢看。(就象很多人不敢盯她吃了药后呆瞪瞪的双眼)。只要看一眼,他们就会深深一脚踩空,永不能爬出。她曾寄希望于她爱的人,他们逃离。西渡是第一个。他在夜晚聪明地在她眼睛四周游走,并且找到了不被她吸入的机会。只留下一个暧昧的影子在清晨。
“光看你的掌纹就知道了,你呀,想得太多,所以老是头疼脑热的。”
小音一边看她的右手,一边摇头。“因为你太敏感了,老天不想让你受那么多罪,所以让你头疼,让你依赖‘克感敏’。因为你只有那个时候是钝感的。”
细细看自己的右手掌纹,果然是密密麻麻的。要是每一条纹路都是一个故事,不知道要应多少?
生命线弯弯曲曲的前进,走到半途,一个斜劈断开。这一劫,是什么时候的事?自己可能过去么?统统不知道。
人握着自己的命茫茫然的走着,不知何处有沟何处有坎,何处是归程?
不是不可笑的。
小时侯母亲就常抱了灵子在院子里坐,说,灵子乖,咱们灵子是属马的,又是在春天出生,春天多好啊,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不愁没草吃。
又说乖女一头的卷发,是大吉大利头,前环金、后环银,不愁没钱花。
灵子对着镜子扯扯乱蓬蓬一头黑发,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卷得金银归,赚个盆满钵满的?
看来是没什么指望了,苦笑笑,突然想起今天小音要为她介绍一份兼职的活儿,急忙打开了淋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