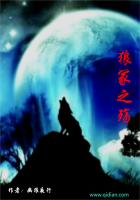“她错了,”洛宾说,“我们若使没有密谈过,我们现在也不至于这样隔膜了。我向她说我万分爱她,但是我没有法子使那小姑娘相信我是诚意的。”“我不晓得你能够有什么法子使她相信,”他的母亲说,“凡是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不能够相信你是诚心诚意的,对着一个你十分晓得境况极坏的可怜姑娘说一套这类的话。”
“但是请你听我说,儿子,”她继续说,“你既然告诉我没有法子使她相信你,我要问你我们怎样相信你才好?因为你说话时总是东拉西扯,跑一阵野马,谁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诚意的还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从你自己的口里证明出那女孩对我说的是实话,我希望你也说出实话来,正经地对我讲出你的心曲,使我可以得到把握,知道里头到底有什么没有?你是认真的,还是闹着好玩的?你真是被她迷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坦白地说出,叫我们好放心。”
“皇天在上,太太,”洛宾说,“再扭扭捏捏地不说,或者多扯些谎都是没有用了。我是诚意的,同一个快去受绞刑的人一样地诚意。若使柏蒂姑娘肯说她爱我,愿意嫁我,我情愿明天饿着肚子把她娶来,我可以不吃早餐,我急着要说‘属于我的,永久属于我的’。”
“好吧,”母亲说,“那么我丢了个儿子。”她说时音调非常凄酸,的确是很担心。
“我希望我不算做失丢了,太太,”洛宾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算失丢了,当有个好妻子照顾着他时候。”
“但是,儿子,”老太太说,“她是同叫花子同样的穷。”“但是,太太,”洛宾说,“因此她更值得我们的周济,我把她娶来,免得教区要出钱养她,她同我可以一起求乞。”“拿这些事来开玩笑是不对的。”母亲说。“我不是开玩笑,太太,”洛宾说,“我们要一起来求乞你的原谅,太太,你的祝福,太太,同我父亲的祝福。”“这全是傻话,儿子,”母亲说,“若使你是诚意的,你可说是一生休矣。”“我恐怕不会。”他说,“我真怕她不肯要我,经过我姊姊这阵恫喝同怒噪,我相信我现在怎样劝她嫁我也是不能够成功的。”“这真是说得好听,可是她还不至于傻到那样地步。柏蒂姑娘并不是蠢货,”他的第二个姊姊说,“你心里想她会比别人特别高明,敢对求婚人说个‘不’字吗?”
“不错,爱说笑话的姑娘,”洛宾说,“柏蒂姑娘不是蠢货;但是柏蒂姑娘或者已经同别人订婚了那又怎么样呢?”
“不,”大姊说,“这我们可不知道了。但是,和她订了婚的人会是谁呢?她从来没有走出家门过;那么一定在你们两个里面。”
“我没有什么话说,”洛宾说,“我已经受过你们的审问了;这里还有我这个哥哥。若使总是我们两人中间的一个,你们去盘诘他吧。”
这句话打到他哥哥的心坎,他以为洛宾发现了什么。他面上装作没有事样子。“请你,”他说,“别把你的事套在我头上来,我告诉你,对于这班姑娘我是一向没有关系的,我对于柏蒂姑娘没有什么可说,对于教区里一切的柏蒂姑娘们我都是无话可说的。”说了这几句话,他站起,掉过头来匆匆地走开了。
“不,”大姊说,“我敢担保我这位兄弟,他比你懂得多了。”他们的谈论如是就结束了,但是把大哥弄得很迷惑。他断定他的弟弟已经知道了,渐渐疑到我有走漏了风声,但是无论怎样想法子,总找不到机会和我密谈。最后他真是焦急极了,有些拼命样子,下个决心要来我房间看我,不管结果会怎么样。心中蓄了这个意思,有一天午餐后,他注意他的大妹的行动,着她是上楼去的,他故意跟着她后面跑。“哦,妹妹,”他说,“那位病了的姑娘躺在那里?谁也不能看她吗?”“我想你可以去看她,”她妹妹说,“可是先让我进去,等下再告诉你。”她就先跑到门口,关照我一声,立刻叫他上来。“哥哥,”她说,“若使你想来,现在可以来。”他走进来,还是带着开玩笑口吻。他走到门口时候说:“那位患相思病的病人躺在那里?你好吗,柏蒂姑娘?”我想从椅里站起,但是太软弱了,要费了好久时间才鼓上劲来,他看到这个情形,他的妹妹也瞧见,她说:“别要勉强站起!我哥哥不拘这些礼节,并且你现在是这么软弱。”“不,不,柏蒂姑娘,请坐着不动吧。”他说,他自己就坐在我对面的椅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他对他的妹妹和我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说这件事,说那件事,无非是替他妹妹解闷,有时又提到爱情的事情,自然是对我而发的。“可怜的柏蒂姑娘,”他说,“堕到情海里的确苦恼得很,你现在已经是很憔悴了。”最后我说出这几句话:“看你这么快活样子,我心里很高兴,先生,但是我想医生也太无聊了,找不出事干,拿病人来开心。若使我患的真真不是别的病,我很知道通常一句俗语,绝不会让他来诊察。”“什么俗语?”他说,“嗬!我记起来了。‘病人害的是相思,医生就同驴子一样的傻了’。”
“是不是这句俗语,柏蒂姑娘?”我轻轻一笑,不说什么。“不,”他说,“我想就医治的结果看来,恐怕真是爱情作祟,你看医生对你仿佛没有多大功效;你身体复原得很慢,他都这样说。我恐怕这里头有些巧妙,柏蒂姑娘;我怀疑你患了不治之症,那就是相思病。”我又轻轻一笑,说道:“不,真的,先生,这不是我的真病。”
我们谈了许多这类的话,有时说些同样不相干的话。他请我唱一曲调子给他们听,我听着又是微微一笑,说我的唱歌日子已经过去了。最后他问我要不要吹笛子给我听,他妹妹说她相信这会害我,我的神经恐怕受不了。我鞠一躬说:“不,这不会对我有害。”“请你,小姐,”我说,“别阻止他,我非常爱听笛子声音”。他妹妹就说,“好吧,哥哥,你吹罢。”他拿出他私室的钥匙,“好妹妹,”他说,“我懒得很,请你到我私室,把我笛子拿来,那是在某一抽屉里。”他故意说出一个,他知道笛子绝不会放在那里的地方,这样子他妹妹会找好半天。
她一走开,他就把他弟弟所说关于我的话全告诉我,以及他弟弟怎样推到他身上,他是多么焦心,所以要设法同我谈一下。我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对他弟弟或者任何人谈到我们的私情。我告诉他我所处的是多么可怕的危急的地位。我说因为我是诚挚地爱着他,而他现在又叫我忘却了我的爱情,把我的心硬移到别人身上,我才病倒床上;我有一千回希望自己会死,真不愿意复原,再像从前一样,来和许多困难的环境奋斗,我这种对于生命的退缩态度也是我痊愈得这么慢的原因。我还说我预料到我病好时候,立刻要离开这家庭,至于嫁给他的弟弟这个办法,我一想起免不了有无限的憎恶,因为我同他既然有了这一段恋史,他尽可放心,我一定不会和他弟弟见面谈这件事情,若使他将他的约言、誓语、赌咒的话全推翻了,那只能归咎于他的没有良心,不顾人格,但是他总不能说我——从前他讲了许多话要我相信我是他的妻子,我也让他对我有各种自由好像真是他的妻子一样——对他没有保持有妻子所应当有的忠贞,不管他是怎样待我。
他正要详细回答,才说他心里有些难过,因为他劝我的话一句也没有效力,还要往下讲去,却听到他妹妹的声音,我也听到,但是我勉强说出几个字来回答他,我说他总不能够劝服我,叫我爱一个人,又嫁给他的弟弟。他摇一下头,说道:“那么,我毁了。”指他自己;他妹妹走进来,告诉他她找不到那笛子。他用快乐的口气说:“可见懒惰是不行的。”他起来自己去找,可是回来也没有带有笛子,并不是他找不着,是因为他心里有点不安,不想吹调子,而且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所要的是同我谈话的机会,这个他已经得到,虽然谈的结果不能够叫他很满意。
我倒觉得很满意,能够这样自由地把心里的话告诉他,并且说得这么坦白,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虽然不能够照我所希望的那样子发生效力,那是使他更加喜欢我,但是这诉说以后,他失丢了离弃我的可能,除非是他简直不讲人格,将上等人的信用全丢开不顾,他从前不是常常用他的人格同信用担保他永不会弃绝我,一得到财产就要娶我做他的正室。
没有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能在屋子里走动,渐渐地复原了;但是我仍然是愁闷、静默、无聊样子,和人们不大接触,使全家人都很惊慌,除开知道这里头道理的他。但是有了好久时候他不理睬这种情形,我也像他一样退缩着不愿交谈,对他总是很尊敬的,但是没有向他讲过一句含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话,这样子相持继续了十六七个礼拜,我天天都在那里预期被他们撵出,因为她们是很不高兴我,虽然我并没有什么罪过。我同样地天天都在那里预期他不会再向我说什么话了,不管他从前怎地严肃地立下誓言,说了许多殷勤的话,我想我总可说是毁了,被他所弃绝了。最后我自己向那家人提出我的迁居。有一天我很郑重地同老太太谈到我现在的情况,以及我病后的精神愁闷,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这些话,老太太说:“我恐怕,柏蒂,我从前告诉你关于我儿子的话使你的心境不宁,你的愁闷或者也是因为他的缘故,请你说给我听你们两个人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若使说出来对你没有什么不便。至于洛宾,每回我询问他时候,他总是开玩笑地胡说一阵。”“太太,”我说,“现在的情势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我要把这事情的始末倾怀相告,也不去顾到对我会有什么结果了。洛宾先生有好几次向我求婚,这真是出乎我意料,因为我的境况是那么穷苦,但是我一向是拒绝他的,或者说的话有些太过了,是我所不该说的,因为我对你家里的每个人都应当很尊敬才是,可是,太太,”我说,“我绝不能够忘记了你同全家人待我的恩惠,会跑去答应一件事情,心里却明知这件事是对你们不起的,我就将这些话做我拒绝他的理由,我坚决地对他说除非是我能够得你老人家同他父亲的同意,我绝不肯存这个心事,因为我对于你们的隆情厚谊的感激是超乎一切利害计较以上的。”“这是真的吗,柏蒂姑娘?”老太太说,“那么,你是很对得住我们的,我们却待你太坏了,我们一向总把你看做是在那里勾引我的儿子,我还想请你移居,怕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还没有跟你提起,因为我想你还没有全好,我怕会使你太伤心了,又要病倒,我们对你还是很看重的,虽然不肯因为你而毁了儿子的前途,但是若使事情的真相是像你所说的,我们的确是太冤枉你,太难为你了。”
“至于我所说的是真话,太太,”我说,“我请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儿子自己,若使他是凭良心讲话,不想冤枉我,那么他所说的不会和我刚才所讲的有什么相差。”
老太太立刻跑去找她的女儿,将我向她说的话全告诉给她们听,她们都很惊奇,这是你可以猜得到的,我早知她们一定会很惊异。一个说她万不会想到;一个说洛宾是个蠢货,还有第三个说她是一个字也不能相信的,敢担保洛宾所说的一定会大不相同。但是这位老太太决意要在我有机会通知她的儿子刚才谈话的经过以前,把这事追查到底,所以决意立即去找她的儿子来谈话,她特意派仆人去叫他回来,他是为着自己一点小事情到城里一个律师家里,一听到她的吩咐,即刻回来。
他回家时候,她们还同坐在一间房里,“坐下来,”老太太说,“我有几句话非得同你谈一下不可。”“无比欢迎,太太。”洛宾说,愉快得很的样子。“我希望你是同我商量如何替我娶个好妻子,因为对于终身大事我真是不知道怎样办好。”“怎么会没有办法呢?”他母亲说,“你不是说立下了主意要娶柏蒂姑娘吧?”“不错,太太,”洛宾说,“但是有一个人阻止我们的婚礼。”“阻止婚礼!”他母亲说,“是谁?”“就是柏蒂姑娘本身。”洛宾说。“什么?”母亲说,“那么,你征求过她的意见吗?”“是的,太太,”洛宾说,“从她得病后,我正式向她求婚过五次,都碰了钉子!这丫头固执极了,她不肯答应,什么条件都不行,除非是我实际不能办到的条件。”“讲明白些,”母亲说,“我真是莫名其妙,不懂得你的意思。我希望你这回不是开玩笑的。”
“怎么,太太?”他说,“我的情形是很明白的,用不着解释,她不要我,她说。这不是很明白的吗?我想是很明白的,并且太刺耳了。”“哦,但是,”母亲说,“你讲你实际上不能答应的条件,她要的是什么条件——是不是一份授与她的产业?她所得的归她名下的产业应当按着她的妆奁来定,但是她带有什么妆奁给你?”“不,说到财产,”洛宾说,“她的美貌就是一份好妆奁,这点我是很满意的,可是我却够不上她所提的条件,她又是那么坚决,除非我践行了她提的条件,她是不肯允诺的。”他的姊妹就插嘴进去。“太太,”他的妹妹说,“同他是没有法子正正经经地谈一件事的。什么话他也不肯好好地回答,你还是让他一个人去吧,不对他再谈这些事,若使你以为这里面有些把戏,你是知道怎地打发她使他看不见她。”洛宾看到他妹妹这样苛刻,心里有些生气,但是他也说出尖酸话来和她相抵,还说得很圆转。“天下有二种人,太太,”他向他的母亲说,“是没有法子同他辩论的,那是,聪明人同傻子,这的确有些太苦的,我要同时对付这两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