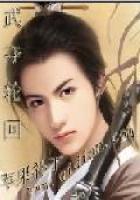五尺道开通时代考
段渝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从蜀之成都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为“西南夷道”。西南夷道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西道是“灵关道”,或称为“零关道”、“牦牛道”,由蜀之成都通往云南;中道为“五尺道”,由蜀之成都通往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东道是“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南夷道”,由蜀之成都经贵州通往两广已至南海。西线灵关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通,在商周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它都一直发挥着中国西部民族与文化南来北往交流互动的通道作用,并充当着中国西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交通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对于中线五尺道的开通时代,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战国末叶秦时开凿,很少异议。但是,历来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五尺道开通年代的理解却难以经得起推敲,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五尺道的开通不始于秦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五尺道是秦始皇时开通的,也有学者认为是秦汉时开通的。笔者曾在1993年出版的《四川通史》第1册已简略说明,蜀、滇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官道,但早在殷末,蜀王杜宇即由此道从朱提(今云南昭通)北上至蜀。至春秋时代,蜀王开明氏“雄长僚、僰”,进一步开通了成都平原与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的交通。以后,“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对殷周至战国时代已经存在的这条道路予以进一步整修。这就意味着五尺道并不开凿于秦,秦仅是对五尺道加以重修和整建。葛剑雄教授在《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亦认为五尺道的开凿不始于秦,该文认为秦法既然是“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却公然会修建“五尺道”,而严峻的秦法是不可能容忍“五尺”之制存在的,从而否定五尺道始修造于秦。实际上,《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句所说的“略通”,并不是“开通”或“始通”的意思,而是“略取通行”的意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索隐》引张揖曰:“蒙,故鄱阳令,今为郎中,使行略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师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可见,“略通”并非“开通”之义。至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事为“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则有着整修和整饬的含义,这与《史记》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略取和整修往往是前后相接、一以贯通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但《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却是:“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对于“蜀故徼”,《史记》记为“開”,《汉书》记为“関”,究竟是开还是关呢?二者必有一误。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五尺道的开通时代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蜀故徼”,是蜀在经由五尺道通往西南夷诸族的途中所设置的关隘。这里的“開蜀故徼”,“開”为开通的意思。其实这个“開”字,实为“関”字之误。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段文字所说的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即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说“邛、笮、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既然秦在这些地方开通了郡县,置有守吏,那么秦王朝时这些地方之间的关隘必然就是开通而不是关闭的。至秦灭汉兴,这些地方的族群“皆弃此国”,即拒绝汉王朝的统治,那么这时“诸此国”与汉王朝之蜀郡间的通道就只可能是关闭而不是开通的。而司马相如所说:“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此句“今诚复通”十分重要,它确切说明,在邛、笮、冉等请求内附之前,汉王朝与西南夷的交通关隘是关闭而不是开通的。正是因为邛、笮、冉等“诸此国”关闭了蜀与西南夷地区之间的通道,所以才会出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到南中做买卖的现象,以及西南夷诸族阻碍汉使十余批出使大月氏那样的结果。假若是“开蜀故徼”,那么巴蜀民就不会“窃出”西南夷地区,而汉武帝为打通与大月氏联系所派遣的十余批汉王朝使臣,也就不可能在西南夷道上遭遇到“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那种尴尬局面,受到西南夷的重重阻碍。“開”、“関”二字,古文形近,今本《史记·西南夷列传》所用的“開”字,显然是在传抄过程中因形近而导致的讹误,致使谬种流传,我们自然不能根据错讹的字义来领会史书所载历史。
据上所论,蜀与西南夷之间早有商道可通,这就是“蜀故徼”。这个“蜀故徼”,在秦王朝“略通五尺道”以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二、古蜀人的尚五观念与五尺道的开通时代
五尺道之所以称为“五尺”,应与古蜀王国“数以五为纪”有关。史书虽未明言蜀人数以五为纪,但是蜀人崇尚五这个数字,从王室祭祀制度、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信仰,都以五计数,却是斑斑可见,史不绝书。并且,古蜀的文物制度多以五为纪的情况,也为历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一致性,十分明确反映了古蜀这一特有的制度。
古代蜀人的尚五宗教观念形成甚早,从目前的资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以前古蜀文明起源时代,今成都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中部大型房屋内的五座卵石台基,由此连续贯彻到商周、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其遗风至汉魏之际犹可观瞻。在尚五观念的支配下,古蜀人发展出了一系列“数以五为纪”的文化丛:以五为朝代数的王朝盛衰史,以五为庙制的宗庙祭祀制度,以五为王制的青铜器组合,以五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以五计数的其他若干事物,都是以尚五观念为核心凝成的文化特质。由此可见,尚五观念已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规定并支配着蜀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例如,青铜器中的罍、无胡三角形援戈、柳叶形剑等,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表现出古蜀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自有其演进规律;然而青铜器的组合却以五为纪,而为巨制,为王制(从新都蜀王墓中可充分证实此点),并且同样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存而不改,则表明古蜀青铜文化组合方式是在蜀人尚五观念支配下产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它的发展受到了尚五观念的严重制约。又如,五丁制度作为古蜀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其具体由来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组织形式同样是在尚五观念支配下发展出来的社会行为方式。至于其他以五为纪的事物,也莫不受到尚五观念的支配和制约。
公元前316年蜀亡于秦以后,虽然古蜀文明物质文化形式的发展受到遏制,社会组织形式完全被秦改造,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但由于尚五观念极深地镌刻在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当中,具有极广大的社会功能和极强劲的历史惯性,所以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其统治秩序,不得不利用尚五观念来作为工具,因势利导,以期引起广大蜀人的共鸣,李冰之所以“以五石牛以压水精”,正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宗教观念,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他就牢牢把握住了治蜀的精神武器,终于成功地修建了都江堰,创造出历史的奇迹。秦时“略通五尺道”,也是出于同样的情况,因而成功地略通了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通为郡县”,“颇置吏焉”。这些史例,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尚五观念在古代蜀人和先秦蜀文化中所占有的核心凝聚力地位。
五尺道的命名同样也是出于蜀人数以五为纪的制度。《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古蜀“五丁力士”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国家公共工程的修建,而凿山开道、开辟和维修交通路线又是五丁力士的最重要功能之一。蜀人数以五为纪,所辟道路亦以五计数,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偶然的关系。而且,由五丁力士所开的道路,称为“五尺道”,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此看来,五尺道始辟于蜀人而非秦人,是信而有征的。这也说明,五尺道是古蜀国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
五尺道的开通应始于商周时代。史籍关于杜宇入蜀的记载,为这条交通线路开辟的年代在商代晚期提供了有力证据。史称杜宇为朱提人,朱提为今云南昭通,由云南昭通北上,经大关、盐津至四川宜宾,正是五尺道所经由的线路所在。杜宇由云南昭通入蜀,只可能走这条线路,再从今四川宜宾沿岷江河谷北上达于蜀地。杜宇为云南之濮,杜宇入蜀当是以他为首的整支族群入蜀,否则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在蜀地推翻古蜀王鱼凫氏的统治,“自立为蜀王”,建立起杜宇王朝。可见,杜宇氏族从昭通入蜀,表明五尺道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通的事实。据《逸周书·王会篇》所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提到殷畿的正南诸族中有“百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专贡矮犬,当即云南之濮。西周初年正南之濮进入中原参加周成王的成周之会,其间通道必然是经由灵关道或五尺道至蜀,再出蜀之金牛道,经褒斜道转至陕南而达中原。
考古学上,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前后,威宁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的玉器,均说明古蜀文明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传播时代,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既有文明的传播,必有传播的通途。而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恰好是在五尺道的主线路上。这就意味着,五尺道的开通年代,至少是它的初通年代,一定不会晚于商周时期,否则对于昭通和威宁地区在那一时期出现古蜀文明因素的现象,将无法给以恰当的解释。
那么,为什么秦人仅将从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之间的交通线路称为五尺道,而从蜀地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另一条交通线灵关道却不称为五尺道呢?这与秦人重修五尺道并沿袭其旧称有关。五尺道原为蜀王国的官道,属于古蜀王国的国家工程,故以五尺为名。从史籍可见,秦人从蜀至西南夷地区,分为两路南行,东路沿五尺道,西路沿旄牛道(灵关道)。这两条交通线均为蜀时故道。东路的五尺道可由黔西北通往黔中,历来为秦王朝所特别重视,同时为笼络蜀人,利用蜀人维修整治,故沿袭蜀时旧名。而秦沿西路旄牛道南下,其政治统治势力仅达越嶲而止,而且这条道路没有经过秦人修整,故其旧名没有为秦人所沿袭下来。古蜀至南中的东西两道——东道“五尺道”和西道“邛、笮道(即旄牛道)”,均为古蜀国时期的官道。五尺道之所以称为“五尺”,而不是为秦王朝“一断于法”之下“数以六为纪”的“六尺道”,原因就在于“五尺”是沿袭古蜀王国的旧制,而不是由秦重新命名。五尺道为蜀国五丁力士所开凿,故命之曰五尺,而古蜀“数以五为纪”的制度均以五为纪,道路亦不例外,所以由五丁力士所开之道,自然命曰五尺道。五丁力士专为蜀王国负担国家工程,开山凿道即是其重要义务之一。由五丁力士所开五尺道,当然就是蜀之官道。旄牛道的情况同样如此,并且因为这条线路未经秦人“略通”(整治),故其名未被秦人沿袭下来而已。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秦人在蜀地南部分东西两路南下,一路沿五尺道,在五尺道上“颇置吏焉”,一路沿旄牛道,在邛、笮“通为郡县”,两道的“略通”年代均在秦灭前十余年,远远晚于古蜀通西南夷的时代。而且,秦人所略通的这两道都是沿着旧时古蜀王国通西南夷的道路而下,并没有新辟道路。这两道都在秦灭后,立即恢复了旧日的古蜀关隘,而蜀商要入南中必须偷越五尺道,《史记》明言有“蜀故徼”,旄牛道虽未明言,但从《史记》所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旄牛”,可知旄牛道同样设有“蜀故徼”。由此可见,在这两道上,古蜀时均设置了关卡,收取关税,此即相当于《孟子》所说中原地区的“关市之征”。既然如此,那就表明这两条道路都是古蜀的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