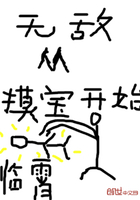在派出所的大门口看见了芳芳。我并不吃惊,因为这么快放了我,就知道有人出钱替我作了保。在这座城市里,除了芳芳,还有谁会这么做?因为只有她对我死心塌地。我对她笑了笑,她也对我笑了笑。她说:“出来了,就好!”这时我发觉今晚的月光特别皎洁,即使在路灯下,也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说:“谢谢!”她邪么地一笑,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该谢你那个老朋友阿辉。”我不解:“他?”芳芳说:“是呀,是他打的招呼。”芳芳挽起我的胳膊,把保释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原来,芳芳晚上到我住的地方去找我,房东便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那种地方她进去过,所以并不着急。她很平静地在我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本通讯录,以前她听我说起过阿辉这么个当官的人,看到了张辉映这个名字就知道准是他。于是给阿辉打了电话,请他帮忙,阿辉先还有点犹豫。芳芳便说上次的事就是她出面做的,阿辉这才答应了。他究竟找了什么人,芳芳也不知道。三个小时以后,阿辉的电话过来了,说是招呼都打过了,只要到派出所交一万块钱,人今晚就可以出来。最后阿辉说,以后别再拿这臭事烦他。芳芳说完后,洋洋自得地耸耸肩说:“你看我还行吧?”我没有搭腔,而在思考阿辉的话。芳芳摇着我的身子说:“我的话你在听吗?”我说:“以后,真的不能再拿这种事烦那个朋友了,他还要向上爬的。”芳芳噘起嘴不屑一顾地说:“什么烦不烦的?为了他向上爬,我们帮他都做了什么臭事呀。他欠我们的!”听得出芳芳心里很委屈,我不再反驳,只是说肚子很饿,提议到润河街吃宵夜。
我们在独臂老太的大排档坐了下来,点了好多菜,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芳芳问:“你不是要保持体形的吗?干吗吃这么多?”我说:“今天不吃,怕以后吃不上了。”芳芳问:“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吃完了就回去拿行李,拿了行李就奔火车站。”芳芳说:“你要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只要能离开这里,到哪儿都行!哪班火车最早开,就上哪班。反正呀,越快越好!”芳芳不再言语,划亮火柴,点上一支烟,深吸了几口之后,便哭了。豆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滑落,在面颊上流淌。看着这一切,我有点于心不忍,凭良心讲,我欠她很多,但是我必须离开这里,因为这座有着两个灵魂的城市于我而言,已犹如一座坟墓,要是还住在这里,非得憋死我,我要寻找一个适合我的地方。我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便沉默着。芳芳擦干眼泪,又划亮一根火柴,自言自语:“火柴的味道真好闻。”她向我投以一丝邪么的笑,说:“你去吧,我不会再拦你!姗姐临走时给了我警告,让我不要拴着你,拴住人,拴不住心。”我很吃惊:“姗姐走的时候通知了你?”芳芳说:“是呀。难道不可以吗?”女人的做法总是很奇怪的,这就是女人。芳芳说:“吃完了,我帮你去收拾行李。不过,我要你告诉我,纹身上的芳芳到底是谁?”我说:“真的谁也不是。那个替我纹身的游医对我说,她是我命里注定的女人。”我看见芳芳的眼里闪过一丝希冀的光,但一闪就熄灭了。她笑了笑:“这么玄乎!我听人家说,爱情就是一种气味,你闻到了对方的那种气味,就有了爱情,如果你闻不到,就是一辈子在一起,也不会有爱情。有一首歌叫《味道》,很好听的!”芳芳轻轻地哼唱起来,鱼尾纹已很明显地刻在她的眼角。
我们没有打的回我住的地方,而是走着回去的。不知道为什么,却不约而同地绕道去了市中心的广场。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夜色中的广场其实是非常空旷和凄凉的。突然间,心里涌上了一股离别的伤感。我说:“真要离开这里了,反而有点舍不得了。”芳芳看了看我,向干喷泉后面的舞台奔了过去。她奔跑的身姿非常轻盈,像一枚羽毛在飘。她飘呀飘呀,突然转过脸来冲着我笑,但我看到的却是燕雁的脸,苍白、瘦削、无助。我赶紧闭上眼睛,用力晃了晃头,再睁开眼时,她已飘到了舞台上,开始舞蹈起来。思维一下又回到了现实之中,那是芳芳不是燕雁。芳芳的舞姿散发着强烈的挑逗性,传递着荷尔蒙的气息。以前她在一家夜总会跳脱衣舞时,就是跳的这种舞。芳芳的笑声透过浓浓的夜色传递进我的耳朵,我分明感到了自己的心猛地疼了一下,这时那句话又飞进我的脑海--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我冲芳芳吼:“下来,别跳了!”芳芳骤然间停下,呆若木鸡地望着我,月光投射在她身上,仿佛给她披上了一件白纱,很迷茫。她跳下舞台,走近我,轻声问:“你怎么了?”我摇摇头,说:“走吧!”
夜风中传来一种熟悉的味道,那是这座城市的味道,其实就是长江和润河混合的气味。我嗅着它们,想到了大海,那是长江和润河的终点。我明白了,下面我要去的地方就是有海的城市。突然间我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又觉得什么话也没有,就这样看着路灯下变幻着的影子无言地走着,这座城市的气味萦绕着我,那份离别的伤感如这浓重的夜色充溢在我的心间。曾经是那么憎恨这座城市,因为它充满了谎言和冷漠,可是,却心甘情愿地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些年。现在我明白,我就是为了闻这里的气味,长江和润河混合的气味,它的名字叫“毒”。其实,在这座城市里,我早已变成了一个毒瘾很深的瘾君子,难以自拔了。在路过一排棕榈时,“毒”的气味里冷不丁蹦出了一种全新的气息,很快就淹没了这座城市的气味,同时也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它们很陌生,但很纯洁。我问芳芳:“你听到了什么没有?”芳芳漠然地摇摇头。我说:“不对,周围一定有东西,一定有!”我像被什么控制着,开始在四周又嗅又闻,芳芳在身后叫我,我也不听,只是一个劲地寻找,却不知道要寻找什么。那声音那气息越来越强烈了,激起了我心中压抑已久的一种情感,诱惑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近那个未知的东西。终于在一片小黄杨底下,我看见了一样东西,月光把它照得很清晰,我叫了出来:“天,一个孩子!”我冲上前去抱起他(她),只见他(她)在瑟瑟地发抖。芳芳走过来,也惊叫了出来,赶紧脱下身上的大衣盖在这婴儿的身上。她说:“天下还有这种父母?真该死!”我说:“走,上医院!”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向医院直奔过去。坐在飞驰的车里,芳芳用最恶毒的话诅咒起遗弃这孩子的父母来,而我在她的诅咒声中看见了自己的养父,他在对我说话,他在对我笑,他在对我哭;我还看见小宇的父亲,看见他寻找儿子时孤独而坚强的背影,于是我感觉到了爱意,那爱里面浸淫着艰辛、苦难、泪水,还有希冀,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知道,那就是父爱。温暖中,我低头看了看怀抱中的婴儿,他(她)的脸上是痛苦的,是混沌的,更是纯洁的,我把他(她)紧紧地按在了心窝上。车窗外的城市在父爱里和孩子的纯洁中,如夜色一样温柔。那种叫“毒”的气味变得模糊了,渐渐地闻不到了。
婴儿是个男孩,脐带是才剪断的。医生作了检查之后,说还有救。我和芳芳都舒了口气。隔着婴儿室的窗户,我看见他很安静地睡着,像个刚刚下凡到人间的小天使,让人生出无限的怜爱来。芳芳走过来,问:“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做他的父亲。”芳芳一惊:“什么?你在说什么?”我看着惊得张大了嘴的芳芳说:“我曾想拯救一个人,一个孩子,但是我失败了。这一回,我得成功。”芳芳蹿到我面前,像打量陌生人一样打量着我,然后摸摸我的额头,说:“你是不是脑子发热?”我说:“不,现在我很清醒。我就是他的父亲,他就是我的儿子!”芳芳摇着我的身体,说:“你想过没有,被遗弃的都是有残疾的,很难养的。”我说:“但他没有残疾。”芳芳把我拉到一边,着急地说:“就算四肢没有残疾,没准儿有什么心脏病,还有弱智……”我打断她:“就算有,也没有关系。”芳芳不知所措地看看我,捶胸顿足地说:“天知道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我问你,以后你靠什么养活他?”我说:“做苦力,扫马路,拣垃圾……什么都行。有我一口,就有他一口。我还要让他受好的教育,让他学钢琴学围棋,读很多世界名著,听很多世界名曲。对了,还有带着他锻炼身体,让他拥有一身腱子肌,谁都欺负不了他。”芳芳怔怔地看着我,说:“不懂,一点也不懂你。”我说:“会懂的,慢慢会懂的,一定会懂的。”我向婴儿室望去,蓦地我看见了养父的身影,他抱着襁褓中的我,哼着京曲,走在拥挤的人群之中,脸上带着笑。我的眼睛突然一热,便有一种热辣的东西冲出眼眶。芳芳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你在哭!你说你从来不会哭的,可现在真的在流泪!”我摸了摸流淌在面颊上的热热的液体,把沾着液体的手指放进嘴里品尝着,好苦,好咸,好涩,也有一丝隐隐的甜。是的,这就是眼泪!久违了的眼泪!突然间,羞愧涌上心头,我赶紧把身子转过去,于是我看见了天边的第一抹曙光,听见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