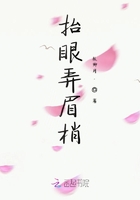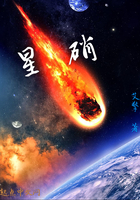“我不喜欢絮叨的对话,这就像是欲盖弥彰的借口。”
此时此刻,下了一整夜的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和芝芝一脸困惑地站在凌荷家前的屋檐下,按着门铃,等她来开。
一个陌生男子却突然凑上来对着对讲机说:“我知道他在你身旁,我很想你。”
隔着门,凌荷把手表递给他,她穿着吊带衫和小短裙,头发有些湿,在这个大雨夜,她眼神疲倦,颈项和裸露的肩膀上有红印,脸颊红扑扑的。
男子接过手表,她转身让我和芝芝进去,便关上了门。一进屋,她对我们说了开头这段话。
凌荷是芝芝法律上的姐姐,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很喜欢这个姐姐。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崇拜胆大妄为、无视这个世界规则的人,现在也是,可很少人是在你了解她之后,还会继续喜欢她的。
那晚,芝芝和我走进凌荷的房间后,都有点儿别扭,猜想是不是会看到让人脸红的场面。情侣的私人空间里,处处都透着隐喻的暗示。我找了张椅子坐下,不敢四处看,芝芝则尴尬又好奇。
“我皮肤过敏,还在感冒中。”凌荷罩了件袍子在身上,两句话就把我们之前的疑惑打消了,原来不是吻痕……
“我一个人住,你们想吃我刚烤的饼干吗?”
碟子里码放着还有些热的小饼干,凌荷介绍说:“名字很好听:玛格丽特饼干。”
全名是“住在意大利史特蕾莎的玛格丽特小姐(Italian Hard-boiled Egg Yolk Cookies)”,据说,很久以前的糕点师在制作饼干时心中默念恋人的名字,将手印按在了饼干上。
凌荷的房间是花色图案的大拼接,花团锦簇,猩红色的棉被、丝绒拖鞋、造型怪异的杯子,四周的衣架上挂着很多仿佛窗帘布一样的衣服,一堆堆杂志和书上摆着烟灰缸和烟,打火机如镇纸般扔在几张单子上。化妆台上放着眼花缭乱的化妆品,几撮亮粉撒在镜子上,还有口红写下的一组号码。墙上贴着几张她的黑白照,真是个镜头感十足的模特。
刚走进屋子,只觉得光线不足,橘色的灯看不清房间的布置,慢慢适应了,心想:怎么可以呢?
小时候无数遍想象以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要装扮得花花绿绿,仿佛心情图案。走进凌荷的小屋,真的就像走进了童年的梦里。
从芝芝口中得知,凌荷是他们家的“叛徒”。她从小就很叛逆,小学时男生三天两头跑来家里告状,把人家给打了。十几岁的时候她和几个朋友跑去很远的地方试镜,做起了平面模特,赚了些钱后开服装店,专卖自己设计的衣服。刚二十岁出头,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凌老板。凌荷的父亲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看不惯她不务正业,从她一意孤行离开学校后,父女俩便开始交恶,平时很少联系。芝芝的母亲偶尔会打电话来关心一下,芝芝跑来这里是瞒着家里的。
譬如这次,芝芝为了隐瞒,跟家里说和我出去玩,其实是来姐姐家。芝芝的母亲当然不希望女儿跟凌荷学,凌荷是“坏女孩”。有天看了林赛?罗翰的电影《坏女孩》,我还问芝芝:“像不像你姐?”她正捧着《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的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遇见的总是人渣,好男孩都是别人的?
凌荷不算美女,她既不柔弱更不温顺,连文静也谈不上,她和她的爱情一样,不等到隆重,没有粉墨登场之时。她长相清丽,波波头,身材纤长,换上T恤和牛仔裤,活脱脱的嬉皮士。
“门口你们刚看到的那个人,他叫陶禾。”
“江兹呢……”芝芝小声地问了句。
芝芝见过江兹一面,用她的话说:“帅得让人鬼哭狼嚎!”
“在养伤。”凌荷点了支烟,细细长长的外烟,味道很淡,氤氲的烟圈从窗户细缝里钻进了雨夜。“他们都是我的男友。”凌荷对我一笑,像是特意解释给我听的,我脸上的表情肯定很奇怪。男人脚踏两只船,会被女人骂人渣,而同类会保持沉默;可要是换成女人这么做,不仅要被男人骂,还有一部分女人也要跳出来“主持公道”。
我和芝芝互相看看对方,十分担心她会不会告诉我们整件事,那个被关在门外的陶禾明明一表人才,怎么不让进呢?当时我和芝芝都只有十几岁,某些细节现在想想,好像还是不太懂。
凌荷选了瓶银色指甲油:“想试试这个颜色吗?”我们都很积极地送上十指,“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样,还要从头说起。”
江兹的父亲和凌荷的父亲是几十年的老同事,因而他俩从小就认识,小学在一个班级上课,前后桌。女孩小时候长得快,她比江兹高大半个头,一吵架,揍他没商量,告过几次状后,他就再也不哭不闹了,乖乖地跟在凌荷屁股后面,被其他男生欺负时,凌荷还会替他出头。
江兹的功课很好,考试成绩年级前十,从小是正太,老师、女生都喜欢他,他在男女生中都混得不错,每天早上他的作业被全班抄。
念到高中时,凌荷认识了陶禾,那时她的心思全不在念书上,她每天都想逃跑,下决心要走,就一定会走。
陶禾家里是开影楼的,认识几个圈内的摄影师,凌荷去拍了几张照片后,便跟着陶禾走了,和家里闹翻。凌父没多久就娶了芝芝的母亲。
江兹是优等生,高中念完便出国留学,一次次打电话去凌家问凌荷的情况,好几次还是芝芝接的,出国之前他还特意登门道别,也就是那次芝芝见到了江兹的真面目,傻兮兮地一路送人家上车还舍不得离开。芝芝告诉我说:“有这么帅又这么好的男孩子跑到家里来看我,我就算病倒也要爬过去!”
凌荷在模特圈打拼了四年后,江兹学成归来,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她。
今非昔比的凌荷,深感与他的云泥之别。
“怎么会有差距呢?你是时尚妖精,他是白衣学生啊!”芝芝冲口而出。
凌荷擦了擦手上沾到的指甲油,不置可否。
她厌倦了圈内的尔虞我诈,决意不再继续。陶禾筹资组建的公司正陷入危机,问她借了一笔钱。她问陶禾要回,他推三阻四地拖延,最后两人为此翻脸,陶禾到处对人诋毁凌荷的过去,连她早年离家的母亲的事也抖落出去,骂她是个十足的贱人,只认钱,指着她说:“像你这么贱的女人,谁会跟你好一辈子!”一向在圈里显得有些神秘孤傲的凌荷,顷刻沦为笑柄。
我和芝芝听得大气也不敢喘一声,面红耳赤,真像是骂在自己脸上的,凌荷则继续着手上的涂抹。
终于要回自己的钱,凌荷开起了服装店,店面不大,货物大多堆在家里。日子过得很清苦,刚开始根本赚不了几个钱,每天起早贪黑,图样画累了就睡在工作台上。她说那段时间是她最开心的日子,这是她喜欢做的事,不用老被乱七八糟的人挑剔,她曾经一天之内被七八个造型师否决,理由是:太高、太矮、太胖、太瘦、太现代、太土气……
“可是、可是当时江兹不是回来找你了吗?”芝芝瞪大了眼睛,小声地说。
“要学Coco Chanel这么厉害,得自己想出路?”我看了看凌荷的表情,她淡淡一笑。
凌荷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时,陶禾回来找她,厚着脸皮想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
“你原谅他了?”芝芝吃惊地看着她,其实我和她心里都有数,陶禾不太可能跪在手表上来这里求凌荷原谅。
“我爱过他。”凌荷涂完了我的手指甲,芝芝凑上来看。她缓缓道:“上过几次床后,就结束了。”
我和芝芝都想问她,为什么不和江兹在一起?他一回来就找你,难道不是想跟你在一起吗?
话到嘴边,怎么都没问出口,凌荷似乎也刻意不去提他。
“你们谁想学做玛格丽特饼干吗?”她笑着问我们,“指甲油还没干透,看着我做就行。”
沸水煮熟的鸡蛋取出蛋黄,在筛网上用手指按压,成为蛋黄细末。软化的黄油加糖分和盐,用打蛋器打发,直至膨松,加入蛋黄细末、低筋面粉、玉米淀粉,用手揉成面团,完成后冷藏一个小时。
凌荷的电话响了,她擦干手去接,声音很轻快地问:“好点没有?我烤饼干呢,想不想吃?”
我猜想会不会是江兹?芝芝伸长了耳朵偷听。
凌荷接完电话回来,看我们的表情就明白了,点点头,说:“没错,是江兹。我明天去看看他。”
“他怎么受伤的?”芝芝问。
“打架。”
“跟谁?”我就是要知道是不是心里想的那个答案。
“你们刚才不是都见过了吗?”她斜了我们一眼。
芝芝给我个“我就说嘛”的眼神,我回她一个“谁说不是呢”。
“芝芝”凌荷忽然表情有些严肃,说:“你别跟我爸说这些事,尤其是关于江兹的事,他问起来也不要说。”
“可、可是以后总会知道的啊……”
“没什么是需要他知道的,你认识了几个新朋友需要向家里交代吗?”
“我是说以后呀,你们结婚的时候!”
凌荷看着她,面无表情:“谁要结婚?”
“你们不会结婚吗?”我和芝芝齐声问了出来。
凌荷气得笑了起来,说:“你们两个言情小说看太多了,以后少看点,满脑子不知想些什么。他和陶禾打架住医院,我就要嫁给他侍奉他吗?干吗呀,以身相许啊,至于吗?”
“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芝芝急道。
“男女朋友过了。”
“你怎么不嫁他呢?”我问。
凌荷沉默。芝芝尴尬地看着我,我塞了块饼干堵住自己的嘴。传说中的糕点师默念着恋人的名字制作饼干,因为变化无常,生活更为美丽,每一口松松软软地入口即化,如爱情是人们心中的柔软,为什么不在现实中发生呢?
“谁会傻得嫁给最爱的人?”凌荷说,起身去冰箱拿面团。冷藏后的面团取一小块,揉成小圆球,在烤盘上用大拇指按扁,饼干出现自然的裂纹。做满一盘,放入烤箱烘烤。
“假如你在乎一个人,在乎得要命,你会把自己那些乱糟糟的过去告诉他吗?你瞒着他,能够隐瞒多久?你愿意下这样一个赌注吗?输了,你连仅有的也失去了,你敢不敢?”
临走时,凌荷送了我们一人一袋饼干,香喷喷热烘烘的,揣在手上,可爱又诱人,芝芝说:“没有人能抗拒这么有爱的小饼干,糕点师倾尽了满满的爱意,每一个都是恋人的名字。”
我们无法回答凌荷的问题,那时,我们还不明白男女之间的微妙万千,总以为真正的爱情就是相知相守、不离不弃。
大雨过后,路面上亮闪闪的。
“他们真的不能破镜重圆吗?”
“凌荷真奇怪,我也搞不懂她是怎么想的,好像真的没什么人了解她。”
“她爸爸呢?”
“不,这点我很肯定。”
“你知道她妈妈是怎样的吗?”
芝芝眨着眼睛,似乎在努力回想支离破碎的记忆:“听邻居说,是跟人跑了,当时凌荷才两三岁吧。她妈妈回来找过,有段时间家里气氛很怪,我听出来是这个意思,她妈妈好像遇到了什么事,我好像还问过我妈,被骂了一顿。”
“你见过江兹,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说话很礼貌,那时他刚高中毕业,很高很帅,是女生会跑去篮球场偷看的男生。”
当时,总以为要不了多久,凌荷总会和江兹走到一起,爱情不就是百折千回、蓦然回首的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跟芝芝打听情况,她闭着眼摇头,一副非常遗憾的样子。
多年后的一个深夜里,我独自一人看电影《两小无猜》,看到落泪,忽然有些明白她了。
爱情在最初最美的时候,即便再小的孩子也懂得弥足珍贵,这是我们的唯一。最爱的人是最好的朋友,我怎么敢冒着失去你的风险去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