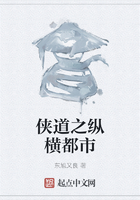绿岫听完乌都奈的叙述,不由微微发慌:事情,想必不会就此结束。她向山洞望去,一阵一阵地担忧。
山洞中。雷诺正为云初定施针医治。
“穆初雨的解药不假,但是你想尽快复还,我还得用些手段。”雷诺说道,“会有些疼痛。”
云初定脸色苍白中隐隐藏有黑气,那是毒-性未尽之兆。他听雷诺如此说,哈哈笑道:“江湖儿女,怕什么痛?我不敢自比关公刮骨疗伤,却也不惧。”
雷诺笑道:“鸿门宴你不惧,刮骨疗伤你也不惧,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云初定所惧何物?”一边说话,手中不停,取出怀中银针,在云初定腿上承山、后溪、阴陵泉,足部隐白、公孙等处皆施了针。
云初定在几处着针时,些微抽了口冷气,但却没叫半声。
雷诺双掌摩擦,以内功助云初定移宫换穴。过了片刻,几根银针皆尽转黑。他以布掩手,拔去银针,置于早先备好的一杯药水之中,以药水渡出针中之毒。又换了数枚银针点刺。如此几次,银针不再转黑,云初定痛感渐去,换之以酸胀之感,眉尖的黑气也尽数褪尽。
他知自己已无大碍,不由赞道:“雷兄弟,你本事这么多,你女人都知道吗?”
雷诺抓抓头:“我就是个笨蛋,她也会跟我好的!”
云初定失笑道:“你倒很有自信!”
雷诺道:“你还没回答我,你有怕的事物么?”
云初定沉吟道:“我之所惧,或者与你相同。”
像他们这样的男人,畏惧的不是生死,而是不能护自己所爱周全。对此雷诺了然于心。他点点头,突然大喊一声:“唉呀,不好了!云兄!”声音中极尽惊恐。
云初定一愣,不知道他意欲何为,一怔之间,绿岫已然冲了进来。她先是惊恐万状,再后来发现云初定已经能自行坐起,欢喜得扑入他怀中,嘤嘤地哭了起来。
展眉也赶了进来,见云初定好端端地,而雷诺却在一边偷笑,瞪他道:“你想吓死人啊!”
雷诺道:“我这不是让他们先苦后甜么?”
展眉道:“苦你个头!我只要甜!”
说话之间,乌都奈的声音响起:“旗主,旗主!”
绿岫忙从云初定怀中离开,抹了抹脸上的泪水。
乌都奈进来,见云初定虽然疲倦,但显然无碍,也自欢喜。瞄了绿岫一眼,忍不住露出点古怪的神情来。
众人顺他目光向绿岫看去,亦是忍不住想笑。
绿岫奇道:“怎么了嘛?你们在笑什么?”
云初定嗤地笑了:“不知哪里跑来一只会说话的小花猫,你说好笑不好笑?”
原来绿岫又是生火又是摸炭,一手的黑,因为心系云初定一直未及清洗,刚才哭得一脸是泪,再这么一抹——可不是只小花猫么。
众人皆笑起来,绿岫恼道:“云初定、乌都奈,你们戏弄我,该当何罪!”
她是无心的玩笑,然在云初定和乌都奈耳中却有如惊雷,是的,她是什么身份,他们又是什么身份!
云初定问道:“乌都奈,你怎么会在这里?”
乌都奈肃然,以最简洁的言语解释了一遍。
云初定听着,脸色变得铁青:“我留信给你的时候,没能预计到接下来的这许多事。所以只是要防若是率丹心旗、乃至联合萨满神宫中与其政见相同的长老,对碧血旗下手。”他叹了口气:“我与若是相斗多年,他有小聪明,但绝无此严密谋划之能。”
从卡洛依被逼婚,到柳初动盗圣器,再到如今令云初定与绿岫暂时“消失”。这背后,是否同一个人的手笔?
云初定想着,与雷诺交换了一下眼色。
从雷诺的眼中,他看到了相同的猜测。他又将目光转向乌都奈:“乌都奈,你们不该来!”
乌都奈争辩道:“旗主,我们难道要一直被欺负?”
云初定道:“还不是时候……你们不来还好,这一来,是授人以柄。若是故意激怒你们,不就是为了有个名头么?他一定会以平叛之名,围剿我碧血旗!”
他这话近乎斥责,乌都奈慌忙半跪下去:“是属下不够清醒!”
云初定道:“不怪你们,你们是担心我的安危。”
雷诺问道:“云兄作何打算?”
云初定道:“我教中的纷争,本来还需要一个长期博奕的过程,只是我……唉!非到不得已,不能让碧血、丹心双旗对敌。乌都奈,你们先悄悄地回去,如果若是还没发难,就罢了;如果若是对旗中所留的妇孺下手,你们正可以保护我们的族人。至于我,我需要时间来修复,你们大队人马在我身边,我反而不易躲藏。”
乌都奈还要争辩,绿岫道:“乌都奈,有我们护住云旗主,你尽可放心。而要让他放心,你还是带人回去,护住碧血旗才是要紧。”她顿了一下:“只有他放了心,才能专心复原,不是么?”
乌都奈瞪着她。适才喜见云初定体内之毒祛尽、对她敌意暂去,现下想起来云初定狼狈至此,实有她一份“功劳”,不免有气,可她所言又在情在理——几种交织的复杂情绪在他内心冲击。
云初定道:“乌都奈,相信我。”
雷诺与展眉也皆劝,乌都奈方同意:“明天一早,我就率部回去。旗主,你好好歇息!”
“不,你们马上走。”云初定坚持,“时间宝贵,对我来说,对碧血旗来说,都是如此!”
…… ……
夜半时分,一直处于冥想入定状态的云初定睁开了眼。他是个无论是精神意志还是身体素质都无比强悍的人,加上之前有雷诺施针救治,短短几个时辰,已然恢复了八九成。
雷诺与展眉在山洞口结营休息,而绿岫却趴在他不远的地方睡着了。
云初定久久地看她,看她绝美的面庞上眉尖微蹙,想是在梦中还在为自己担心。他忽然有些害怕,害怕自己对她作出的“同生死”承诺并非出自本心。
他问自己,他是感动,还是想在她身上找寻穆初雨的另一个种可能,或者,如她所言,是因为他们共有沈一白这秘密?
对待别的事,他从不犹豫,而在感情的世界,他始终受挫。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心意,因而害怕,害怕因此伤害到这水晶一般的女子。
仿佛与他有所感应,绿岫忽地睁开了眼,明眸在昏暗的火堆余光里一闪,犹如天上之星。她见云初定醒了,露出灿烂的笑来:“你在想什么?”
云初定道:“没想什么。”
绿岫坐直了身,她盯着火光,仿佛很随意地说:“你可以反悔,但我会继续努力。”
云初定道:“你不后悔,我便不后悔。”
绿岫眼睛一亮,转而咄咄地直视他:“你后悔,我也不后悔。”
云初定看着她问:“你本来是想去哪?”他问的是前夜,她离开碧血旗后,并未有回萨满神宫之意,他这才策马追她。
“圣地。”绿岫的坦然令云初定吃了一惊。
“去圣地做什么?”
绿岫笑了笑:“你忘了么,我是师傅的弟子。”她是师傅的弟子,这话说得十分无聊,然而云初定竟然听懂了,点了点头道:“确实。”
然后他说:“萨满神宫,我必须去一趟。我必与若是一战,生死战。”这是他一直都明说的事情,然而绿岫竟然也听懂了,点了点头道:“本应如此。”
因为是沈一白的弟子,所以绿岫毫不惧进入圣地,哪怕她是萨满教的圣女;碧血旗若与丹心旗非要站在对立面上,云初定宁可与若是对决,除首恶而求一时之宁。
这是他们当下所理解的对方。
不久以后他们才知道,这不是对方所要表达的全部意思。进圣地、杀若是,都有其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
两人各自想心事,沉默了一会儿。云初定道:“陪我出去走走。”
绿岫二话不说,起身扶住了他。
山林密密,他们登到高处,看星空,看远处连绵的草原。他们很庆幸只需过自己的这一生,不必像那个无休无止地在别人的人生里穿梭的人。他是过客是他所笑言的“打酱油的”,或者偶尔也推动别人的人生,但终究无望地追寻自己的人生。
“你说他现在去了哪?”云初定看得再远,看到的也只能是这个时空的跌宕起伏。
“一定是个很好的地方……”
“他既然在这时空还呆了一段时间才走,为什么不再来找我?”云初定耿耿于怀。在某次事件中,沈一白受伤失踪,他以为沈一白已经死去或施展神通离开,谁知是被绿岫所救。
“师傅说,他讨厌分别。如果注定要离开,分别一次就好,何必一而再地道别?不过是徒增烦恼。”绿岫回答。他是沈一白欣赏的人,她从沈一白的口中听说他许多事,所以她说,在他们相见前,她早就认识他。
她靠住他的肩,忽然,她发觉他的肩上的肌肉硬了起来,那是感知敌人的本能反应。
她也做出了本能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