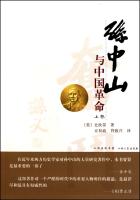月色朦胧,四下黑漆漆的,野地的野草旺盛,在月光下摇曳。萤火虫在草地里飞舞,忽闪忽闪。若是别的什么地方,一定是极美的。但这是一片乱葬岗,破败的碑牌歪七扭八的竖着,鼓起的坟头长满了野草。周围也有露在外面的棺材,里面的尸体被野狗拖出来,啃得七零八落,露出森森白骨。那些野狗如狼一般,在黑夜里,一双双眼睛绿幽幽的,不时传出抢食时发出的咆哮声。
鬼火荧荧,一个又瘦又小的身影举着火把,硬着头皮走在这片坟地里,不时警惕的停下来往四周看看。
她爹已经失踪了大半年,这半年来,她一直在找,找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今天,她去了更远的邻县。白天的时候不觉得这里可怕,但这会儿,身上汗毛直立。
地面不平,忽高忽低,她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一个没踩稳,扑倒在地。火把本就是她用枯草树枝随便做的,扑哧一下熄灭,化成了缕缕白烟,四下顷刻一片黑暗。
惨淡的月光下,李茯苓还没来得及爬起,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就在眼前,她差点没大叫出来,但怕惊动了野狗,忙捂住了嘴,退缩着躲到一边。
没有了灯火,她更加害怕,摸到那火把,缩到一棵老树下,哆哆嗦嗦的从怀里摸出一个火折子。
她吹了几口,火折子亮出火星,正要往火把上去凑,忽然发现前面草丛里一团红光忽明忽暗。
那是什么?
李茯苓没少听乡人说过野地里的鬼神妖怪故事,顿时身上冷汗直冒。
一阵风吹来,草低云动,李茯苓吓了一跳,手颤抖了一下,火折子滚到脚下草丛里,再去找,已经找不到了。
前方的红光还在闪动,身后隐约传来动物踩踏草地的声音,李茯苓咽了一口口水,吓得不敢再乱动,双手合十求神保佑。
过了好一会儿,腿都蹲麻了,前面的红光依旧不肯离去,一闪一闪,好像在召唤人似的。仔细一听,好像有什么东西摩擦的声音,一下一下,并不清晰。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李茯苓狠狠咽了一口口水,壮起胆子轻手轻脚的摸了过去。
那一眼,叫李茯苓难忘终生。
那红光并不是什么妖鬼之光,而是灯笼,围着一个坑摆起的灯笼。
那边有人在挖坟地!
还好是人,李茯苓松了口气,拍了拍胸口,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
嚓嚓,一下又一下,有条不紊,铁锨扬起的尘土淹没月光,很快的,就冒出一具棺材。油亮的黑漆在摇晃的红光下,闪着幽幽冷光,说不出的诡异。
李茯苓松了口气后,又提了起来,大气不敢出。
这些人这么晚来挖墓,看他们的装束,并非普通人,但乱葬岗,埋葬的都是贫贱百姓,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棺材?
正疑惑时,隐约听到有人说话。她屏气凝神,就听一个手下模样的人对着一个黑影说话。
“主子,是否开棺?”
李茯苓擦擦眼睛,眯了眯眼,这才看到阴影深处的一个高大黑影。随着那个黑影转过身来,慢慢的走出阴影,轮廓越来越清晰,而李茯苓的眼睛也睁得越来越大。
她从没见过长得那么好看的人,又显得那么清冷,那么高贵。
脸是月色白,眉是墨染黑,那一双眼,看似慵懒,却有着洞悉一切的锐利,睥睨天下的霸气。
“开……”
“是!”那人得令,一抱拳,马上指挥开棺。
随着吱吱嘎嘎的一阵声响以后,棺盖终于开启了。
这时,李茯苓的全部注意力也全部被吸引了去,拨开草丛,脖子往前探了探。
就见那男人走上前,弯下腰来,将里面的人抱了出来。
如瀑的长发在月光下倾泻而下,一袭白衣风中轻扬,绝美的脸如九天下凡的仙子。她闭着眼,仿佛睡着了。
那男人的目光冷淡,看不出喜怒,抬手摸了一下她的眉心。李茯苓这才注意到,她的眉心有一点红印。
太美近于妖。
李茯苓的脑海浮现了这么一句话来。
那女子也不知埋了多久,还未腐烂,一阵夜风吹来,她闻到一股香味,淡淡的,但很好闻。
她睁大了眼,看着前方那一对人,觉得他们像是话本里所说的——神仙眷侣。只是可惜,爱侣已逝。
李茯苓替他们可惜,轻轻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不是她的动静惊动了男人,那男人往她这边的草丛瞥了一眼,目光冷的如同寒冰一样。
李茯苓吓了一跳,忙缩了脖子,压低了身子。那男人没有再有什么动静,李茯苓也不敢妄动,窝在草丛里,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不知怎么的,她的眼皮子越来越沉,不知不觉间就睡了过去。
等她醒来,已经是很久之后,那些人早已离开,只留下一具空荡荡的棺材。
李茯苓没敢再多做停留,也没了勇气再去一探究竟,拔了腿就往家里冲。
她的家在封水村,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四面环水,走过一座破败的石桥就到了。
这个时候,村子里安静的几乎听不到声音,只有薄薄的门板遮掩不住屋主发出的鼾声。李茯苓脚步匆匆往家门赶,才到门口,隐约听到里面有说话声。
“李大娘,说句不中听的,你们家老李多半是回不来了。你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多孩子生活,总要想想将来。你们家茯苓长得机灵,过去了未必吃苦。做童养媳有什么不好,怎么说也是个少奶奶,还能帮着你一起养家……”
这一梦,李茯苓竟然梦到了很多年前,她已很久没有再想起的事。
那时,她才八岁,去顾家做童养媳之前。
李茯苓擦了擦眼角不知什么时候流出的泪,起身坐了起来。
这个时候,天色依旧黑得深沉,月光笼罩大地,跟那个夜晚一样。
李茯苓看着窗外,一时怔忪。她怎么会做到那个梦……
今天的那个墨衣竟然跟记忆中那个男人的脸如此相似,难怪她会有一种好像见过的感觉。
可仅仅是相似,她很清楚,那个男人与今日的墨衣,不是同一个人。